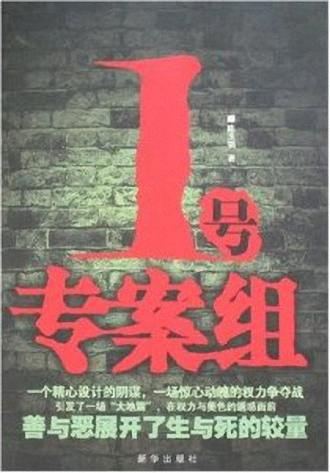专案组长-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姝怎么突然提出这个要求?”
林为驹冲吴伟苦笑:“我这两个女儿干什么都爱较真。”林为驹将目光转向司徒竞湖:“你让人告诉文姝不要问一些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以免拖延审判时间。还要告诉文亭,审判要抓住金玉良主要问题进行。”司徒竞湖站起身。
吴伟掠了一眼林为驹:“沙叶霜是干什么的?”
一个副市长回答:“原来黄金公司的会计,被收审了六个月,很有情绪。”
“有情绪?她今天为什么不到庭?她现在在哪?”吴伟问。
第三节 重要证人未到庭
沙叶霜在哪?她正在和老同学、现任吴伟的秘书李毕书飙马。
她事先已经知道今天的判决结果,也知道今天她到庭的所有证言都将白说,都是屁也不如的一股热气。于是她决定将刚接任吴伟秘书的老同学约出来,以便在新来的领导跟前埋颗钉子。蓝天丽日,只是绿草不能如茵。这种时候应该说还不是飙马的最好时机,但为了将来,为了金玉良的命运,沙叶霜还是提前了这个活动。两匹飞马并驾齐驱在草原上驰骋。沙叶霜有意将这个夹紧尾巴在市委混事的老同学甩在后面,不时回头看看他玩命追赶的样子。这小子总算十年媳妇熬成婆,一下子窜到了大秘的位置上,过不几天这小子就会抖起来的。沙叶霜必须抢先登陆,好歹这小子在学校时对她就有过那么点意思。沙叶霜看着神采飞扬追来的李毕书,有意放慢了速度:“怎么样?比你待在办公室里开心吧?”
“不开心。骑马开什么心?现在人家都在骑……”
“骑女人?你们这些臭男人,整天想什么啊?”沙叶霜冲胯下的马猛地甩了两鞭子:“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学坏了,我手里的鞭子可是不饶人的。”
李毕书冲他的马也下狠劲甩了两鞭子:“要是现在领导找我,全瞎了。”
“你们书记现在不是在听金玉良的审判吗?你听你听!毕书。”沙叶霜几乎和李毕书同时勒住了马头。他们被远处飘来的一首牧歌吸引住了。那歌声很美,尤其是在这草场泛青的季节里,尤其是在牛羊躁动着春情的艳阳下,这歌声是发自心底的对生命的呼唤,每到这种时节,只要来草原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沙叶霜和李毕书信马游缰地迎着歌声走去,唱歌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的身边围着低头啃草芽的羊群,她的音域很高,声带很宽,歌声没有任何修饰,草原的歌手大都是从这里练出来的。
沙叶霜瞥了眼李毕书:“像不像一幅油画?蓝天白云,少女和不加任何修饰的歌声……”
李毕书苦笑道:“老同学,你死拉硬扯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想干什么?说吧!该不是让我听歌的吧?”
“趁你还没有老于世故时,帮你找回一点童真和自己。另外,你现在是全市第一书记的秘书,我得先巴结巴结你。”
“说目的吧。”
“目的就是金玉良的案子。想让你在新来的市委书记面前说几句公道话,让他知道金玉良是代人受过,全案都是一个骗局,一个大骗局。”
“你……你说什么?全案是一个大骗局?”
“金玉良只不过是黄金大案的一只替罪羊,全部都是假的。”
李毕书看着沙叶霜:“现在正在审判!你,你为什么不早说?”
“早说有什么用?现在这座城市里没有人能有这个回天之力。如果说将来有的话,那只有一个人。”
“你是说吴书记?”
沙叶霜瞪了眼李毕书:“否则,今天我请你干什么?还不如坐在草根前看蚂蚁搬家。我可告诉你,这马可都是花钱租来的。”
“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雪山查的吗?后来怎么让他出差了?”
“如果让雪山继续查下去,那西方市非乱了套不可。他现在正在返回的路上。”沙叶霜一叩马蹬跑了。
第四节 黑锅谁背
车窗外的绿色渐渐少了,雪山知道火车已经驶出了八百里秦川,正在向中国的最西部飞驰。西部,这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那里的一切都还处于生长成熟的阶段,那里充满着生机与希望,那里更像个刚刚长高的女孩,在热切地期盼着少男们热辣辣的目光。转业时,部队首长问他愿不愿意留在南方,他用摇头做了回答。他决定回到生他养他的西部土地上来,他认为这里才是他生命的根,这里更需要他。没想到回来后,市上领导就让他接手黄金公司的案件,而且担任专案组长一职。他不知道组长是什么级别,什么规格,组织上的安排,他只能听命。查了六个月的案子,刚查出点门道,市长又让他带队来南方考察纺织业。作为军人,服从是他的天职,但他确实想不通,工作如果这样变来变去,哪还能干成什么?他带过兵,当过团政委,他知道如何用人,更知道如何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次调整他的工作使他真的不明白他是铁还是钢了。前天他在电话里才听妻子林文姝说,金玉良案要开庭审判了,而且是她担任金玉良的首席辩护律师。他当时有些懵,这么大的案子,他作为专案组长查了六个月,竟然不让他参加开庭,也不通知他参加庭审旁听,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
雪山一点打扑克的心情也没有,他脸上被几个随员粘满了纸条,而且纸条还在增加。“组长的脚太臭,能熏死人。”
“嫌臭不打行吗?”
“不行!我们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办了半拉子的那个黄金专案,现在开庭了,却不让你参加。”一个随员边抓牌边带有讥讽地说。
“头儿,那金矿是怎么开的?那些金把头是怎么进死亡谷的?那些采金的老乡交的钱怎么退?死的那些金农谁来承担责任?你整了六个月,整清啦?”
雪山不想同任何人交流自己的想法,他只顾打他的牌。
“判了个金玉良,那是找了个替罪羊。现在的事……嗨!谁较真谁他妈是傻熊!”
雪山轻轻将牌拢了起来:“出牌!”
“组长,反正都是共产党的事,你当专案组长和当考察组长都一样,你要不是跟市长拍桌子,还不会有这次公款旅游的机会呐!”
雪山轻轻闭上了双眼。
“这也不是我们说,外面都在传,说是你自己冲司徒市长一拍桌子退出了黄金专案组……”
雪山猛地站起身,用力从毛巾杆上扯下毛巾,他要用凉水清清自己的脑子,他现在大脑热辣辣的很乱。他回来干什么?又能干什么?闹法庭?跟人家拼命?脚下车轮铿锵铿锵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雪山到现在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可笑。你现在不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团政委了,你已经退役,你已经是个临时性的组长,你的思想必须从部队转到地方来。出来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朱支峰他们就能把金矿开采审批的问题查清喽?国家的矿产资源向个人开放,这样才是资源的合理配置?金玉良能有审批金矿开采的权力?这些问谁去?即使查清了,那倒卖给金农的采金证的钱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们能退给金农们吗?朱支峰啊朱支峰,你和文亭是多么的浑啊!你们可不能糊涂,你们要对百姓和历史负责的!
雪山决定中途下车,去土吉淖,去找那些受害金农的亲属们,那儿也许才是他现在真正应该去的地方,这也是他决定返回西方市时经过反复思考的问题。而且要设法找到林文寒,让她把真相进一步向社会上披露。她现在从北京返回西方市了吗?回答他的只有铿锵铿锵的车轮声。他现在大脑一片空白,只是下意识地在倏倏闪过的车窗外去追寻那些可能出现的绿色,然而车窗外全是黄色的世界,黄土地,黄泥屋,光秃秃的山野,光秃秃的村落,偶尔闪过的几棵古槐老柳也很难看出它们开始复苏的样子。雪山苦笑笑,这种时候你还在这一方天地寻找绿色,不是大白天做梦吗?他回望一眼半掩着的卧铺门,几个随员还在继续他们的话题。
“知道林老爷子为什么让雪山带队出来考察吗?”
“说说内部消息。”
“老爷子原来安排这主调查黄金大案是有他的想法的,一个刚从部队转业的团政委,他得要有点政绩,而黄金大案上上下下都知道,老爷子想让他冒一炮,然后安排一官半职不是顺理成章吗?可是这主太冲,非要打破沙锅璺到底,把黄金大案查个底朝天,这不乱了套了吗?于是……”
“于是老爷子怕他在黄金专案上捅了娄子,但又要提拔他,就把他弄出来带队考察南方的纺织业,然后提拔他当副市长。这些都是你的杜撰吧?还是真有其事啊?”卧铺厢内传出一阵快乐的笑声。
“嗨!这种事见怪不怪,连孩子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现在是父子局,夫妻科,儿子开车爸爸坐,孙子倒水爷爷喝,婆媳办公桌对桌。人家有个当市委书记的岳父,这就够了,岳丈大人给女婿发个官帽还不是小菜一碟?有什么议论的。”
“不是说安排他到财政局、税务局和市政府,他都不干,非要到检察院反贪局不可吗?”
“现在怪事就是多,有人求钱,有人谋权,这主却谋虚的。嗳!你们听说了吗?这小子在部队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侦察敌情时,在敌人的粪池里潜伏了一天一夜,鼻孔里全爬满了蛆。这次为了他的工作安排,没把他岳丈大人气得晕过去。”
“要说这市里也怪,黄金专案谁也不抽,偏偏抽了个朱支峰,法院那边呢,又点名让司徒文亭上。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这三剑客是战友?而且一个是书记的女婿,一个是市长的儿子,这要是办错了案……”
“说不准这还是领导有意安排的呢!”
雪山不自觉地看看腕上的表,还有二十分钟车就要到土吉淖了,他不能回西方市,他要去看看那些受害的金农。那场雪崩被埋进雪里的金农,他们土吉淖就有13人,可是作为黄金专案组的组长,你到现在还没有找他们了解关于雪难的第一手情况呐,你的专案组长称职吗?你为什么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这个专案组长,而且又和朱支峰、司徒文亭他们搅和在了一起?而且是人家早已设计好的方案,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必须沿着这套设计好的方案进行?他觉得他仿佛钻进了一个长长的掩埋起来的战壕里,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即使头上的对手在埋地雷,他也只能在地壕里等死。可是那些死难的金农呢?雪山用脚后跟叩了叩卧铺厢的门示意里面的议论该停止了。卧铺厢半掩的门被拉开了,几个随员看着雪山冰冷的脊背,有些尴尬,“进来吧,你站在门外干什么?”
“我不站在门外,能听到你们的长篇大论吗?”雪山阴着脸走进卧铺,开始收拾他的行李。“一会儿到土吉淖,我提前下车。”
“头,那我们,我们……”
“回去,先在家歇着。”
雪山没想到一踏上土吉淖的土地心里就有一种冲动,而且每次都是这样,死不悔改。他现在人过中年,已不是20年前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冲动?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有时他也冷静地问过自己,家乡是什么?不就是那些不规则散落的黄泥小屋?不就是那些整日袖着手闲得心慌的穷庄稼汉?他整日魂牵梦绕的就是这些?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雪山才慢慢弄明白,这是一个长期漂泊在外的游子对生命对根的追寻。村庄里因为没有什么树木,比以前更显得荒凉,这种荒凉感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就如同他们的火车进入函谷关西行一样,那种感觉除自然本身以外,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
路边是土吉淖的墓地,也是土吉淖的历史。
至于土吉淖什么时候有了人家,什么时候有了村庄,人们从哪里来,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生息之地,已经无人能说清楚了。只有这片不大的墓地能告诉你土吉淖的过去。每年的清明节,土吉淖的人们都扶老携幼来到各家的坟堆前,为过世的亲人们添土烧纸,后人对三代以下的坟堆还能知道,对三代以上的就不太明白了,添的土和烧的纸钱也相对减少,以致先人们的坟堆慢慢低矮下去,有的最后夷为平地。雪山每次探亲路过此地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沧桑感。
墓地的间隙中出现了一些新埋的坟茔,坟茔上的纸幡有的虽然已被风沙打碎,但还在瑟瑟地飘动着。新的坟堆正好13冢,雪山知道这是死亡于金矿的那些金农们,也就是说,家乡的这些鲜活的生命除了他们的新坟堆外,已经进入了土吉淖的历史,不几年他们就会像那些长出草芽的坟茔一样,成为人们慢慢淡忘的过去。
母亲阿牧吉做梦也没有想到儿子雪山能回来,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呢?“饿了吧?妈给你弄吃的去。”
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