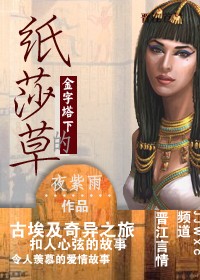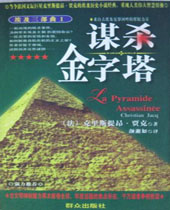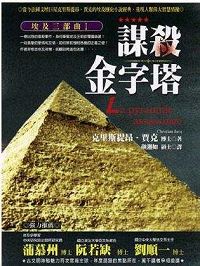我钻进了金字塔-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85年1月,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前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首席顾问达什获准访问这位已经与世隔绝了23年的伟人。达什写道:“他身材修长,仪表堂堂,看上去不到66岁。自制合体的咔叽衣裤,没穿囚服。平静、自信、具有威严的举止绝不像一个游击队员或激进理论家,而像一位国家元首。”
此时曼德拉的处境进一步改善。早晨三点,曼德拉开始做操、举重、俯卧撑、跳绳和长跑,然后淋浴、浏览报刊、听新闻广播。早饭后看电视节目“早安,南非”,继而是处理来往信件。共有十几名士兵看守着曼德拉,其中三名几乎与他寸步不离。
曼德拉结过两次婚,早已离婚的第一位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这位妻子现在与曼德拉惟一的儿子在老家特兰斯凯开杂货店度日,女儿梅基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第二位妻子就是著名的温妮,她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泽妮嫁给了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二世的第58个儿子,小女儿津妮成了作家,现在美国。
早在1956年还在念中学的22岁的温妮在法庭上第一次见到曼德拉,当即被这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律师所吸引。当接到曼德拉请她去吃午饭的邀请时,竟激动得“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服”。曼德拉经常不断地请温妮吃麻辣的印度饭,拉她到体育馆去看他如何锻炼得大汗淋漓,由此拉开奇特的爱情序幕。
1958年6月,正受“叛国罪”审判的曼德拉获准离开约翰内斯堡与温妮结婚,可保释候审只有四天时间,传统婚礼才进行一半,曼德拉就赶回法庭受审。由于曼德拉的政治活动被判非法,从此新娘温妮只有待午夜窗户上神圣的叩打出现,才能与新郎柔情一番。
一天,温妮为家里那辆因老掉牙而趴窝的破车发愁,当天来了个穿蓝工装、戴宽边帽的修理工。修理工命令温妮上车,直开进一家汽车修理厂,温妮这时才认出这个化装成修理工的大个子竟是曼德拉。曼德拉帮温妮卖掉破车又买了辆新车才消失在熙熙攘攘的公共汽车站里。
1962年曼德拉被判入狱时,温妮刚怀上小女儿津妮。
温妮总是每月千里迢迢赶赴罗本岛,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指定的路线乘船渡海,只为能隔着装了厚玻璃的铁窗看看一眼憔悴的丈夫。
狱中的曼德拉每天都抚摩身边的温妮照片,他在给温妮的信中说:“婚姻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互相爱恋,而且在于相互间的永恒的支持。这种支持是摧不垮的,即使在危险关头也始终如一……我真想在你身边,把你抱在膝上。”
直到22年后,南非当局才允许曼德拉夫妇直接接触,“这22年中我们甚至没碰过彼此的手”。当这对夫妻拥抱在一起时,连狱警也表示剥夺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男人拥抱妻子和孩子的权利22年之久是可恶之极的。
获释出狱劳燕分飞
1990年2月11日16时15分,南非开普敦维克托·沃斯特监狱大门打开,被囚禁了27年的曼德拉在警车和直升机护送下走出牢门。年已71岁的曼德拉须发斑白,与夫人温妮手拉手向群众挥手致意。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记者汇集于此,报道曼德拉出狱,据南非报纸称,第一张曼德拉出狱的照片当即以数百万美元的高价被美国人买走。
曼德拉两位妻子养育的一子三女已经长大成人并为他生了12个孙子孙女,儿孙绕膝,其乐融融,清晨,温妮为她年迈的丈夫挑选合适的衬衫和领带,摆好不含胆固醇的早餐,盯着他服完药,敦促他到院子里会见客人。温妮结婚31年后才首次经历这种家庭主妇的生活,她表示:“我对这种状况很不习惯。”比她大十八风岁的曼德拉“甚至不能洗涮一下他喝水的杯子。在监狱里人们从不让他做这类事。”
温妮嫁给曼德拉时还是个年仅22岁的幼稚的女学生。
在婚后的31年里,她独自一人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并坚持探视狱中的曼德拉。南非政府不断地对她拘留、监禁、流放,温妮住在无水无电漏雨的草棚中,吃未熟的米粥、带泥的萝卜,子然一身面壁而坐。久而久之,她产生了被遗弃的感觉,养成了酗酒的毛病。一次,她在屋内换衣服,一名警察闯进屋来,暴怒的温妮一跃而起扑将上去,将警察打翻在地,几乎扭断了警察的脖子。
温妮把自己当做曼德拉的替身、非国大当然的接班人,时而表现出独断专行的作风,令非国大领导人十分不满。
九年的流放生活使她养成好斗的作风,这与曼德拉“不反对白人,只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温和政策格格不入。温妮组织的“曼德拉俱乐部”是一个以街头流浪者为主体的冲锋队、频繁地介入斗殴、绑架、刑讯乃至谋杀。温妮本人经常威胁当地少年加入她的组织,否则就将他们干掉。
1988年12月,温妮手下的人干掉了与她政见不和的斯通比,司法当局在调查臭名昭著的“斯通比案”中发现温妮本人也卷入了这场丑闻。此外,还有23起刑事案与温妮有牵连。这使曼德拉十分尴尬,忿然命令温妮立即解散“曼德拉俱乐部”,可温妮置若罔闻。
曼德拉考虑多年的独居生活和南非政府的持续迫害给温妮生理心理造成的创伤,企图以宽容抚慰温妮,让她担任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长。可温妮我行我素,酗酒闹事,公然与一个29岁的情人同行同止。曼德拉在忍无可忍之后,断然撤销了温妮的部长职务,并与其分居。他对报界宣布:“鉴于我们的分歧,最好的抉择是分居。但我对她的爱决不减弱,我希望诸位理解我正在受的痛苦。”
“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在南非,家喻户晓的曼德拉是最受欢迎的黑人领袖,他的声望犹如他受囚禁的岁月一样令人肃然。索韦托“十人委员会”主席莫特拉纳对公众说:“如果有一个人能把南非各个组织的黑人团结起来,这个人只能是纳尔逊·曼德拉。”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黑人大主教图图说:“曼德拉是南非黑人的真正领袖,政府必须把他作为黑人领袖对待。”
出狱的曼德拉利用自己的威望取代年老多病的坦博,负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他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与开明的德克勒克政府间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并赢得南非最大部落祖鲁族酋长布特莱齐的合作。曼德拉成了名副其实的南非260万黑人的领袖,其坚定而又温和的政治主张得到其他种族的理解和支持。
1993年夏,曼德拉列席在开罗举行的非统国家首脑会议,一时成为大会的核心人物。当身着黑色西装、雪白衬衫,系花格领带的曼德拉气字轩昂地缓缓走人会场时,尽管他走路时大腿略显不适,但腰板挺直,形象特别高大。当时,开罗国际会议中心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迎这位领导人。
这是南非代表首次被非统国家组织接受的象征。当时,我作为新华社摄影记者有幸一睹他的风采。曼德拉是非洲贵族与英国贵族风格的混合物,教会教育使他言谈像个英国绅士,衣着风格也是英国式的。祖上的皇族血统使人觉得他举止自尊自信甚至傲慢。曼德拉身高约在1。80米以上,头发花白,步态和缓潇洒,怎么看也不像75岁的古稀老人。尽管当时他参加竞选总统尚无结果,可其优雅的绅士风度、敏锐的思维、略带伦敦口音的英语表达,使他的政治魅力超过了在场的任何一位国家元首而成为众多记者捕捉的目标。
一位中年女秘书始终不离他的左右,礼貌但坚定不移地把围拢上来的各国记者控制在一定距离之外,以免这帮全身披挂、鲁莽好动的家伙碰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曼德拉优雅地坐到代表席上,只有极少数人“POOL”(英文:池子。按国际通行惯例,在重大采访中,因记者太多而实行的特殊采访权制度。一般由主管当局和记者协商推举国际著名新闻单位或资深记者享有特殊采访权,代表全体记者采访,所得采访素材全体记者共享。获得特殊采访权的记者称POOL)的摄影记者获准进入会场,我亦有幸混迹其中,紧跟在曼德拉四周。我右侧的WTN记者法鲁克一上来就朝曼德拉大喊:“您想您能当选南非总统吗?”直震得我右耳暂时失聪。
也许因为我是当时在场唯一的黄面孔记者,曼德拉对这张以众多白脸为背景的黄脸格外客气,频频朝汗出如浆的我点头微笑。
“Poo1”采访结束,趁与曼德拉合影留念之机,我破坏摄影记者不得提问的惯例,向这位为自由而身陷囹圄27年之的斗士表示敬意。我低声告诉曼德拉:我是中国记者,正在写一篇有关他传奇的小文。这位目光炯炯的慈祥长者各善地望着我:“无论我们对谁产生多大的敬意,也不要把他写成天使。因为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
第7节 我的外国记者朋友
莽汉纳伯特
在开罗市泽马利克区一幢别墅的阳台上,一条壮汉正逐一向参加酒会的来宾打听最新出品的镇静剂,因为现有的所有安眠药对他都已不起作用。他懒洋洋地变换着姿势,努力保持上身水平以使一只以他的驼背为沙发的黑猫睡得舒服些。他一面大口嚼饮不加冰的黑牌威士忌,一面不停地埋怨时运不济,混到如今这步田地,回忆当年玩命的辉煌岁月。这条蓬头垢面的壮汉就是大名鼎鼎的纳伯特。席勒,美联社驻开罗摄影记者,一条胆大包天的莽汉。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位老兄在许多场合的古怪举止只有在娱乐宫拐角的哈哈镜中才能找到。
以色列从加沙撤军前夕,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拉宾在开罗紧急会谈,上百名记者汇聚开罗总统府。十几位资深记者,身佩胸卡,自报姓名,获准鱼贯进入总统府,所有人都诚惶诚恐,惟有纳伯特·席勒一脸狠亵地自称是《花花公子》摄影师,结果一下子惹恼了不苟言笑的总统卫队。幸亏美联社牌子大,一位新闻官员又认识纳伯特的老脸,才把众目睽睽下出尽洋相的纳伯特从轻发落。
埃及内政部长被刺,安全人员拳脚相加驱赶摄影记者,一拳正打在纳伯特的小腹上,这条莽汉当即大吼一声,放开美式门户,直打得那个警察望风而逃。以上这两场闹剧都是我亲眼目睹。
谈起辉煌的往事,纳怕特总是陶醉在两伊战争的硝烟里。当时他受雇于法新社,把自己绑在直升机的滑橇上,航拍波斯湾的海战和油井大火。这类冒险对他可不是偶尔为之。纳伯特每天不停一直干了整整一年半。当他结束这份工作、返回老家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时,就像远征伊比利之后凯旋的拿破仑。家乡电视台的一个摄制组闯进他本来已奇热无比的小屋,又打亮两盏钨灯,直烧得他面对摄像机双手乱舞:“我是自始至终呆在直升机滑橇上而惟一活下来的人。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战争中的人全他妈疯了!”
纳伯特在开罗已经住了12年,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聪明远大于他的鲁莽,至今鼓舞他振作起来的惟一动力还是他早年看过的一本书,该书的作者威尔福雷德是位勇猛异常的英国水手,本世纪初便横扫了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伊拉克沼泽等人迹罕至的各种禁地,并将自己亲历的奇闻轶事著书出版。
纳伯特嚼了一口威士忌:“我现在还在读威尔福雷德关于埃塞俄比亚的一本书,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内燃机的发明大大损害了世界原本完好的面目。我本应生活在威尔福雷德时代,真正的探险不依赖任何机器,人只有强迫自己把他的能力用到极限才叫探险。”
埃及是纳伯特人生探险的第一站,他在这里的感悟远比在中东、非洲其他洪荒之地十多年劫掠式探险的全部所得还要有价值得多。
1978年的欧洲是纳伯特人生的跳板,当时他与其他两名大学生邂逅于雅典,计划暑假周游欧洲。纳伯特主张去土耳其,可他的两位朋友却心血来潮要绕道开罗。
“就是当初死活要来开罗的那两个家伙,在开罗呆了三天便悄然而去,而我则坚持下来,我一直向南走到卢克索。在那里,我一人冥思苦想了六个星期,最后我对自己说,我必须生活在这里。”
纳怕特埃及之旅恰逢吉米·卡特总统促成埃以和谈的万象更新之时,当时埃及到处充满了生气。即使这一和平浪潮刮过之后,其余波还久久不散。无论在街头还是在公共汽车上,每个人都想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每个人都要你明确表明你的观点。纳伯特正是为此才重返埃及的。
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继续学完三年课程后,纳伯特感到重返埃及的时候到了。当时他面临三种职业选择:旅行摄影师、自由作家和国际救援志愿人员,纳伯特的背景显然无法与牛津、剑桥的毕业生相匹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