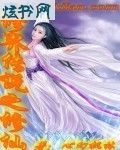梵高传-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儿呢?泰奥生他的气了吗?当他刚刚开始他的事业的当口,泰奥却食言了,这可能吗?他在上衣口袋里找到一枚邮票,这使他能够写信给他的弟弟,请求他至少寄来生活费的一部分,以便能让他有饭吃,并能偶尔雇请一个模特儿。
他接连三天饿着肚子,早晨在莫夫那儿作水彩画,下午在施汤所和三等候车室内作速写,晚上或到皮尔克里,或到莫夫家继续作画。他担心莫夫会发觉他的处境,从而感到气馁。文森特认识到,尽管莫夫喜欢他,但他的麻烦一旦开始对莫夫的绘画产生影响的话,他的表兄将毫不犹豫地把他甩在一分。当叶特留他吃饭时,他谢绝了。
胃里的微弱而迟钝的疼痛使他想起了博里纳日的日子。他一生都将挨饿吗?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不会有一刻的舒服和安宁吗?
第二天,他强忍着自傲去见特斯蒂格。也许他能从支持海牙一半画家的那个人手里借得十法郎。
特斯蒂格有公事上巴黎去了。
文森特发烧了,没法再握笔。他上床睡觉。第二天他抱病勉强再到普拉获广场,发现这位艺术商在店内。特斯蒂格答应过泰奥照顾文森特,他借给后者二十五法眼
“我打算过些时候来看看你的工作室,文森特,”他说。“我很快就会来的。”
文森特只能有礼貌地回答。他想走开去吃点东西。在他去古皮尔公司的路上,他曾想道:“只要弄到几个钱,一切又会好起来的。”但现在钱虽然弄到了,却更为不幸。他感到孤苦伶仃。
“饭会治好一切。”他对自己说。
食物驱走了他胃里的疼痛,但没有驱走占据着体内的一个说不出来的地方中的疼痛。他买了一点廉价烟草,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吸着烟斗。对凯的渴望又剧烈地回来了。他感到极度的不幸,几乎不能呼吸了。他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窗,把头向外伸到冰天雪地的正月夜空下。他想起了斯特里克牧师。他通身发冷,就好象在一所教堂的冰冷的石墙上倚靠得太长久了。他关上窗,一把抓起帽子和外衣,出外奔向他在雷伊恩火车站前面所看到的一家酒店。
酒店的人口处挂着一盏油灯,酒柜上也挂着一盏。店堂中央半明不暗,靠墙放着几条长凳,凳前是杂色的石面桌。这是一家劳工们的酒店,墙面利落,水泥地,与其说是一个寻开心的地方,毋宁说是一个避难所。
文森特在一张桌旁坐下,他无力地背靠着墙,当他作画的时候,有钱买食物和雇请模特儿的时候,情况还不坏,但他能与谁作伴,友好地随便拉拉家常呢?莫夫是他的老师,特斯蒂格是一个繁忙、显要的画商,德·博克是上流社会里的有钱人。也许一杯酒能帮助他消愁,明天他能作画,情况会好转起来。
他慢慢地呷饮着酸味的红酒。店堂里人不多,对面坐着一个劳工模样的人。酒柜近旁的角落里坐着一对男女,女的衣饰俗而。隔壁桌上一个女人单独坐着。他没朝她看。
传者走过来,粗鲁地对那女人说:“还要酒吗?”
“一个钱也没有了。”她答道。
文森特转过身去。“和我一起喝一杯好吗?”他问。
那女人对他看看:“行。”
侍者送来一杯酒,拿了二十生丁,走开了。两张桌子并了起来。
“多谢。”那女人说。
文森特仔细地端详着她,她并不年轻,也并不美,有点憔悴,一个生活已经完了的人。她、身材瘦削,但是匀称。他注意到她那握着酒杯的手,不象既那样,是贵妇人的手,而是一个辛苦劳动人的手。她使他模糊地想起了夏尔丹或扬·斯蒂思所画的一些奇妙的人物。她的脸当中挺着一根钧鼻,嘴唇上隐约可见些许须毛。她的眼睛忧郁,但很有生气
“没什么,”他回答。“多谢你作陪。”
“我叫克里斯廷,”她说。“什么?”
“文森特。”
“你在这儿海牙工作?”
“对。”
“你干什么?”
“我是画家。”
“哦,那也是一个鬼差使,对吗?”
“有时候。”
“我是洗衣服的。我有足够气力的时候就脱不过并不是经常有气力的。”
“那你又干什么呢?”
“我在街上漂泊好久了。当我没有气力干活的时候,我就回到街上去。”
“洗衣服是很辛苦的吧?”
“对。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他们的钱不是白给的。有时候,洗了一花天以后,我还得找个男人为孩子们挣点吃的。”
“你有几个孩子,克里斯廷?”
“五个。我肚里又有一个了。”
“你丈夫死了?”
“孩子的爸爸都是陌生人。”
“生活不好过把。是吗?”
她耸耸肩。“他妈的。矿工不能因为可能送命而拒绝下井,他能吗?”
“不能。你可知道其中有一个的父亲是谁吗?”
“只晓得第一个五八蛋。我从来不问他们的姓名。”
“那你现在肚里的一个呢?”
“嗯,我也说不准。那时我没有力气洗,所以常在街上。这无所谓。”
“再来杯酒吗?”
“一杯社松子苦艾酒。”她的手伸进行包,摸出一段黑雪茄烟蒂,点着了火。“你看上去运气不怎么好,”她说。“你卖掉过画吗?”
“没有,我不过刚刚开始。”
“你开始得太晚了一点吧。”
“我三十岁。”
“你看上去有四十岁。那你靠什么过话呢?”
“我弟弟寄给我一点钱。”
“嗯,那也不比洗衣服坏呀。”
“你和谁住在一起,克里斯经?”
“我们都住在我妈家。”
“她知道你上街吗?”
那女人大笑起来,但一点也不高兴。“他妈的,是她叫我去的,他一生就干这个。他就是那样生下我和我的兄弟。”
“你兄弟干什么?”
“他在屋里弄了个女人。他替她拉皮条。”
“那对你的五个孩子不会有好影响。”
“没有关系。有朝一日他们全会干这一行的。”
“都是甜酒在起作用,是吗,克里斯经?”
“我就是哭也没有用。我能再来一杯柱松子苦艾酒吗?你的手怎么搞的?黑了一大块。”
“烧伤的。”
“嗅,一定伤得厉害吧。”她温柔地捧起他的手。
“不,克里斯廷,没有什么。我是故意的。”
她放下他的手。“你一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没有朋友吗?”
“没有。我有兄弟,不过他在巴黎。”
“一个人感到寂寞了,是吗产
“对,克里斯廷,寂寞得发慌。”
“我也一样。所有的孩子都在家,还有母亲和兄弟。还有我找到的男人。但你却独自一个人生活,是吗?问题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有一个你真正喜欢的人。”
“你没有喜欢过谁吗,克里斯廷?”
“第一个家伙。我那时十六岁。他有钱。因为家庭关系,他没法跟我结婚。不过他给孩子抚养费。后来他死了,我被撇下,一个子儿也没有。”
“你几岁了?”
“三十,得不能再养孩子了。免费诊疗所的医生说,这一个孩子会送我的命。”
“如果你得到适当的医疗和护理,就不会的。”
“我到什么地方去疗理呀?没有一分钱的积蓄。免费诊疗所的医生们漠不关心,他们碰到的病妇太多了。”
“你没有办法凑点钱吗?”
“毫无办法,除非我一连几个月整夜在街上。但是,那比生孩子会更快地叫我送命。”
他们默默不语了一会儿。“你离开这儿后上哪儿呢,克里斯廷?”
“我整天怄在盆桶旁边,我来这儿喝一杯,因为累死了。他们也许给我一个半法郎,但要拖到星期六才给。我得有两法郎买吃的。我想,在找一个男人之前,该休息一下。”
“你答应我跟你去吗,克里斯廷?我很寂寞。我高兴跟你去。”
“当然可以。帮了我的忙。再说,你是好人。”
“我也喜欢你,克里斯廷。当你拿起我烧伤的手的时候……我记不清楚,那是多少日子以来,一个女人对我讲的第一句温柔的话。”
“真好笑。你长得不难看。样子蛮好。”
“我在爱情上就是运气不好。”
“呀,往往是那样,是吗?我能再来一杯杜松子苦艾酒吗?”
“听着,你和我不需要醉后行事。就把我能给的放进你的口袋。我很抱歉,为数不多。”
“我看你比我更需要钱。不管怎么,你能来。等你走了!我会再找一个家伙弄两法郎的。”
“不,请收下钱,我能给,我向朋友借了二十五法郎。”
“好吧,我们就走。”
在回家的路上,穿过一条条黑暗的街,他们从容自在地闲谈,就象老朋友一样。她把她的生活告诉他,对自己毫不同情,也毫无怨言。
“你当过模特儿,摆过姿势吗?”文森特问她。
“年轻的时候干过。”
“那么为什么不给我摆一下呢?我不能给你很多钱,甚至一天一法郎也不可能,不过,等我开始卖画后,我会给你两法郎一天,这比洗衣服强多了。”
“唁,我高兴的,我带上我的男孩,你可以画他,不用付钱。当你把我画腻了,你可以画我的母亲,她高兴常常赚点外快,她是打杂的零工。”
最后他们抵达她的家。那是一所租石砌成的平房,带一个院子。“你不会碰到谁,”克里斯廷说。“我的房间在前面。”
她住的是一间简陋的小房间,墙上的素色糊壁纸显出单调的灰色,就象夏尔丹的图画——文森特想。木地板上有一块擦鞋的棕垫,一块深红色的旧地毯。一个角落器放着一只普通的厨房用炉,另一个角落里是一口衣柜,当中是一张大床。那是一个真正的劳动妇女住家的内景。
文森特早晨醒来时,发觉并不孤单,在蒙俄的亮光中看到身旁有个人影儿,这使世界显得大为友好。痛苦和孤寂从他身上消失了,被一段深沉的安宁感所替代。
他在上午邮班中收到泰奥的信和附奇的一百法郎。泰奥在一日过后好几天方才能够寄出。他养出去,看到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在邻近的她的前院里拥上,便问她肯否来为他摆姿势,他给五十生丁。老妇人欣然答应。
在工作室里,他让她坐在烟囱和边上放着一把小茶壶的炉子分,衬着呆板的背景。他在寻求色调,老妇人的头都很有光彩和生气。他用不成熟的、过于讨好的格调,作了一张四分之三的水彩画。那妇人坐着的一角,处理得很柔和、平稳和多情。有一个时候,他感到很难,枯燥无味,容易画坏,现在得心应手了。他在纸上苦心经营,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感激克里斯廷为他所做的一切。缺乏爱情的生活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但不了他。
“情爱使人滑润,”他一边顺利而自在地画着,一边低声自语。“真奇怪,为什么米什莱老爹竟然从来没有提起呢。”
响起了敲门声。文森特请特斯蒂格先生过来。他的条纹裤笔挺,他的回头棕色皮鞋镜子一样晶亮,他的胡须剃得净光,他的头发在边上整齐地分开,他的衣领雪白,无懈可击。
特斯蒂格看到文森特有一个真正的工作室,并在努力作画,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喜欢看到年轻的艺术家们取得成功,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天职。但他要那种成功通过有条不紊的、预定的途径实现。他感到一个人最好先以惯常的方式方法努力,失败,然后再打破一切清规戒律,取得成功。对他来说,法规远比胜利来得重要。特斯蒂格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他期望人人都同样地善良和诚实。他不承认有这样的环境,它可以把恶变成喜,超度罪孽。把作品卖给古皮尔公司的画家们懂得:他们必须信守法规。如果他们违反这个高尚品行的指示,特斯蒂格就拒绝处理他们的作品,即便那可能是杰作。
“啊,文森特,”他说,“我真高兴,你竟然在作画。那就是我之所以喜欢拜访我的艺术家们的原因。”
“你跑那么多路来看我,实在过意不去,特斯蒂格先生。”
“没什么。你搬到这儿来以后,我就一直想来看看你的工作室。”
文森特望望床、桌、椅、炉子和画架。
“没有什么可看的。”
“别介意,努力干起来,很快就能拿出象样的东西来的。莫夫告诉我,你开始画水彩了,水彩画的销路很好,我一定能替你卖掉几张,你的兄弟也一定会的。”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先生。”
“你的精神似乎比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要好得多。”
“是呀,我生过病。但昨天晚上好了。”
他想到酒、社松于苦文酒和克里斯廷;如果特斯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