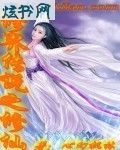林语堂自传-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先生,你到过云南吗?”我说:“没有。可是共产党这些年一直在中国,我这些年一直和他们打交道。我记得他们在长沙的所做所为。”在会场上,史沫特莱有意不再提这件事。我敢说,我在蒋委员长侍从室那些年,只是挂了个名儿,我并没向中央政府拿过一文钱;只是为拿护照方便一点儿而已。
我在自由中国漫游一番,回到美国,当时的情形,我自然明白。我一回去,在广播电台上我说:“现在在重庆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们正在掳胳膊,挽袖子,为现代的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华尔舍(Richard J。 Walsh)一个严厉的警告,告诉我不可以,也不应当再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不利的环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场失利的战役,我只是战场上的一名伤兵,对这事并不很放在心上。
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个杰出的作家是:
托玛斯·曼(Thomas Mann)。他由日内瓦回来之后,我在纽约的国际笔会上遇见过他。他说英文,他的英文是复杂的德文结构,没法儿听,也没法儿懂。当时还有Eve Curie和另外几个人,大家一同在讲演人的台子上。我讲的是明朝的太监魏忠贤,他在世之时各县就给他立生祠。在与赛珍珠同坐的台子上,有一个客人问我:“太监是什么?”
我和Carl Van Doren也见过多次,他对我很和善。他的妻子Irita,后来与Wendell Wilkie相交往,还有他哥哥Mark Van Doren(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最喜爱活泼愉快斯文典雅的学者Irwin Ed…man,他是美国的哲学家,他的英文极为简练。他搜集了些很长的留声机片子,那是他业余的嗜好。
罗素,虽然年事已高,还机敏灵活,目光闪亮。我记得是在朋友的公寓住宅里遇见他的。不幸的是,他娶了一个美国菲列得尔菲亚城的小姐(大概是他第三个,也许是第四个妻子),这位妻子太以她的“爵士罗素”为荣而时时炫耀。每逢说话,她就一个人包办。很多朋友愿向罗素提问题,这位太太便插嘴代答。大家感到兴趣的是听罗素说话,没人喜欢听她的。所以朋友们见面也是人人感到失望。
在Knopf Sartre夫人的公寓住宅里和萨特(J。 P。 Sartre)相见,也是件新鲜事。萨特坐在一把椅子里,我们大家都坐在地板上。我们大家都很轻松。他的英文说得很好。他的措词用字极其精确,犀利而动人,但是有时他会前言不搭后语。我能想象到他在Raspail大道,一边喝咖啡,一边和许多崇拜他的“自觉存在论派”的小姐们闲话的神情。这些自觉存在论者创始了不擦口红不抹粉的时尚。这种时尚后来被观光的嬉皮游客所采取,就成了美国现代文化的特色。他们认为万事不如在佛罗伦斯(Horence)或是在罗马仰身而卧,或是伏卧在地,阻碍通往大教堂的道路,使人无法通过。
萨特否认人生有何意义,但却力言我们为何而生活,以何为目的,全由我们自己决定。他的主张也不完全是否定一切。
由于赛珍珠和她丈夫理查德·华尔舍,我才写成并且出版了我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本书之推广销售也是仰赖他们夫妇。我们常到他们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去探望。我太太翠凤往往用国语和赛珍珠交谈,告诉她中国过去的事情。赛珍珠把《水浒传》翻成英文时,并不是看着原书英译,而是听别人读给她,而边听边译的,这种译法我很佩服。就像林琴南不通英文,译司哥德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和《天方夜谭》时的情形一样。赛珍珠对收养美国父亲韩国母亲生的孩子,很感兴趣,后来又收养印度婴儿。她有一个农场养牛。收养婴儿与扣减所得税有关系。
赛珍珠懂中国话,说得也流利,她父亲曾在中国做传教士,她是随同她父亲Knickerbocker在中国生活,先是在安徽,后来到南京,她算是在中国长大的。后来她嫁给Lossing Buck教授,所以她对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的风俗,还有相当的了解。但是我发明中文打字机,用了我十万多美金,我穷到分文不名。我必须要借钱度日,那时我看见了人情的改变,世态的炎凉。人对我不那么殷勤有礼了。在那种情形下,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后来,我要到南洋大学去做校长,给赛珍珠的丈夫打了一个电报,告诉他我将离美去就新职。他连麻烦一下回个电报也不肯。我二人的交情可以说情断义尽了。我决定就此绝交。那是在我出版了抗战游记《枕戈待旦》(The Vgil of a Nation)之后。在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向我接洽,说我写什么他们都愿出版之时,赛珍珠这位丈夫正在出版我的《朱门》(Vermilion Gate)。我断了二十年的交情,写出了小说《奇岛》(The Unexpected Island),这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在外国我出书,John Day出版公司一般都是保持百分之五十,但经朋友Hank Holzer夫妇帮助,我把一切权利都收了回来。有一次赛珍珠去看我,其实主要是看我何以度日,我们的友情没再恢复。
赛珍珠急于和共产党搭线,好和别人共同“前进”,她从未到台湾来过,我想台湾也不欢迎她。在一九七二年,她想办护照前往中国大陆去看看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但是共产党政权知道她若与中国农民交谈,会对中国大陆了解得太多,拒绝她前往。此后不久她就去世了。赛珍珠毕竟还是保持中立的态度,她并不是共产党员。
第十二章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自然的节奏之中有一条规律,就是由童年,青年,老年,衰颓,以至死亡,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身体。在安然轻松的进入老年之时,也有一种美。我常引用的话之中,有一句我常说的,就是“秋季之歌”。
我曾经写过在安然轻松之下进入老境的情调儿。下面就是我对“早秋精神”说的话。
在我们的生活里,有那么一段时光,个人如此,国家亦复如此,在此一段时光之中,我们充满了早秋精神,这时,翠绿与金黄相混,悲伤与喜悦相杂,希望与回忆相间。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一段时光,这时,青春的天真成了记忆,夏日茂盛的回音,在空中还隐约可闻;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不是如何奋斗操劳,而是如何享受自己有的那宝贵的刹那;不是如何去虚掷精力,而是如何储存这股精力以备寒冬之用。这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到达一个地点,已经安定下来,已经战到自己心中想望的东西。这时,感觉到已经有所获得,和以往的堂皇茂盛相比,是可贵而微小,虽微小而毕竟不失为自己的收获,犹如秋日的树林里,虽然没有夏日的茂盛葱茏,但是所据有的却能经时而历久。
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其金黄色的丰富并不表示春季纯洁的无知,也不表示夏季强盛的威力,而是表示老年的成熟与蔼然可亲的智慧。生活的秋季,知道生命上的极限而感到满足。因为知道生命上的极限,在丰富的经验之下,才有色调儿的调谐,其丰富永不可及,其绿色表示生命与力量,其橘色表示金黄的满足,其紫色表示顺天知命与死亡。月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日的余晖照上秋日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的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别的眼泪。因为是早秋的精神之歌,所以有宁静,有智慧,有成熟的精神,向忧愁微笑,向欢乐爽快的微风赞美。对早秋的精神的赞美,莫过于辛弃疾的那首《丑奴儿》: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我自己认为很有福气,活到这么大年纪。我同代好多了不起的人物,已早登鬼录。不管人怎么说,活到八十,九十的人,毕竟是少数。胡适之,梅贻琦,蒋梦麟,顾孟余,都已经走了。史塔林,希特勒,邱吉尔,戴高乐,也都没了。那又有什么关系?至于我,我要尽量注意养生之道,至少再活十年。这个宝贵的人生,竟美到不可言喻,人人都愿一直活下去。但是冷静一想,我们立刻知道,生命就像风前之烛。在生命这方面,人人平等,无分贫富,无论贵贱,这弥补了民主理想的不足。我们的子孙也长大了。他们都有自己的日子过,各自过自己的生活,消磨自己的生命,在已然改变了的环境中,在永远变化不停的世界上。也许在世界过多的人口发生爆炸之前,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中,成百万的人还要死亡。若与那样的剧变相比,现在这个世界还是个太平盛世呢。
若使那个灾难不来,人必须有先见,预做妥善的安排。
每个人回顾他一生,也许会觉得自己一生所做所为已然成功,也许以为还不够好。在老年到来之时,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权休息,可以安闲度日,可以与儿孙,在亲近的家族里,享天伦之乐,享受人中至善的果实了。
我算是有造化,有这些孩子,孝顺而亲爱,谁都聪明解事,善尽职责。孙儿,侄子,侄女,可以说是“儿孙绕膝”了,我也觉得有这样孩子,我颇有脸面。政治对我并不太重要。朋友越来越少,好多已然作古。即使和我们最称莫逆的,也不能和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一生的作为,会留在我们身后。世人的毁誉,不啻风马牛,也毫不相干了。无论如何,紧张已经解除,担当重任的精力已经减弱了。即使我再编一本汉英字典,也不会有人付我稿费的。那本《当代汉英词典》之完成,并不比降低血压更重要,也比不上平稳的心电图。我为那本汉英字典,真是忙得可以。
我一写完那好几百万字的巨册最后一行时,那最后一行便成为我脚步走过的一条踪迹。那时我有初步心脏病的发作,医生告诉我要静养两个月。
第十三章 精查清点
我必须清查一下儿我的作品。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都可以传世。我写过几本好书,就是:《苏东坡传》,《庄子》;还有我对中国看法的几本书,是《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还有七本小说,尤其是那三部曲:《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因为过去我一直在美国多年,这些书还没译成中文。但是上海和香港的出版商擅自翻译出版,所出的书之中,有的根本不是我写的,也有的不是我翻译的,未得我允许,就硬归做我的,其中不管有删节或译与未译,这类书至少有十几种。
在冬天,我打算把我用中文写的文字印行一个可靠的版本。
1。无所不谈集——所有我写的分做第一,第二,和最后三集。
2。林语堂选集——(两卷)民国二十四年以前的中文写作,包括在《语丝》,《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内写的文章。
3。平心论高鹗——是对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为伪作的回答,民国五十五年印行,文星出版。原登《传记文学》杂志。
英文著作:
1。Kaiming English Grammar(开明英文法)
民国十八年,上海开明书店印。
2。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Narrative Essays(谢冰莹原著《女兵自传》)
民国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3。The Little Critic(一,二集,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
4。Confucius Saw Nancy and Other Translations(子见南子及其他译文)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版。
5。A Nun of Taishan and Other Translations(老残游记续集及其他译文)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商务版。
以下在美国出版。在伦敦则由William Heine…mann出版。
6。A History of Chinese Press and Public Oninion in China(中国新闻舆论史)
一九三六年由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
7。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
一九三五年由美国John Day出版。
一九三六年二版由Reynal Hitchcock出版。
8。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
一九三七年由John Day出版。
9。The Wisdon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
一九三八年由Random House出版。
10。Moment in Peking(小说,京华烟云)
一九三八年由John Day出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