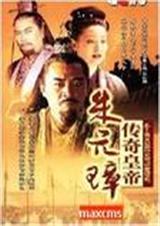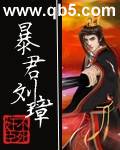朱元璋-第4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相信你此言是出自内心。”刘基道,“只怕到后来,你自己也做不了你自己的主了。”
朱元璋问:“此话怎讲?”
刘基说:“不说了。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说也无益。”他看了宋濂一眼,问:“想给我个什么官呀?我办事,是喜欢丑话说在头里的。”
朱元璋显得很费踌躇,说:“我深知先生是清高的清流大师,向来不把官位看在眼里。”
“不,不,”刘基故意说:“我是凡人,岂有不贪图荣华富贵之理?”
朱元璋沉了一下,说:“我决定不给先生任何官职,因为多大的官你也不稀罕,都是对你人格的亵渎。我终生称你为先生,朝夕请教,先生以为如何?”
“此话当真?”刘基乐了。
“当然,只要先生无异议。”朱元璋说。
他们的对话令胡大海大为惊奇、纳罕,有这样傻的人吗?不要名也不要利?他悄悄地问冯国用,冯国用告诉他,这样的高士,是不能用世俗眼光看待的。胡大海仍是摇头,他无法理解,这样的清高太不实惠了。
刘基说:“这样最好。日后你给我官职,我可不要,你不要感到没面子。”
朱元璋说:“一言为定。”
“宋濂呢?”刘基又问。
宋濂忙说,他更不宜为官了,也没资格当先生,他当个幕中食客,吃一碗闲饭足矣。
刘基说:“你呀,就重操旧业,当教书先生,朱平章的孩子归你教了。”
“太好了,”朱元璋说,“我没念过多少书,从前是刘先生的老师佛性大师教过我几天,今后要拜宋先生为师了。”
宋濂说:“这可不敢当。”
朱元璋说:“浙西四贤我已有其二了,另外两位,还望先生为我请到。我走前,已令人在金陵修了礼贤馆,是专为你们预备的,希望择日启程。”
刘基说:“章溢、叶琛包在我身上就是了。”
李善长家又到了开晚饭的时候。
胡惟庸又像每次一样,亲口尝了河豚之后立在一旁等待。李善长抿了一口酒,突然说:“你坐下。”
胡惟庸说:“我不敢坐。”
李善长说:“你也是个读书人,不要太折了身份。”
胡惟庸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是读书人?胡三说的吗?他告了声罪过,却只坐了椅子边儿。
李善长说:“从明天起,我不能再用你下厨了。”
胡惟庸吓得站起来,极为不安,不知是菜烧得不可口,还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李善长和善地说,他用一个举过乡试、中过江南第一名解元的才子给他来当厨子,又要冒性命之险尝毒,于心不忍。
胡惟庸大有良马遇伯乐之喜,眼里放出亮光来:“这事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起过,大人怎么知道的?”
李善长也是偶然得知。前几天他奉命清理江南贡院,在碑林石碑上发现了胡惟庸中解元的名字,先时还以为重名,随后又在卷库里翻到了他的卷子,文章写得好,可圈可点。
胡惟庸说:“谢谢大人夸奖。”心里有得见天日的感觉。
李善长说:“你是当地有名的刀笔,最擅长写讼状,是吧?”
胡惟庸脸红了,刀笔吏并不是褒义,他说是偶亦为之,都是气不公,才代人打打官司,哪敢称刀笔。
李善长笑道:“你在至正十二年一纸状子,杀了三县令、二平章、一左丞,轰动江南,你还不够刀笔吗?”
胡惟庸说:“大人把我胡某人说成讼棍了!”
李善长说:“那倒不是。以你的才学,是可以进士及第的,你为什么半途而废?熏没有进京会试?”
胡惟庸说,天下这么乱,即使成了两榜进士又能怎么样?倒不如看准时机求进取。
“聪明人。”他的选择已暗合了李善长的心志,他不也有类似经历吗?李善长知道他想走终南捷径,于是煞费苦心,来给自己当烧河豚的厨子。
胡惟庸也不否认,他听说大人爱才、广纳贤人,他虽是无名小辈,也想求得提携,便找了这么个差使,不然怎么可能接近声名显赫的李善长。
李善长叹道:“难为你一片苦心了。我想过了,不能让你久居人下。你可先在我这里帮办点文牍上的事,有机会荐你到平章那里去,那里才有你施展才干的机会。”他认为,朱元璋一定会看中胡惟庸的才干、学识和机敏的。
胡惟庸感激涕零地跪下了:“您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李善长拉他起来。胡惟庸指着盘子里的河豚说:“可以吃了,没事的。”
李善长玩笑地说:“我当一回伯乐,却再也吃不到这么美味的河豚了。”
“我还可以来烧,”胡惟庸说,“不然,我把手艺传给我的同乡胡三。”
李善长笑了:“也好。”
朱元璋的平章衙门公堂里惟一悬挂的条幅,就是马秀英所题的“能屈者能伸”,已裱好了。他的桌子上、背后屏风上到处贴满了纸条,他伏在案上写着,冷丁想起什么,便站起来浏览屏风上的纸条。
朱元璋叫:“来人!”
上来一个听差,朱元璋把写好的东西交给他,叫他差人飞马快递浙江胡大海,叫他先不要攻打方国珍。
这人下去后,朱元璋又看桌角粘的纸条,马上又叫人:“来人!”
又上来一个书办,朱元璋吩咐把太平府收税的底册子拿来,谁叫他们又加了丁税?他把一个札子递过去,勒令太平知府马上把丁税免掉。
这个书办下去后,朱元璋又看了一张字条,再次唤人:“来人。”
又上来个书办,朱元璋问应天府修建学堂的钱到了没有?
书办说:“还没到,我昨天去催了。”
朱元璋让他告诉陶安,三天之内不能开学,让他把大印送回来。
书办说:“是。”
朱元璋自语:“没有人才,国家怎么能兴旺?”
书办答应着下去了。
朱元璋又开始看粘在桌子上的纸条,揭下一张,又向阶下叫:“来人啊。”
半天无人应答。廊下的侍从快叫他指使光了。朱元璋站起身向外叫:“有人吗?”
这才跑上一个人来,是胡惟庸。
朱元璋觉得面生,就问:“你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胡惟庸恭敬地禀报,说自己叫胡惟庸,是新来的奏差,是李善长李大人荐来的。
朱元璋问他是什么地方人?
“原籍吴县,”胡惟庸说,“后来搬到宁国。”
“那你对府县赋税一定很知道了?”朱元璋说。
“知道一点。”胡惟庸说。
朱元璋百思不解,他在所占区域内不断减税,可百姓仍然不肯交税,是何道理?
胡惟庸不经思索便对答如流,战乱经年不息,土地多被豪绅大户兼并,农民无地,想缴税也缴不着,而有地的大户又与官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瞒报土地,这就形成了有钱的不用交税,穷人没地没钱交税的局面。穷人实际上得不到减税赋的好处。
朱元璋问:“那你说怎么办?”
胡惟庸献计,丈量土地,把瞒产的大户惩治了,让世代盼地的农民有地种,天下粮仓有粮了,国家也有税收了。向来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而不是损有余而奉不足,天下不会太平。
朱元璋大为惊讶,说:“你谈吐不俗啊!你既然这样体察民情,我派你到县里去当个县令,按你说的办法去做,如何?”
胡惟庸并无受宠若惊的表示,但当县令总比当奏差强,便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朱元璋又站到了屏风前面,那上面有密密麻麻的人名。他找到了宁国县字样,勾了下面一个人名,把胡惟庸三个字填上了。他说:“就派你回你家乡宁国去当县令,回头我让李善长给你办理。”
胡惟庸说:“谢平章大人。”
长江边上码头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朱元璋亲率文武百官来迎接刘基等人。
一条官船拢岸,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四人站在甲板上,没等船停稳,朱元璋便带李善长等人踏上跳板。
乐声大作,列成方阵的舞女翩翩起舞,变幻着队形。在乐声中,人们簇拥着四贤人分别上了四乘大轿。
朱元璋一直把浙西四贤送到了为他们而修葺一新的礼贤馆。
在悬挂着礼贤馆泥金巨匾的大门前,刘基惊慌地让轿夫停下,他跳了下来,心里很不安,他认出这是南京有名的夫子庙,是供奉大成先师孔子的圣殿,朱元璋这人怎么想的,怎么让他住在孔子的享殿?
但朱元璋的解释听起来也很合乎逻辑。他说,刘伯温等人就是师承孔夫子学问的薪火传人,住在这里,可随时接受孔圣人的灵气,也可在孔圣人跟前做学问,这是大敬,而非大不敬。
刘基与同伴们相互望望,便也不再争辩。
朱元璋仰望着门前“礼贤馆”三个大字,刘基问朱元璋,这是谁的字?
朱元璋开玩笑地说:“这可是大书法家的字,一字斗金,请先生猜猜。”
刘基看看宋濂,问:“这字如何?”
宋濂不夸字好,只笑道:“挺有个性。”
“个性谈不上。”刘基说,只有霸气。此人够不上书法家,再临十年帖也许有希望。
宋濂发现朱元璋脸色已不太好看,便捅了刘基一下,悄悄提示他别再贬了,有可能是朱平章的手笔。
刘基早猜到出自朱元璋之手了,他不但不留面子,反倒扭头问朱元璋:“真的是你写的吗?”
朱元璋不自然地笑道:“献丑了,因为是礼贤馆,大家都不敢题,我便不揣冒昧题了。”
刘基哈哈大笑:“你不必附庸风雅,这样的字,今后千万不要各处去题,以免贻笑大方。”
这话令在场的人大为震惊,人们无法想像,这话他怎么能说出口,朱元璋会是什么感受?李善长不断地看朱元璋脸色,陶安、李习、杨宪等人也都惴惴不安,不知怎样收场。
朱元璋干笑着说:“是,很是。”他心里虽然反感,也不好在这请贤的好日子里发作呀。
不识时务的刘基仍不算完:“对于你来说,人们只看你的文治武功。倘你不留字,说不定人们以为你书法不错,你留了,不恰恰倒了胃口吗?”
朱元璋已经装听不见,扭头与章溢搭话了。
冯国胜对冯国用道:“这刘伯温如此讨厌,主公能容忍他吗?”
冯国用道:“那要看他有无真本事了。”
他们一行人沿着青石甬道走入柏树森森的庭院,依次通过五道大门,但见上下两层的魁文阁高耸松柏之上,油饰一新,左面是碑廊,大成殿里尊奉着孔圣人的塑像,旁边是七十二弟子像,巨匾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题的“万世师表”四个大字。
他们在第二进院子的天井停住,这里有凉亭和几株大柏树。
刘基在这万人敬仰的圣地,又一次不安起来。朱元璋却执意不肯为他们另择居所。
朱元璋又恢复了自信的常态:“我把四位大贤请到孔圣人的所在朝夕供奉,不正应当吗?”
朱元璋说刘基未免把孔圣人过于神化了,他说孔夫子的后世弟子多为官,《论语》成了升官的书。他认为孔子比孟子强,孟子有些话莫名其妙,是混账话。
人们不知道他为何要贬孟子,也没人敢问。
刘基却对孔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孔夫子一生并未认真当过官,他的《论语》也不过是和弟子们坐而论道的记录。他就很怀疑,如果宋朝的赵普真的是用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岂不是说,背熟了《论语》,人人都可以得天下吗?可见赵普没有讲真话。
这话倒对了朱元璋的脾气,他说:“太对了,我就曾试过在《论语》里找治国之方,可是没有找到。做人嘛,不妨学学《论语》。”
第三十章
一主一仆,出于同一师门,为得到刘伯温,只得为苏坦妹立碑,实则是朱元璋的耻辱柱。后花园里出现鬼影,明知鬼在何处,却又不能捉鬼,谁解苦衷?
朱元璋与四贤以及随侍官员来到魁文阁二楼大厅坐定,朱元璋先向李善长等说:“刘伯温先生是天下大贤,我们能请来,实属不易,今后不要用繁文缛节来打扰他们,我连官职都不敢委屈他,永远称先生。”
刘基说:“端人饭碗,总不能什么也不干。我们在舟中试着草拟了治世十八策,请过过目,不知有用否。”
朱元璋接过来,说:“这一定是良策,回头我细细地揣摩。”
刘基看到门口旗上有“大宋小明王”字样,很不以为然,就说:“你们迄今为止还用着小明王龙凤年号,不知想用到何时?”
朱元璋向他解释,虽用小明王的年号,我们的事,他并不管,这总比树敌为好,如果这个时候废了龙凤年号,反目为仇,便在北方又多了一个劲敌。
刘基认为既是权宜之计,就更不该在各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