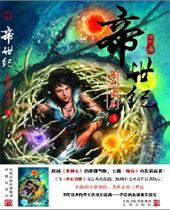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厨房里突然淫邪地捏紧她的膀子。她“哇”的一声,没命地跑出了店门。
到哪里去呢?找朋友去哭一场?眼泪不能当饭吃。她想起了一个和颜悦色的女教授。女教授曾一再表示过,愿意尽力帮助她解决困难。白薇满怀希望地到了女教授的家。女教授非常热情,待她如上宾,并柔声柔气地对她说:“你是我很看重的一个中国女学生,在东京,你没有亲人,需要什么,尽管向我说好了。”
白薇说:“我最近生活十分困难,想向您借二十元钱,两个月后一定奉还。”
话音未落,女教授丰腴慈爱的笑脸突然变成一副丧门神的模样,并恶声恶气地骂道:“你这样专门靠借钱生活,简直不是一个正经女子所走的路。正经女子在未嫁以前,要顺从父母,也只能仅仅用父母的钱;出嫁以后,要忠贞于夫君,也不能欺骗夫君去用他人的钱……现在都会的女子坏得很,却不料你这个支那的姑娘也学到了坏女人的行径……"
听了这些话,白薇不屑解释,拔腿就跑。她满面泪痕。她不明白,为什么人穷了,就什么冤枉,什么脏水都可以往身上泼。尤其是和黑暗社会抗争的孤单贫穷女子,无论心地怎样清白,人格怎样高尚,也不会被人理解,只会无理地受摧残,受虐待。生机在哪里?这可诅咒的世界!可诅咒的人心!可诅咒的金钱!可诅咒的无价值的交际!
写信给湖南的父亲,父亲责怪她在海外挥金如土;写信给下南洋的恋人,恋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骂她无能。那么去投降父亲,投降封建礼教,乖乖结束留学生活回国走父亲为自己安排好的路?不!不能!
在萧瑟如寒林的屋子里,她坐卧不宁。白天她苦苦躲在家里看借来的书,晚上饥火总要把她逼到街上去。夜色沉沉,灯光昏迷,她的心绪恶劣透顶。这个冷冰冰如铁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铁轨像蛇似的曲转延伸……“躺上去,白薇!”一个声音催促着,“双眼一闭,火车呜的一声,你就不会再有穷困和屈辱。躺上去!还等什么!”
“不,你要再想想。就这样去死?做异国的孤鬼?白薇,你不能丧失生的勇气,不是你自己几次鬼门关里打回来的么?要轻生?背叛自己?真可耻!”
她迈上铁轨的脚下来又上去,上去又下来……最后,她一下子瘫坐在铁轨旁,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
东方发白,慢慢地射出了几道金光,冉冉升起了一个通红的火球。她慢慢站起来,向着苍天起誓:“我不要死,我要和世界上这一切恶毒宣战!我要革命!要让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她恨不得立刻飞到广东去,学骑马,学开枪,打前锋!赶快推倒封建势力,推倒资本主义势力,还要把现在腐败的恶劣人的人心,统统送到北海、鄂霍次克海去喂鱼。
四
南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革命的热潮,民众的激情,放射着巨大的磁力。
白薇在日本,虽然又补上了官费,还可以进研究班多读两年,但回国参加革命的热望,使她再也不能安心坐在教室里了。1926年初冬,身着西装、风度潇洒的白薇,从长崎登上美国的远洋轮回国。海水拍击着船帮,为远归的游子演奏进行曲。充当下女,流浪街头,狂热的初恋,勤奋的学习……异国九年的往事,已留在身后。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着眼于未来吧!她头脑里索绕着美丽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作家们热情地接待了她。成仿吾、郁达夫、王独清、郑伯奇成了她新结识的好友,成仿吾还像老大哥一样,教她读马列主义的书。
十几年没有见到父母了,怀乡思亲之心油然而生,催促着她跋涉了八天,翻过高耸的大庾岭,回到了湖南资兴。秀流的水还是那么碧绿。可爱的家乡却由于连年军阀争战,官兵土匪的蹂躏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像个大病一场的女子,改变了娇美的容颜。
进了家门,她想拥抱母亲,却不料被母亲推出五六尺远。母亲看着眼前身材修长、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的“洋”女儿,困惑而气愤地摇了摇头,接着便嚎哭起来。当天,她就被打发到了舅舅家。
父亲一直躲着不见面,等女儿一走,马上就出来了。两位老人赶紧打开女儿的箱子,翻来翻去,没有搜到一件“茶花女”式的服装和首饰,只抄出一些简素的旧衣、书籍和她写的一些诗及诗剧《琳丽》。
父亲细细读了她的作品,觉得女儿是个“未来人”,即革命人,很有出息。二老悲喜交集,深悔多年误会、薄待了女儿,错听谣传。于是马上从舅舅那里接她回了家。父亲用慈爱的目光倾泻自己的感情。母亲特地杀了只黄母鸡,用甜酒汁蒸给女儿吃。妹妹把父亲抄检箱子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她。
父母同情女儿的境遇,考虑了女儿的未来,帮助她解除了同李家的婚姻关系。乡亲们希望她留下来,为家乡办学,培育人材。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牢牢牵挂着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她早就幻想当一名女兵学习射击、骑马、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亲身讨伐糟踏祖国山河、蹂躏同胞、卖国求荣的北方军阀。她怀着满腔热血,辞谢了父老们的盛情,匆匆投奔革命中心武汉,这是1927年春天。
到了武昌,旅费快用光了,她住在一间很小旅馆里。白天用白开水送下一个面包,晚上臭虫成群结伙吸她的血。她在街上徘徊了几天,终于碰上了一个留日时期的补习学校的同学殷德祥。经殷介绍,她到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国际编译局担任日语翻译。
她庆幸自己这么顺利就迈进了革命队伍,每天努力译着日本报纸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报导和评论,供高级首脑们参考。业余时间抓紧写作,有时参加军民演出活动。过了不久,她又兼任武昌中山大学讲师,教授日语、动物、植物等科。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她的意料。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
4月下旬至5月下旬,武汉军队的主力北伐。自薇穿着军装,脚踏一双长统皮靴,站在职员队列里。
大会主持人慷慨陈词,动员大家武装起来,完成北伐,打退川军,打倒南京政府,统一中国。
白薇惊奇地发现,不论是在台上演说的,还是在台下听着的,越是职位高的,越是踊跃兴奋,越是对革命热情。她想:“他们那热烈滔滔的演说,有的犹如站在柏林的革命海军围住营前的斯巴达克斯团人领袖卢森堡;他们那一阵阵狂呼怒吼的口号,有些像巴士底狱的呼声冲霄破汉,他们那矫拔的精神,俨然个个都是站在群众面前的指挥;他们那觉悟的毅力,真个每人都以革命的铁血儿自命的。”
她越凝视这些纠纠雄伟的狂热奔腾的人物,“越感觉自己是一根茫茫飘荡的羽毛,算不得一个人……直像一砂石比泰山。”但是,她总有些不相信这天的光景是事实,以为“自己在做梦”。
不久,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之,汪精卫之流就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清洗”和屠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一线光明瞬息即逝。白薇真的做了一场“梦”。
她不愿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辞去编译局和中山大学的职务,力拒同志和机关的挽留,愤然到了上海。到上海,她想演电影。创造社的朋友们劝她写文章,并把她的名字列入《创造月刊》的执笔名单上。创造社对她的影响很大。帮助白薇迅速成长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她第一次见鲁迅,是杨骚带她去的。
1927年10月末,一个晴朗的午后。忽然房东奶奶喊着白薇的名字,告诉她来了客人。她从窗口向外一看,啊?竟是自己深深爱过的、阔别了三年的男朋友杨骚。蛰伏在心底的爱情,刹那间滚沸了。他走进她的房间,看见里面一张行军床,一张桌椅外,只挂着一张他绘的画,桌子上的镜子和相片,也都是他的东西。又看到白薇白净秀美、线条柔和的脸庞放着光彩,一双深情的眼睛,爱恋地注视着自己。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此,他常来看她,要求恢复恋爱关系。在白薇,虽然一想到他对她的折磨不免有些恐惧,但,以往的爱,确实太深氏
他们终于决定搬在一起,像好朋友似的,一个住前楼,一个住亭子间。中间的过道,摆一张吃饭的圆桌和两张圆凳,共同使用。他们共同买菜烧饭,吃饭的时候,两人时常握着手有说有笑。在这里,他们各自努力自修和写作,杨骚写出不少诗、戏剧,还翻译了一些作品。也就在这个时候,经杨骚介绍,白薇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创造社和大阳社一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白薇由于偏爱创造社,思想上也曾和鲁迅不接近。加上她“不可攀名人巨柱的怪癖”,所以又迟迟不想同鲁迅见面。后来虽去鲁迅家送稿,但每次都是到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跑了。鲁迅曾玩笑地和人说:“白薇怕我吃掉她。”鲁迅不以创造社的对立为嫌,像对许多青年作家一样,对白薇非常关心和器重。
《打出幽灵塔》是个古典浪漫写实的悲剧,描写了第一次革命战争中,一个土豪家庭的分裂。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它向那些沉睡在家庭中做傀儡的不幸妇女们,喊出了赶快觉醒的呼声。鲁迅将白薇这部作品在《奔流》创刊号上刊登。她的名字出现在郁达夫、柔石、冯雪峰等大手笔之列,从而成了当时“文坛上的第一流人物”。
鲁迅主编的另一份杂志《语丝》,还刊登了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受难》。这个寓意深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剧本,通篇都在痛斥着反革命两面派。
“你阳称和某某伟人一致北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彻底的革命;阴则昼夜想方设法,将要怎样去残杀同类,怎样地去剥夺国力,结局务必要达到狡兔死,走狗烹,给你一个人无忧无虑地做军阀以上的帝王!”
“你做恶就索性做恶魔也罢,但表面上要做伪善的君子,暗地里全是丑恶,当个无耻的革命叛徒,你最会借别人最善最大的主义,并且借些最美的名目,来做你去吃人去出风头的利器!你根本就不懂得革命是什么,你本身就是革命者的仇敌!”
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言辞,当然要戳痛一些人的心。国民党政府为这个剧本警告了《语丝》。
白薇开始试写长篇小说,取名《炸弹与征鸟》。它同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一对姐妹参加革命前后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再现出大革命时期形形色色的事件和人物,反映了作者对革命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积极态度。白薇认为自己写的不过是些用热烈感情把直感编排起来的记录,结构和修辞都不讲究,不想拿去发表,更缺乏继续写下去的勇气。杨骚替她把稿子送给鲁迅,回来之后高兴地对她说:“鲁迅先生说你写得好,你继续写下去罢,他的杂志上可以连载你的小说。”
“连载?”这两个字给了她多大的勇气啊!继而她又担心地问杨骚:“我的句子简直写不顺,又不懂结构,怎么办?”“我也这么说,你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句子,请他帮你改改。鲁迅却说,修改它做什么,那正是她的别有风格。假如什么文章都由我修改,那整个杂志的文章,只有我独一的风格了。”听了杨骚的转述,她才放心大胆地把这个长篇写下去。果然,鲁迅对她的作品,除了错字或生硬的句子略有改动,其他均未随意涂改。鲁迅尊重作者的精神,大大壮了她的胆气。接着,她又把长诗《春笋之歌》拿给了鲁迅。
白薇终于见到了鲁迅。那天,杨骚带着她刚到楼梯脚,她又想跑。不料鲁迅已在楼口亲切地招呼了:“白薇,请上楼来呀,上来吧!”她走进他的书房,微微低着头,不敢看鲁迅。鲁迅温和地给她扇风,拿出许多书画给她看,还同她开玩笑说:“有人说你像仙女,我看也是凡人。”拘束立刻打消了。她这才看清楚,“他原是我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一股敬爱的心,陡然涌上心头。之后,在《奔流》的餐席上,在“左联”,在内山书店,她常和鲁迅见面。有时她也到鲁迅家里,鲁迅总是对她温和诚恳,说话含着微笑。
正由于受创造社和鲁迅的影响,白薇走上了革命的文学道路,成为“左联”和“左翼剧联”的早期成员。不顾特务盯梢和敌人搜查的迫害,她积极参加活动,掩护革命同志,讨论文艺问题,深入群众,热心做宣传辅导工作,尤其是妇女工作。一些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