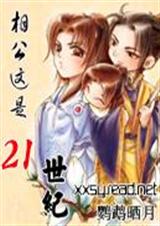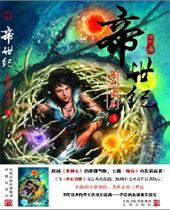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辆,掩藏着黑暗的僻静胡同里。懦弱的张顺,“这时忽然勇敢起来,他毫不胆怯地实行路劫了。不过劫的对象不是别的人,而就是他自己,他的衣服,一件件地用自己的手剥了下来,这时刺骨的凛寒,已经使他招架不住而战栗了,可是那英雄般的决心,是毫未动摇的。”他用修脚刀疯狂地向自己的头颈和手背等地方胡乱划去,计划完成之后,凯旋似的奔向大街,边跑边喊:“捉强盗呀!捉强盗呀!”他被人群围起,尽管流着泪叙述其遭难,但没有人施舍他,希望破灭了。最后,在署长的反复桔问下,张惶失措的张顺,只得照实招来,终被从严法办。
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悲剧。读后,人们并不想笑,而是想哭。张顺不忍农村的悲苦和压迫当了兵,父亲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到城市谋生。张顺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完全是被黑暗现实压迫的结果。
以上的短篇小说,作者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生活的。每篇结尾作者都未把故事写得山穷水尽,也毫不发挥,一切弦外之音,篇外之意,读者均可自己想象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读者可以自得结果。除《女性》以外的三篇小说,是描写下层普通人物命运的作品,这在沉樱的创作中,就篇幅而言,不占主导地位,但就其精神而言,是难得的,在沉樱的创作思想上,却占着重要地位。
尽管沉樱一再对我说,她的小说创作不多,内容不新颖;但我认为,这些作品毕竟是在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出自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之手,其中一些作品毕竟表现了她对生活的感受、砚察、希望、追求以及爱憎,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人物毕竟带着历史流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烙印,即使按沉樱的说法,把那些小说看成“历史资料”,也是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关于她的早期小说,虽不是她成熟时期的作品,但历史应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的作品毕竟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
五
不知为什么,1931年初,沉樱和马彦样离了婚。接着,她到了北京,认识了知识广博、才华横溢的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他学习上肯下苦功,翻译上一丝不苟、反复推敲的精神,使沉樱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她到过日本,目的在于学习日本文学。在那里,她游历了不少地方,写下了《在日本过年》等散文。翌年回国,与梁宗岱在天津结婚。梁在南开大学任教授,她闲居家中,偶有所作。
抗战八年,她蛰居重庆,先在北碚,后移南岸,曾和女作家赵清阁亲密为邻。这时期,她在乡下得到了英文《伊索寓言》和美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当时书少,就反复读,英文的阅读能力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先是以读为乐,后来试着翻译,希望将美的英文变成美的中文。那时她写作极少。但散文创作的代表作《春的声音》、《我们的海》却是被赵清阁逼出来的。
抗战的胜利,使她感到一种民族感情的解放。她兴高采烈地到了古都开封。1946年,在上海的赵清阁介绍她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之后,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国文,还在图书馆工作(在那里,她看了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直到离开大陆。
这十年来,对沉樱来说,像一块不毛之地,创作上几乎没有收获。但她是一位酷爱读书的人,除了家务,她的生命浸透了书本。
她是在抗战中带着孩子离开梁宗岱的。沉樱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
六
沉樱,终随母亲、弟弟,并儿女到了台湾,好像人生的一个长梦,真真切切……
她住在苗栗县头份镇,淡泊的生活中,开始了对故乡的刻骨怀念,耳畔响着杜鹃声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呼唤。在大成中学,整整七年,以教书为生,以翻译为乐,走着人生的路。为了儿女读书,她移居台北,在第一女子中学教授国文,一晃又是十年。1967年,她六十岁,退休在家,微笑着寻找夕阳里的光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沉樱也一样,她喜欢小东西——小花、小草、小花瓶……她说:“我对于小的东西,有着说不出的偏爱,不但日常生活中,喜欢小动物、小玩艺、小溪、小河、小城、小镇、小楼。小屋……就是读物也是喜欢小诗、小词、小品文……特别爱那'采取秋花插满瓶'的情趣。”(《关于〈同情的罪〉》)所以连她在头份镇朋友果园中所筑的房子,也名之为“小屋”,并以散文《果园食客》记趣,写尽了那片大自然中的花花草草、风声雨声虫声鸟声,这使得她的“小屋”在台湾女作家的圈子里更加闻名。虽居台北,她却常到周围花木扶疏,四季竞秀的“小屋”里,在清晨和傍晚,在撩人感情的古庙钟声飞翔之后动笔写作。
对沉樱来说,大小创造和劳作都是幸福。她说:“我不找大快乐,因为太难找;我只寻求一些小的快乐。像我爱听音乐,从来没想到做音乐家;我爱画画,从来没想到做画家;我爱种花,从来没想做园艺家;我爱翻译,从来没想到做翻译家。我对什么事只有欣赏的兴趣,没有研究的魄力,更没有创作的热情。”
实际上,她是在创造。她又说:“人生的快乐有两个来源:一是创造,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沉樱的人生哲学。她一直都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工作。就在那座“小屋”里,她翻译了《爱丝雅》、《蓓蒂》、《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还编了《散文欣赏》、《观摩文选》等。
沉樱是台湾妇女写作协会的成员,虽然她极少参加活动,却与台湾的著名女作家林海音、潘琦君、钟梅音、刘枋等人过从甚密,同苏雪林、谢冰莹一样,被大家尊为“先生”。
沉樱执著于生活,有一颗不老的童心。她善于布置居室,精雅有致,极富匠心,更会欣赏色彩,爱做摺纸、针包、手帕、椅垫等小玩艺。工艺品。造纸花是她的手工绝技:“一根细丝,几片明艳的绉纹纸,串在一起,用手三抓两抓,就是一朵花。”她的纸花样子和色彩都很奇特:“可以说是花都不像;色彩之鲜,形态之美又比任何花都像花”。做手工艺品不仅是一种野趣,她觉得,在这个机械文明的工业社会中,最伟大的工具——人类的双手,不应该在平凡的劳作中失去尊严。每当她做完一朵花,同译好一本书一样,得到的是完成一件事的满足。1971年春,在台湾女作家的年会上,曾以她的纸花为主,举办了一次“女作家艺文作品展览”——包括各种手工艺品、著作及手稿,而她那姹紫嫣红的富有个性的纸花,是展品中的佼佼者。
七
沉樱的散文不多,但那纯朴、简洁、流畅的文笔,真挚、动人的感情,从不眩惑于奇巧和华丽的词藻等艺术特色和风格,是令人难忘的。1972年,在台湾她自费自售出版了《沉樱散文集》。这本集子分三辑:小品(十四篇)、信札(八篇)和序文(十六篇)。她在《自序》中说,从大陆到台湾,又越洋到美国,她对散文一直怀着敝帚自珍的感情。她散文中的《春的声音》、《我们的海》、《果园食客》等都是读者的难忘之作,先后已选入多种选集。对于散文,她有其追求。她编了三本《散文欣赏》,所收多为世界名家之作(也有中国作家的作品),从三篇序文中,我们可了解她对散文的看法:
这些散文不发议论,没有费解的地方,但轻轻的笔触也会使 你沉思默想,若有所悟;这些散文不重故事在有动人的情节,但 淡淡的意味也能使你会心微笑或掩卷太息。
……题材方面,大部分仍是风花雪月,鸟兽虫鱼,偶而有篇 写生活的,也都是身边琐事。记得这类题材一向为人诟病,仿佛 有卢、难登大雅之堂,尤其在这提倡题材积极化的当儿,更是不合 时宜。但自己喜爱的就是这种闲情逸趣,人有偏好,实在是没有 办法的事。……一篇文学作品的好坏,是在于有无意思。这意思 可分为意义、意味、意境三种。三者之中,如果一无所有、就是空 洞无聊;但有一即可,不必俱备。并且要排列次序的话,应该是意 境第一,意味第二,意义第三。这些文章即使不能说意境如何,至 少可以说意味尚可,至于意义有无,那也全在各人的看法、古人 就说过“无用之用,是乃大用”的话。在这繁忙的工业社会中,提 醒人们注意一下星月的光辉花草的芳香,如能因而陶情冶性,也 未尝不是重大的意义。题材不应加以积极消极化的划分,风花雪 月有写不完的情趣,身边琐事也有说不尽的真理,任何艺术的价 值,都是在于作者的感受心灵和表达手法,而不在于所用的素 材。外国诗人曾说“一粒沙内见世界,一朵花中有天堂”。中国诗 人也说“小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可见美感是不受任 何限制的。我们不应以题材论文章……
沉樱关于散文的这些议论,这里不想作深入评析。不过,我的理解,不仅这是她针对台湾社会而讲的一个大背景,广义而言,颇有些透明的真理。好的散文应当兼有抒情和说理,即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的结合。题材,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谈,“但是无论说理还是记事或抒情,文学散文不同于一般议论文记事文抒情文的地方,是在于文字表现上,手法的高妙,态度的亲切,意趣的横生。那种娓娓而谈的样子,使人同时得到真善美的感受,浸泳其中而又不自觉。”她的散文,正是她散文理论的实践。
八
文学翻译,是沉樱迄今不停耕耘的园地。她凭着自己的勤奋,先后翻译了英国、美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希腊等国著名作家及犹太著名作家的优秀作品《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同情的罪》(198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再版)、《怕》、《女性三部曲》(1982年,重庆出版社再版)、《悠游之歌》、《拉丁学生》、《迷惑》(台湾文星出版社)、《青春梦》(台湾正中出版社)、《车轮下》(台湾道声出版社)、《世界短篇小说选》、《毛姆小说集》(文星出版社)等近二十种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及世界名诗集《一切的峰顶》等,使这块园地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也使她成为台湾以翻译影响着读者的著名翻译家。
她的译作统编为“沉樱译书”、“蒲公英译丛”,再加上她的《沉樱散文集》、《散文欣赏》(一二三集)等,又编为“蒲公英丛书”,并全由自己经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自办出版社,能长久生存者甚少,多数最后总要倾家荡产。但沉樱却是成功的一例。那些译作一版再版,经久不衰,使她意外地得到了经济利益。沉樱的劳动,使那些外国名作跨越国界,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须,有了新的生命,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蒲公英译丛”书后,沉樱这样写道:
我喜欢花,尤其是那些有点异国情调的,像曼陀罗、郁金香、 风信子、天竺葵、蒲公英等,单是看看名字也觉有趣。这些花中蒲 公英是卑微的一种,冰雪刚化,它便钻出地面,展开绿叶,挺起黄 花,点缀在枯寂了一冬的地面上,洋溢着一片春天的喜悦。尽管 无人理会,仍然到处盛开,直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时候,它才 结子变成白头翁,悄然消逝。现在用作我杂乱译书的总名,一方 面是为了这名字的可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那卑微的可取。
这些话,说的是“译丛”,表现的却是她谦虚的美德、她的为人和性格。她与世无争,没有“野心”,她以蒲公英自况,甘作“白头翁”。
以翻译赢得读者是不容易的。但沉樱是一位幸运的成功者。她的译作——奥地利近代大文豪诸威格(Stefan Zweig)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与莫泊桑的《项链》、都德的《最后一课》、斯笃姆的《茵梦湖》、欧亨利的《礼物》并驾齐驱登上世界短篇小说典范宝座,一经发表就轰动了台湾,头一年就印行了十次,后来又印行了二十多次,打破了台湾翻译的记录,至今仍畅销于台湾和海外。
诸威格曾被称为七个伟大的欧洲人之一,他是首先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用在小说创作和传记文学写作上的人。罗曼·罗兰说“他如火如茶地发掘着伟大人的秘密、伟大热情的秘密,以及伟大创作的秘密……”,并以灵魂的钥匙,开启伟大的奥秘。他的作品多是警世之作,有三十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