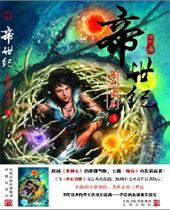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种生活的反映。这里面有血有肉,可歌可颂。”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丁玲结识了陈明。这位“…·二九”运动锻造出来的共产党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具有出色的群众工作才干。他当时是宣传股股长,协助丁玲做了不少工作。共同的事业,亲密的合作,使他们灵犀相通,结为伴侣,相扶相搀,直到丁玲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新闻记者,编《解放日报》副刊,进马列学校,在中央党校学习。这仅是她在延安生活近十年的部分记录。更大量的时间,她生活在群众中,心与战士、农民相交融,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双脚完全移向了工农大众。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贵的、很幸福的时代,也是她创作实践的一段黄金时代。丰收的硕果,来自辛勤的耕耘。这期间,她写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入伍》等小说。这些作品血淋淋地揭露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表达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细腻地描绘了知识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丁玲以对工农群众的现实主义描写,代替了她三十年代对于人民大众生活的偏于意念的表达。
这些作品后来也像丁玲本人一样,在褒贬毁誉之间升沉。小说中的主人公——乡指导员、贞贞、陈老太婆、陆萍等人,也跟丁玲本人一样被人批判和践踏过,今天,他们又像山土的文物一样,仍然清晰地刻着时代的印记,深深地留下了丁玲在铺满荆棘的路上走过的带血的脚印。
丁玲从上海亭子间来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时代”,这一段漫长的路是“用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它记载着作者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的痛苦磨练过程。丁玲回忆道:“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丁玲:《〈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正如冯雪峰在们丁玲文集)后记》中所说:“这些作品可以作为作者对于人民大众的斗争和意识改造及成长的记录。”
杂文《三八节有感》也是同期作品。她从关心妇女社会地位出发,就恋爱、婚姻、家庭等问题,列举妇女所遇到的各种思想障碍,并提出,妇女要获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要有健康的身体,进取的精神,思索的习惯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她从自己半生的经历中领悟到并告诫妇女们:“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韧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丁玲:《三八节有感》)
这篇杂文反映了在延安妇女问题上存在着的某些真实情况,作者的态度是积极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忽略了延安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人们的思想实际。
在解放区,丁玲创作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写了大量的歌颂新人新事的通讯报导。如《到前线去》、《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彭德怀速写》等。
1942年,丁玲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后,她思忖着如何写好工农兵的问题。胡乔木对她说:“你到工农兵中去吧!可以多写些通讯报导,多写些短文章。”同年7月,为纪念抗战五周年,朱德约了几位在延安的作家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电报,朱德说:“这里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请你们看吧,看了好写。”丁玲本不赞成作家没有生活,仅从文字中摄取材料来写小说的,但在那里读了两天后,前方的英雄事迹,确实是感动了她,她连续写了《十八个》、《万队长》、《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后,丁玲到边区文协从事报导写作,写了《三日杂记》。后来延安召开边区合作会议,会上,丁玲被丰富的素材所感动。不久,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毛泽东专门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请丁玲和欧阳山去吃晚饭。在晚餐桌上,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不久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又向大家说:“丁玲写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写工农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迈开了新的脚步,她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紧张的采访活动。在杨家岭,她访问了从前线归来的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刘伯承给了她明确的指示和具体的帮助。丁玲说:“他表现出来的才智、细致,对于干部的爱护,对人民的负责,更给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写在(到前线去)的前边》)
她还访问了蔡树藩、杨秀峰、陈再道、陈赓、陈锡联等人。他们都很健谈,提供了丰富、动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窑洞的黑角里,一手扇着扇子,一手写成了《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她高兴得一边写一边笑。
这些朴实无华的作品,表现了丁玲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她犹如一个高超的画家,或轻描淡写,或酣畅淋漓,绘制了时代的画卷。
在桑干河上
“这些人真使我感动,我不能不深情地望着他们,心里拥抱着他们,而把眼泪洒在这难走的乱石涧上,洒在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于9月离开延安,徒步经晋绥解放区,年底抵张家口。她本来要去东北,因内战中断交通,只好在张家口停脚。人走进阔别多年的城市,情感却仍停留在老解放区的农村,连做梦,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党中央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丁玲的眷恋之情有了新的寄托,她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她吃派饭,和身上长着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个炕头,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兴致勃勃地和农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们挑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熟悉人。当她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图景,已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了。她说:“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豚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上改中活动着的人们。”“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丁玲:《〈太阳照桑干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当她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已经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厉害,只好把火炉砌得高一些,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间,才能入睡。每当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时候,就像火线上的战士冲锋陷阵那样,坚持着写下去。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终于完稿了。
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国土改会议以前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翻身过程;小说通过华北地区一个村子土改运动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显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丁玲在创作小说中的人物时,立足于现实,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这个形象即如此。丁玲说,她开始在怀来搞土改时,一个地主的侄女长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闪过一下,她向周围的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难,却被村里一些人视为异己。丁玲虽然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她的影子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这个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使丁玲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坛上得到了较高的赞誉。1957年以后,这本书跟着丁玲同样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
欢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个春秋,在风浪的冲击下,她更加坚定、纯真,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联常委、《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务,倾尽全力完成党交给她的工作任务。
她曾作为中国作家和中国妇女的一名代表,为保卫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积极奔走。散文《旅欧散记》等作品,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活动和见闻。
新中国的明媚春光,热情、开朗、忘我劳动的人们呼唤着她,她决心用深情的笔墨描绘和歌唱她多年来梦寐以求,为之斗争的新生活。虽然事务缠身,她仍然写下相当数量的评论、杂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时代中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两个集子中。其中有宣传阐述党的文艺政策的演说和论文,有关怀作家成长的书信和报告,有缅怀革命烈士,歌颂英烈们丰功伟绩的纪念文章,也有歌颂中苏、中朝人民友谊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压肩,仍尽量找时间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写下了一些优美的散文《粮秣主任》(1953年)、《记游桃花坪》(1954年)等。这些作品同样注重写人、写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感情炽热,艺术手法精巧细腻。
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除她优秀的作品,为祖国解放而战的奋斗精神外,还有一点,即她遭受到罕见的不公正的待遇后,在逆境中仍然保持着不忘人民,执著信仰、不懈奋进的可贵精神。
1955年,她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头目。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时,又把她定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记》,连同在延安写的《三八节有感》、《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写的《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一并成为反党大毒草,她本人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并成了中国文坛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儿去了?
她在人民中间生活,在北大荒劳动。
“对于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实和丰富自己”。(《庐山访丁玲》、《解放日报》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认为到北大荒不是充军、劳改。她拒绝留在北京,要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她说:“我是个作家,不能离开社会,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孤独地写作,否则,我一定会苦闷。不是说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环境中做一个更扎扎实实的共产党员!”行前曾有人劝她,改个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玲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风浪也顶得住,没有什么了不起。“语言铿铿,铁骨铮铮,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
从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妇带着“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后在汤原和宝泉岭农场养鸡、养猪、种菜、锄草、扫盲,搞家属工作。她干什么都干得很出色。
丁玲到汤原农场后,遇上农垦部长王震视察工作。王震关心地让她当文化教员。在畜牧队,丁玲的扫盲成绩名列前茅。“还是老丁的队扫得最好。”——扫盲对象争相传颂她的先进事迹。她在生产队出墙报,一点也不马虎。为了画好墙报插图,她托人从外地买来不少绘画参考书,这些书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农场,她还是个有名气的养鸡能手。
十多年来,她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老共产党。她实心实意地接受基层干部的领导,也开诚布公地提出对工作的意见,认真细致地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她成了基层干部的助手和参谋。
在农场,她结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