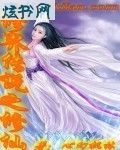张居正大传-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穆宗裁决底时候了。他和大学士商量:居正是策动人,当然认为可许;高拱也在后边策动;通过封贡,全是高拱指挥,张四维四处活动底结果。在这几个人底怂恿之下,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便是一面诏许封贡、互市,一面整顿国防的政策。政府底大政方针决定了: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其余授官的,一共六十一人,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都督同知是现代的中将,指挥使是现在的上校。从此以后,鞑靼骑士都成为中国的贵族和军官,有王,有中将,有上校。他们底铁蹄,不再践踏中国底田野;他们底刀枪,不再濡染中国底膏血。当然,朝廷谈不到使用鞑靼作战,但是朝廷也用不到对于鞑靼作成。高拱、王崇古、方逢时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谭纶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土;李春芳、张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土。他们回想到在自己出身的时代,正是俺答屡次南下,北京屡次戒严的时代:京师九门被围,侥幸没有失守;如今的国家,在他们手里苏醒过来了,整个的北边,解除了敌人底威胁,而且在人力和物力不再感受压迫的时候,可以从容布置。他们感觉到一种特有的愉快。朝廷方面,所费的只是几十件红袍;让红蟒、红狮子安慰鞑靼罢,当时所得的是北方底安全。
隆庆五年辛未会试,居正为主考,吏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吕调阳为副主考。居正嘉靖三十二年曾为同考官,那一次的进士如庞尚鹏、梁梦龙、陈瑞、曾省吾都是居正底门生,以后成为有名的人物。辛未科第一名进士张元汴,和第三名进士邓以讚同入《明史·儒林传》,但在事功方面,同样没有什么表现。同科惟有徐贞明留下一部有名的著作和一件伟大而始终没有完成的事业。他认定北方只知水害,不知水利。他也认定水害未除,正由于水利未兴。在他谪居潞河的时候,著《潞水客谈》,列举修北方水利十四利。万历十三年,贞明迁尚宝司丞,兼监察御史,奉诏垦田永平,于是招南人,大兴水利,次年垦田三万九千余亩。一切计划,正在逐步完成,但是北方人惟恐水田成功以后,江南的漕粮,必定派到北方,于是御史王之栋奏称水田必不可行,又称开滹沱河不便者十二事。经过这一个打击,贞明底计划,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不能不算是辛未科杰出的人才。最有表见的是刘台、傅应祯、吴中行、赵用贤。他们都是隆庆五年进士,都是居正底门生,其后对于居正,都曾经提出弹劾,因此在历史上都留下不朽的盛名。居正底不树立党羽,和刘台等底不阿附座主,都是可以称道的事件。不过从大体讲起,辛未一科的人才,还是贫乏;这一科里,任何方面,都没有第一流的人物。
俺答封贡的决策中,兵部尚书郭乾底表现太差了;没有办法,没有决断。五年三月,郭乾免职。高拱想起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杨博,但是杨博曾经做过吏部尚书,他已经是六部底领袖,也许不愿意回兵部。不妨事,官衔仍是吏部尚书,由他管理兵部的事。整个的政局,因为高拱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杨博以吏部尚书管理兵部事,显见得畸形,但是高拱和杨博都算是用当其才。
政权是高拱的了,首辅李春芳一切放任,自己既不眷恋政权,为什么要争权呢?而且春芳也明白,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私人秘书,首辅底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显的规定,一切都是演变底结果,既然是演变,根本就说不上固定,那吗,由他去罢。但是高拱决定不能容许春芳底存在。高拱想起自己和徐阶的夙仇,正要报复,都被春芳挡住了,因此决定攻击春芳。春芳也看见了,认得高拱不能相容,索性上疏请求致仕,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穆宗还在留他,经不起南京给事中王祯又提出一次弹劾,五月间,春芳终于致仕而去,他从隆庆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二年十一个月的首辅。据说王祯这次的弹劾,完全是仰承高拱底意旨。从此高拱是首辅兼管吏部尚书事。凭着穆宗底信任,和他自己底才具,以及那有仇必报的气度,他已经成为事实的独裁者。
在封贡、互市的争论中,居正占据主要的地位。这次决策的大功,当然应由高拱、王崇古,和居正平分,但是居正却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郭乾徬徨歧路的时间,向皇帝请旨召集廷议的是他。封俺答一事尚未决定的时间,检出成祖敕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故事以为前例的是他。决定以后,拟旨敕行的也是他。他正在和王崇古计议四件事:(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所以最初必须由官中布置,使人知有利,自易乐从。(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底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掉换。(三)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加意防备。种种方面,他都顾虑到了。讲和也罢,封贡也罢,这是一个名称;居正只认为是停战。停战是继续战争的准备,他要修城堡,开边荒;他要消灭赵全这一群汉奸底余党,他要训练将士以防鞑靼底进攻。(参书牍三《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
居正对于国事的筹措,没有使他忘去对于老师的维护。徐阶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首辅,但是对于自己的三个儿子,竟是毫无办法。隆庆三年应天巡抚海瑞到了,这是有名的铁面御史,他对于属内的大绅巨室,一概不买账。最先感觉威胁的便是徐阶底三位少君。他们写信给居正,居正一边诰诫,一边安慰他们说:辱翰贶,深荷远情。近来人情风俗,诚为可骇,俟海公人至,当作一书善譬之。太翁老师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护。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贻戚可也。恃在通家,敢尔妄及。(书读十四《与符卿徐仰斋》)
这一阵风波过去以后,高拱再相,徐阶更感觉不安,居正和应天巡抚朱大器说:存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闻中翁再相,意颇不安,愿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刚峰(瑞)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虚心剂量之,地方幸甚。(同卷《答应天巡抚朱东园》)
隆庆五年,事态更加严重。这年,徐阶生日,居正去信,自称“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又说,“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同卷《答上师相徐存斋九》)内阁的大权,完全在高拱手里,言官们又听他指挥,一步走错不得,一句说错不得,这是隆庆五年居正所处的地位。徐阶底地位更坏了。三个儿子同时被逮,田产充公了,两个儿子也问了充军的大罪,只留得徐阶慢慢地回味会不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果。在严重的局势下面,居正还是苦心调护。他不愿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阶;集中留着下列几封信:忆公昔在姑苏,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宪节以临之。乃近闻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吴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高拱)有憾于徐,故为之甘心焉。”此非义所宜出也。夫古人敌惠、敌怨,不及其子。中元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仆素所深谅,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元公曾有手书奉公,乃其由中之语,必不藏怒,而过为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终老,未有显过闻于天下,而使其子皆骈首就逮,脱不幸有伤雾露之疾,至于颠陨,其无乃亏朝廷所以优礼旧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乐闻也。仆上惜国家体面,下欲为朋友消怨业,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闻,惟执事其审图之。(书牍十四《答松江兵宪蔡春台讳国熙》按国熙承高拱旨,穷治徐阶事,见王世贞《首辅传》卷六)
松江事,高老先生业已寝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为已甚,报怨亦自有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夺之牛,无乃过乎?今全吴亦所以爱郑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往者奉书云云,盖推元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业已施行,自难停寝,但望明示宽假,使问官不敢深求,早与归结,则讼端从此可绝,而存老之体面,元翁之美意,两得之矣。仆于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谓“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仆之所欲闻也,倾耳以承,幸勿终靳!(同卷《答应天巡抚》)
这三封信,都很闪铄,尤其是后面的两函。高拱和徐阶结怨,急图报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指高拱给蔡国熙的信,大致是解释仇怨的话,这是表面文章,居正认为“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只是顺水难舟,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答梁鸣泉函》,不知是否误题,梁梦龙(即鸣泉)为居正门下士,函中语气,似不类。徐阶、松江人,高拱、新郑人,所谓“全吴”“爱郑”者指此。答应天巡抚函所谓“辱回示业已施行”,正指来函“无可挽回”的表示,至于“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对于居正的一种谣言,正取一种欲说不说的姿势?现在不管他,但对于居正,还是一种威胁。“是仆之所乐闻也”,是一句挣扎的话。
高拱入阁以后,居正所处的是一个最困难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审慎。热中的人不肯轻易放弃政权,但是要想维持政权,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庆五年居正还遇到一个问题,然而也居然被他度过了,这是胶莱河的问题。
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河水骤浅,江南来的粮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却在南京。一切的资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万石粮食,全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惟一的生命线是运河,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联络,整个的国家,立刻受到影响。偏偏运河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那一条安全的水道,从瓜洲渡江,要经过邵伯湖、高邮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这些地方还好;再上去便是洪泽湖,淮水从安徽来,在清口和黄河交汇,这是最大的难关。再上去,从清口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运河要靠黄河底接济。水量太大了,南方来的粮船随时有漂没底危险;可是水量太小了,粮船便要胶搁半途。国家底前途,完全寄顿在这一条毫无办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险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底职责,一面仍是不时提出海运底问题。海运是从太仓、嘉定沿东海绕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条航线。在现代当然是一条很简单、很安全的航线,但是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和造船底技术不比现代,所以一路的危险还是很多。有了危险,便不免要牺牲。牺牲人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明代,连皇帝杀一个罪犯,还要经过法司五次底执奏,何况是平常的官吏!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为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引起南京给事中张焕底弹劾。三千二百石只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损失,本来不算太大,但是张焕质问,“米可补,人命可补乎?”便无从答复了。运河既然时常发生困难,海运又危险太大,因此便有缩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议。这便是胶莱河。
胶莱河出自山东高密县,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至掖县海仓入海,这是天然的水道。单凭这一条水道,当然谈不上漕运,因此便有人提议在中间另凿新水道,沟通南端的胶河,北端的莱河,这便是所谓胶莱新河。胶莱新河始终不曾完成,但是却不断地涌现在明人底脑际。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旧事重提,上疏请开胶莱新河。恰恰在隆庆四年黄河再决,高家堰大溃,运河水量不足,漕运中断以后,这一个问题,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极力主张重开胶莱河,这不是他底好大喜功,而是他底公忠体国。有了胶莱河,漕运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胶州湾入胶莱河,再由海仓口出海直入天津,漕运便利了,北边底粮饷有了把握,国防问题、经济问题、跟着胶莱河一同解决,为什么不要开!居正底公忠体国,和高拱一样,但是他不能不顾虑到水源的问题。胶河和莱河的分水岭要凿,已经够困难了,还不算是困难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从哪里来?山中不是没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