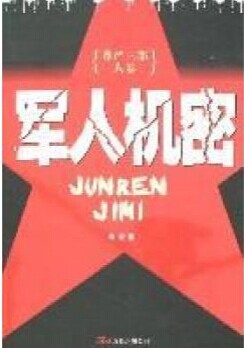军人大院-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们席地而坐,可以把视野放得远远的,仿佛能看到一个连着一个的山头,无法想象山的尽头在哪里,又是何年何月能走出这些山。尽管这样,此时的她们就这样坐着,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后来分了工,任务是挖果树坑,该挖果树坑的地方都用白石灰做了标记,必须挖成一米见方的大坑才算数。由于是补挖,而且分科室,她们就被分别安到了不同的地方。
任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运了运气,就开始挥舞起锄头,一锄头下去震得手一阵发麻。甩了甩手,又接着干。说起来,她是挖过地的,从上小学的时候就抡过锄头,到了中学时期,用锄头的机会就更多了,学校有专门的农场,每年每一个班都轮流去,带着背包,吃住都在那里,于一种真正的农活,那时全当玩了,一说下农场都高兴得像去度假一样。
任歌的手曾经起过血泡,破了又长好过,那时真希望自己的手掌长出老茧,就总是用手去摸,摸到一点点茧,就很心安,甚至是骄傲。任歌还知道看什么样的锄头好使,主要是看吃土的部分,铮亮而薄的锄头一定好使,因为使得多;如果锄头的把松了,就放在水里泡一泡,把木头把泡胀,这样就不会再松了。下锄时一定要果断,这样会吃土深一些。
不过,已经是好多年没有使过锄头了,现在拿起锄头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锄头总是与年少和欢乐连在一起的,就好像是一个老人在告诉着自己,宝藏的秘密。舞锄头也和骑自行车一样,不会轻易忘了,最起码对任歌来说是这样的。但是手疼是真实的,开始是火辣辣的疼,那是因为表皮与真皮正在分离,这个时候往往容易丧失意志,很想弃锄休息,这时心里喊着要坚持,就坚持着,慢慢地,火辣辣的疼就变成了顿痛,好像似痛非痛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松开锄把时,手掌上就会像长了眼睛一样,最少两个血泡在看着你的脸。
任歌还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微微从她的脸的一边吹来的山风,使她对她正在于的一切,充满了美好的感觉。不知为什么,任歌一个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女孩,对野外、对自然却有着一种如痴如醉的向往。可是,她的这种向往总是被父母繁忙的工作无情地击碎,在她深深的印象里,妈妈对她说得最多的话就是,太忙,没时间。这成了它所有认识的字中最讨厌的几个字,讨厌得几乎从不使用。
“咔喳”一声,打乱了任歌此时的平静心情。原来是杨干事在她最专注于挖苹果坑的时候,抢拍了一张照片。
“你……你怎么这样?我不要照。”任歌喊道。
“挺好看的,”杨干事说,“真的挺好看的。”
“好看也不要,你把它拿出来。”任歌声音中透着厉害。
“这,这怎么能拿呢?”杨干事有些心虚了。
“不管,”任歌说,“我不管,反正你把照我的拿出来。”
“……”杨干事一时不知该怎么好,他感到任歌是真的。
“拿呵,快拿呵,你这是偷拍,知道吗?‘偷’。”任歌一副得理不饶人样。
“任歌,你……你……”杨干事变得结结巴巴。
“我最讨厌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任歌硬邦邦地丢出了几个字,说完就自顾自地抡起了锄头。
杨干事见状,忙上去欲夺她的锄头:“我来。”
“讨厌。”任歌突然把锄头一松,扭头离开。
只听得“咚”地一声,杨干事一只手捻着锄头,一个四脚朝天,锄头也甩到了一边。
任歌忙转身,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是在山坡上,杨干事的头在低处,脚在高处,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努力了几下都没成功。他看到居高临下的任歌,还忙不迭地给她递着笑脸。
任歌本来是想笑的,可是一看到杨干事那个躺着的笑,她的心好像被突然使劲扎了一下,有一种难受极了的疼,她急忙向杨干事奔去,向他伸出了手。
好久,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一句话,任歌坐在山坡的一处,杨干事又抓起了锄头,他挖了起来。空气中传递着的惟一的声音就是锄头落地的声音,听起来感觉是干净果断的,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在老家,我挖的地仅次于我爹。”杨干事突然说。听起来像电影里传来的话外音。
“我爹是全村挖地挖得最好的。他挖的地特别鲜,种什么都能活。我高中毕业后,当了回乡知青,我爹说,我能讨到饭吃,因为我挖地挖得好。尽管这样,我心里还在想,我以后决不用锄头挖地,我要用拖拉机,我没有告诉我爹,我也没有来得及买拖拉机,我就来当兵了。”
杨干事的声音在山坡上萦绕,那时好像所有的人都隐蔽起来了,就只剩他们。
任歌不知不觉竟听了进去,问:“现在呢?你爹买拖拉机了吗?”
“没有。他永远也不会买的,他陶醉在他亲自挖的鲜活的地里,他不相信拖拉机会挖得比他的好。”
任歌忍不住看了一眼正在抡锄头的杨干事,又看了一眼明显深下去一截的苹果树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想一想杨干事的模样,一个感觉:粗。细想也是方嘴大眼的,像一个没有仔细雕琢的塑像胚子。就想到了恋爱这样的事上,其实,也不知道恋爱是怎么回事,但是从书上看总是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比如,心慌,比如,特别想见面。想想自己,一点这样的感觉都没有。竟恨起自己,在没有任何用心的时候,竟伤害了二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办。
“任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直杆杆,杨干事说了一句。
任歌突然不知道该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还从来没有人和她正而八经谈过这事。
“不……不是……”
“我知道你是城里大干部家的子女……”
“不,不是……。
“难道出生就能把一个人的幸福葬送了吗?”
任歌突然想到了才看过的一本书,书中表达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她看来这是最残酷的,最没有人性的。突然心里有一种悲凉的感觉,自己突然成了小说里的某个人物。
“我也想像你们那样,投生到一个好的家庭……”
“不,不是这样的……”
任歌感觉到一种浑身是嘴都说不清的难过。
后来杨干事还在说。一个男人为了获得幸福而作出的努力,让人感觉到有几分勇敢似的。任歌已经不太听进去他说了些什么,她似乎在飘荡着,不知道在哪里飘荡,好像被杨干事的语言托着飘荡。
最后,她说了句:“让我考虑考虑,我需要时间。”
在杨干事的眼睛里,那一天的大平地变得无比的美,过去他从未发现的美。
夏冰兴奋地告诉戴天娇:“找到材料了,用铝片。”
戴天娇看她那副兴奋样儿,笑眯眯地说:“谁想出来的点子?”
“钱兵呗。”夏冰没有看出戴天娇眼神中的含义,她主要是太兴奋了,“先用废弃的铝片做试验。可多了,就是那些铝盖。”
“真是不可想象,它会是什么样呢?”王萍平说。
“是啊,它会是什么样呢?”
姑娘们简直无法想象她们将要制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方的?圆的?长的?扁的?可是,她们想做一件事,想创造出奇迹。
“只要我们去做,一定能成。”夏冰信心十足地说。
“如果真能成,真的有一天穿刺不再是技术,而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操作,那该多好啊。”戴天娇的话里充满了憧憬。
“会有那么一天吗?”王萍平说。
夏冰满眼不高兴地看了一眼王萍平,她总觉得王萍平的性格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阴气。
“也许能成呢。我们还是往好的方向想。”戴天娇说。
这回轮到王萍平不满地看了一眼戴天娇,她在心里忿忿地说道:“在你那里当然一切都是好的,你根本就不知道苦难、倒楣。”。她心里是这样想的,嘴上却在说:“要真是那样就好了。”语气天真。
“哎,萍平,我们一起来帮夏冰吧。其实也不能说是帮夏冰,这是我们大家的事。”戴天娇积极地鼓动王萍平。
王萍平也做出热情很高的样子:“好啊,那多好啊。”
后来她们三个人就真的在一起讨论起铝片的事,讨论归讨论,一切对她们来说都很模糊,但是,这总归是一件事,一件让她们思考、让她们花费时间的事。
白天上班时,她们心里想着这一件事,竟觉得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人在等着她们,她们有责任减轻病人的痛苦。走廊上常看到戴天娇和夏冰奔跑忙碌的身影,护士长心里甜滋滋的,为自己有两个这样的护士。
相比起来,王萍平上班时的工作量要小得多,谁都知道在医院最好待的、最舒服的就是五官科,从病情上来说,五官科的病人死不了,尽管眼睛鼻子出了毛病,手脚还是可以动的,因此生活护理基本没有,输液打针的少,大部分病人都是一日三次点药水,十多分钟就能干完。因为事少,护士们总爱坐在护士办公房里聊天。在王萍平看来,本来年纪轻轻的女孩,就是在聊天中成了地地道道的妇女的。
分到五官科是王萍平没有想到的,她并不贪图这点轻松。当了三年的兵,她清楚要想被重视、被认同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不是怕苦的人,她是有远大抱负的人,就如她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果断地作出决定一样。毕业分配的时候,总医院那边已经传了消息,并且说得很具体,想让她到手术室去,凭她的身体和她的反应,带过她的护士都觉得她天生是一个上手术台的料。可是她还是坚定了她的选择,她希望到一五八这个人人都觉得不好的地方来,干出一番不凡的事业来。
她没有想到她居然到了五官科,她想同来的四个人,如果要照顾谁的话也轮不到她,偏偏就让她到了最舒服的地方,每天看着聚集在护士办公室里聊天的同事,她就觉得自己难以融进去。她不明白有一个老护士能够每天向别人重复她儿子的那点事,诸如吃了什么东西,说了什么话,一切在她听来都庸俗寡淡,可是,那个护士却津津乐道,并且还有人不停地附和。
终于,有一天她发现了一个可以去的地方,那是科里的会议室,在走道的尽头,最大的一间房子。会议室里围墙边放了一圈沙发,因为在走道的尽头,很少有人走到那,王萍平为自己的发现高兴,每天当其他护士聚集在办公室里聊天时,她就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来到会议室,把门关紧在里面学习英语。每一个英语单词在她的眼里都是一个通向她的目标的台阶,她在心里鄙视那些无聊的谈话,她觉得她虽然没有戴天娇那样的出生,但是,她有戴天娇那样的素质,如果让她有戴天娇那样的环境,她会比戴天娇优秀得多。
第八章
护士节一过,各科又紧锣密鼓地准备“八一”晚会的节目。
医院政治处发出通知,“八一”要搞一台工体联欢晚会。这在一五八并不是第一次,可以说,这是一五八的传统。要一五八的老人说起晚会的事,他们都很来劲,他们自己就当过演员。
“那时,不是吹牛的,一五八排的节目,比现在有些正而八经的文艺团体要好得多。就说那个潘霞,舞姿就不说了。还多着呢,什么丁米米,高玲,都是天生的演员。”他们总是这样开始的。
“她们怎么不到文工团去呢?”
“她们本来就是文工团的,后来不是文工团撤销了吗?分到了各个单位。”
“一五八曾经很兴旺的。”说话的人说,“哎……”
话没说完。
“现在她们都到哪里了?”
“到处都有。都好人走了,有好几个嫁给了十航校的飞行员,都是北方兵。长得都很帅。”
这样的话,从姑娘们来到一五八以后,听到了不少。有一些名字是已经烂熟在她们心里的了,关于这些没有见过的人,在她们的心里有了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反正她们都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能歌善舞,那么的不食人间烟火。
朱丽莎回来说:“别看秦护士现在那个样,她就是到部队演出的时候,被一个军医看上了,追到医院来的。”说着,她还比出一副手里握着枪的样子,“呐,就是这样,飒爽英姿五尺枪。”说着就作了一个出枪的动作。
看来在她们还没有到达一五八的时候,一五八已经开始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当然,这并不奇怪。
外二科的教导员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这次晚会出节目,他一点也不发愁了,按规定出节目是按大外科来分的,也就是说,外一、外二和五官科是大外科支部,出节目就是这样合在一起的。教导员甚至有些得意,因为去年分来的五个新学员无巧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