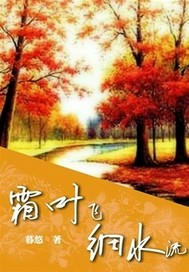霜叶红似二月花-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请不请朱行健呢?”
“回头再看,”王伯申沉吟着说。“子安,你明天就去找他,也把我们租用学产那块空地这回事,原原本本对他说一说。这位老先生有个脾气,不论什么事,只要带联到一个‘公’字,便要出头说话;咱们这件无头公案里如果再夹进一个老朱来,那就节外生枝了,而且又是赵剥皮所求之不得的!”
“要是他硬说不通,又怎么办呢?”
“那亦只好由他去罢。咱们是见到了哪一点,就办到哪一点。”说着,王伯申站了起来,离开那座位,在屋子里踱了两步,又说:“哦,如果钱良材肯替我们说一两句,那么,老朱这一关,便可以迎刃而解;这老头儿最佩服良材的父亲,俊人三先生!”他仰脸笑了笑,忽地又转眼朝儿子民治瞥了一眼,嘴里又说:“子安,明天先找朱竞新,探一探那老头儿的口风,然后你再见他。”
梁子安也退出以后,王伯申兀自在屋子里踱着,好像忘记了还有民治在那里等候得好不心焦。窗外大树有浓荫已经横抱着这小小的洋楼,民治枯坐在屋角却想像着那边凉亭里活泼愉快的谈笑,仿佛还听得笑声从风中送来。
王伯申忽然站住了,唤着儿子道:“民治,现在你有了一个同伴,可以带你到日本去;他是冯退庵冯老伯的晚辈,老资格的东洋留学生,什么都在行。你在国内的学校也读不出什么名目来,而且近来的学风越弄越坏,什么家庭革命的胡说,也公然流行,贻误人家的子弟;再读下去,太没有意思了。”
民治站起来连声应着,那口音是冷淡的,倒好像父亲对他说的是:现在中装也不便宜,又不好看,你不如改穿了洋服。
王伯申也不喜欢民治这种淡漠的态度,睁大了眼睛看着民治好半天,这才慢慢地又说道:“你也不小了,人家的姑娘还比你大一岁;梅生也说过,趁今年他手头兜得转,打算办了他妹子的这件大事,我呢——也觉得今年闲些,先把你的婚事办了,也好。现在就等候退老一句话。他是冯家的族长,而且秋芳小姐又拜过退老的二姨太太做干娘……”
“爸爸!”民治这突然的一声,将王伯申的话头打断。不但王伯申为之愕然,甚至民治自己也大大吃惊,怎么心里正那样想,嘴里就喊出来了。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王伯申皱了眉头,看着发怔的民治。“怎么又不作声了?”
“嗯嗯,”民治定了神,安详地回答,“爸爸不是也不大赞成早婚的么?”
“哦?我有过这样的话。”王伯申淡淡地笑了笑。“你还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罢。”
“我打算读完了大学再结婚。”
“为什么?”
“我还不算大,今年才只二十一岁。而且,而且,冯——
冯小姐也在求学时代,至少也得等她中学毕业了罢?“
“哦!你还有什么话?”
“没有了。”民治俯首低声说,但又提高了声音加一句道:
“我请爸爸缓几年再办这件事罢!”
“嗯,求学,求学——”王伯申微笑着自言自语似的说,他走前一步,站在他儿子面对面,突然沉下脸,口音也变得严厉了,“民治!在我跟前,不许说谎;什么你要等到大学毕业,冯小姐也得求学,这一套是你心里的真话么?结婚也妨碍不了求学啊!结过婚,你仍旧去东洋,冯小姐仍旧进省城,你们照样求学,妨碍了什么?”
民治依然低着头,不作声。
“怎么你又不说话了?”王伯申的口气又和缓了些。慢慢走开,坐在写字桌前,一眼接一眼瞅那低头站着的民治。突然他冷笑一声,很快地说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么?你是嫌冯小姐相貌差,你不愿意她;全是有容惹出来的事。有容的嘴巴,全没一点分寸,我本来就要警戒她;你要存什么别的念头,就不是我的儿子!”
民治抬起头来,正眼看着他父亲的发怒的面孔,但依然不说一句话。
这种无声的反抗,惹的王伯申更加生气了,他又抓起那个玻璃镇纸来,使劲的捏着。他把一切罪过都归在女儿身上:儿子的不乐意这头婚姻,固然是由于女儿的多嘴,甚至近来连太太也对于那位未来的儿媳没有好感,也是女儿之故。好像全家的人都和那位冯小姐缘分不好。王伯申扔开那玻璃镇纸,叹口气道:“民治!难道咱们能向冯家悔这头亲事么?退老的面子,我和梅生的交情,咱们怎么能干这样的事?你去仔细想一想。”他挥手叫民治走,便隔窗唤那蹲在大树下的当差姜奎。
民治心头还是沉甸甸地,但是挂记着什么似的,从父亲那里退出来,便直奔那后园,找他的妹妹。过了那边门,他就伸长脖了望那凉亭。然而亭中空无所有,仅仅亭柱上挂着有容常用的一柄雪白的鹅毛扇,临风微晃,表示了她们曾在这里停留。他惘然走着,满园子静悄悄的。这一个只有他兄妹二人还时时光顾的废园,除了老妈子和当差,还有寄宿在前面平房里的轮船公司的小职员种着玩的几畦菜蔬颇有蓬勃的生机,此外便是满目的萧条和衰黄,虽有几棵大树,却也奄奄毫无意趣。惨绿和衰黄,统治了这周围三四亩地,但幸而尚有这里那里晒着的多采的衣服,点缀了几分春色,民治绕过那凉亭,正在茫然无所适从之际,忽听得有容的笑声起于右首。右首有一个斜坡,坡上那三间破房子在当初大概也颇擅藻绩之美罢,现在却堆放着王伯申的父亲做官不成而留下的纪念物。民治刚到了斜坡前,果然看见有容和静英手挽着手,站在那三间破房前指指点点。
“喂,二哥,”有容已经看见民治,便叫着,“爸爸说什么?
我骗了你没有?“
民治苦笑着,不作回答。他走到了她们面前,这才问道:
“你们望见了什么呢?这样高兴!”
“这个破园子是爸爸手里买进来的。”有容只顾向静英说,“可是他又不修。我和二哥打算把那边的树根弄掉,开个网球场玩玩,爸爸又不答应。”于是又转脸对她哥哥道,“密司许称赞这破园子,说局面是好的,只要稍稍修理一下,便很行了。二哥,你再问她罢,她说得头头是道的!”
静英微笑。民治望着静英笑了笑,却不说话。静英转脸望着树梢上的日影,轻声说:“时光也不早了。”
“嗯,不过四点多罢。”民治应着,但马上又觉得不好意思,别转脸去,讪讪地又说:“到凉亭里再坐坐,不好么?容妹,咱们下去罢。”
有容也不开口,独自当先走了。将到那凉亭边,她忽然回头又问道:“爸爸怎么说?”
民治一怔,有意无意地看了静英一眼,这才轻声答道:
“还不是那两件事么!”
“你怎样回答?”
民治默然半晌,方答道:“爸爸很生气。”
这时候,静英说要回去,有容又留她:“忙什么?被褥帐子的尺寸还没量给你呢。”又唤着民治道,“二哥,你怎么不帮我留她!”
他们三人穿过了边门,却见孙逢达和冯梅生正走进那月洞门去,有一个愁眉苦脸的乡下女人缩手缩脚站在天井角落。孙逢达回头来,对那女人说:“你在这里等候,不要乱跑啊!”
冯梅生和孙逢达刚到王伯申的办事房的门外,正值那当差姜奎垂头丧气退出来。王伯申脸有怒容,两手反扣在身后,靠着那写字桌的横端站在那里,劈头就说道:“逢达,姜奎那哥哥的事情,你怎样答应了姜奎的?怎么我不知道?姜奎这东西,越来越发不懂规矩了,有事不找你,倒来我这里麻烦!”
孙逢达慌了,还没回答,冯梅生却搀言道:“是不是赵守义要吞没姜奎哥哥的田,已经将他的哥哥送到警署押起来了。”
“就是这件事,”孙逢达说。“姜奎跟我说过,想求东翁设法,可是刚才我忘记了,又瞧着东翁正忙,这一点小事,何必——可是,刚才那姜锦生的女人又来了,梅生兄也看见的,缠住我,定要我转求东翁救他们一下。”
“难道要我替他们还清了赵守义的高利贷么?”王伯申冷笑着说。“谁叫他们那样蠢,自己钻进圈套?我猜他们那借契上早就做死了的,他们一不识字,二不请人看看,糊里糊涂就划了押,这会儿又来求我,嗨!”
孙逢达不敢再开口,只对冯梅生瞥了一眼,希望他来帮腔。冯梅生笑了笑,就说道:“赵剥皮那个玩意,简直是天罗地网,几个乡下佬,怎么能够逃出他的手掌心;这件事一旦经官,不用说,道理全在赵剥皮那一边。不过,他现在先将姜锦生押起来了,大概锦生那几亩田还没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所以赵剥皮使出他那打闷棍的一手来。”冯梅生又笑了笑,向王伯申做个眼色,“伯翁何不叫逢达去跟高署长说一声,先把人放了出来?”
“哦——”王伯申沉吟了一会儿,也就点了点头。孙逢达走后,冯梅生挨近王伯申,又悄悄说道:“姜锦生这件事,倒来的凑巧呢,借此我们也回敬赵守义一杯冷酒!”
“哦?”王伯申看了冯梅生一眼,慢慢的走到朝外的那个十景橱前,坐在那旁边的躺椅里,“可惜这杯酒未必辣!”
“也不尽然。”冯梅生便在写字桌前那张椅子里坐了,笑吟吟回答。“赵守义,一杯冷酒灌不倒他,十杯二十杯,也就够他受了。他那些巧取豪夺来的田地,十之八九都没有结案;我们把姜锦生弄了出来,还要教他反告一状。尽管借契上是做死了的,但何患无词……”
王伯申点头,也笑了一笑。
“有一个宋少荣,也小小放点儿乡账,他就能够找出七,八,十来个户头,都是被赵守义剥过皮的;可是,皮尽管剥了,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两年,案却没结。都跟那姜锦生似的,被老赵的一闷棍打晕了去,却没断气。”
“嗨!”王伯申站了起来,“梅生!你以为那些乡下佬就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么?”
“怎么不敢。只要有人撑他们一把。”
王伯申又坐了下去,默然深思,好一会儿,这才抬头看着冯梅生道:“吓他一下,这也未始不是一法。不过,我却记起了先严的一句话来:教乖了穷人们做翻案文章,弊多利少!”
“不妨试一试。反正我们能发,也能收。”
“好罢。这算是一着棋,先备好了在这里。可是,梅生,曾百行那边,我想来还是你去一趟。如果他口头松动,许他一点小好处也使得。”
“这倒有八分把握,曾百行已经抛过口风。”冯梅生笑着说,又伸手到衣袋里摸出一张纸来。“这是家叔的回电,刚接到。”
王伯申接过电文看了,眉头就渐渐皱紧;他卷着那电文的纸角,轻声说道:“怎么办呢?退老说柴油轮一时缺货,兼且价钱也不相宜。可是——刚才子安还巴望下月初头能够多开一班呢!”
“怎么,水退了一点罢?”
“哪里,哪里!”王伯申作色摇头。“子安是那么想望罢哩!这几天,哪一班船不是勉勉强强走的?昨天还冲坏了三两处堤岸,自然,也不过几亩田灌了点水,可是,咱们那条‘龙翔’险些儿吃了亏。乡下人竟敢鸣锣聚众,……要不是‘龙翔’的大副有主意,开足了马力只管走,那,那就麻烦了!”
“哦!‘龙翔’船身本来是大了一点。”
“说起来真是困难重重,”王伯申叹了口气,“这会儿夏秋之交,水涨了,不好走;回头到了冬天,水浅了,也不好走。
无非是河床太浅之故。所以我打算参用柴油轮。谁知道……“他忽然苦笑一声,站起来将双手一摊又说道:”谁知道还有一位大少爷脾气的钱良材,简直要把修堤开河的责任都推在我身上!“
冯梅生也笑了笑道:“钱良材来了么?我倒想找他谈谈。”
“可以不必!”王伯申沉吟着说,就把打算请良材吃饭解释误会的意思告诉了梅生,又问道:“明天如何?回头我就叫逢达写请帖。就是我们自己几个人——要不要再请谁呢,你想想?”
“或者加一个李科长。”冯梅生回答。忽然干笑了一声,他又说道:“哦,忘记告诉你了,今天早上碰到李科长,他问起那个习艺所,很说了一番好话,哪知他随手就荐两个人,还说不拘怎么,务必安插一下。”
王伯申冷笑道:“事情还没一点头绪呢,他倒先塞进两个人来了,真是笑话!”
“不过县署里几个科长的看法,认为此事必定能够办成。
赵守义困兽犹斗,徒然拖延日子罢了。“
“也许。”王伯申扬眉微笑。“赵守义也知道正面文章做不过我,所以究凶极恶,到处放野火。串通一个曾百行出来捣蛋,还不过小试其端,我猜他的毒计还多得很呢!”他皱着眉头沉吟了一会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