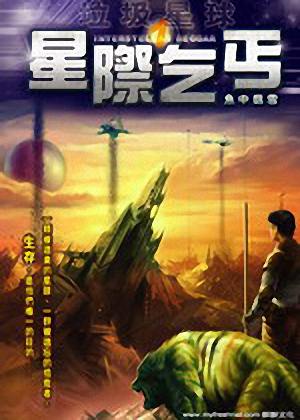中国乞丐调查-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你看我能赚到钱吗”?
“你”?那个乞丐听我这样问他,不由的打量我。
“我看你挺象个好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要做乞丐,你不读书吗”?
“我最烦的就是读书了,我父母一天到晚要我关在屋子里面学习,我学够了就跑出来了,我就是要做乞丐,他们不是最怕我没出息吗?我就是要做最没出息的事儿”。
“那你刚才说你爸爸的事儿”?
“我那是骗你的,我爸爸这会在山东呢”。
“那你行了,做乞丐没问题”。
从那天起,我跟那个老乞丐成了朋友,他教会了我许多做乞丐的规矩,而且,帮我找了几个地盘,他说,天津的丐帮是全国都出名的,要做乞丐就在天津做,这里的钱好赚。
就这样那一段时间,他带我跑遍了天津的大街小巷。他还给买我了副眼镜,让我扮做失学学生,在火车站。汽车站乞讨,这种事刚开始还不错,有许多人相信,我们也赚到了钱,可后来,警察老来赶我们,我们就再也不敢去了。
那个老乞丐说他已经乞讨了20年,他儿子都在农村盖起了大瓦房,娶上了媳妇,给他生了个大胖孙子,儿子劝他别干了,回家抱抱孙子享享福,可他说,干惯了,不干浑身难受。
不过他的心肠挺善良,晚上我们俩睡在一起,他就劝我赶快给家里打个电话,他说,“你爸妈肯定找你都疯了,放着那么好的日子不过,来当乞丐你真是没出息。”
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可我就是扭不过这个弯来,我就是要没出息怎么样。
日子过得也很快,我每天在街上,找个地方一蹲,有时候也学着老乞丐的样子把两只胳膊藏在胸前,垂着两只空荡荡的袖子,赚得钱虽然不多但也够吃饭的了。
好几次路过公用电话,我都忍不住想要给爸妈打个电话,我只想告诉他们,我在外边挺好,不要他们牵挂,可我又不敢,怕他们找我回家,怕他们恨我怪我,如果这样我宁愿不见他们。
这时天也凉了,老乞丐送了我一条裤子和一双破皮鞋,我脱下了短裤和凉鞋,换上了那一套,脏兮兮的往那儿一蹲,正式的象个乞丐了。
这时有人找我,想拉我入他们的帮伙,我知道这些乞丐帮都挺吓人的,所以,我就装傻,搞的他们也不清楚我的底细,打了我一顿便把我放过了。
有了这次经历我才真正的想回家了,这些乞丐无法无天,整天找事打架这让我很害怕,我是出来寻找自由的,而不是走向犯罪的,我想我如果进了公安局,这一辈子就完了,我虽然不想象父母想象的那样出入头地,可我也不想去做个坏人。
但是,在乞丐里边呆着,很容易人就变了,因为他们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老师以前总对我们说,做人不能没有是非感,我一直搞不明白什么是是非感,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做乞丐的人就是缺乏是非感,因为在正常人看来是对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错的。
在他们看来是对的东西,在正常人看来肯定是错的,是不能接受的。
这一点我感受太深了,我跟那个老乞丐说这些,他一边嫌我烦,一边让我赶快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接我回去,他说,你这样爱问问题,在这个圈子里是很危险的,要吃亏的。
结果,我正在犹豫着想给家里打电话时,天津市开始清理整顿市容,我被带到了收容所,然后,被遣送回济南,这次我在外面流浪了四个月,也算尝过了做乞丐的滋味,我知道了人要为自由付出代价,而且,人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我现在觉得对不起爸妈,他们对我真是太好了,我原来不知道为什么总想伤害他们,一想到他们会为失去我而难过,我就忍不住要跑掉,是他们无条件的宠爱把我惯坏了,我总想恶作剧。捉弄他们,我是不是很坏的孩子?
我不敢保证我将来会不会再次离学出走,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对家对父母又感到烦了,忍受不了我就会跑,我想我已经很难管住自己,可是,我真的不想学坏,我想当个既不那累又不那么坏的好人,真的。
采访者思绪:
与姚成交谈的时候,他的妈妈一直在旁边擦眼泪,这个30岁才返城自谋生路,好歹创下份家业的女人,看来实在是为这个儿子操碎了心。
可无论他们夫妻怎么的无条件服从,小心翼翼的照料,儿子的脑后还是一片反骨,这个迷恋流浪的孩子终于过了一把当乞丐的瘾,带着满身的尘土和黑瘦的面孔又回到了家,可他的心灵是否也落满了灰尘,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虽然他同我的谈话因为他母亲的在场显得吞吞吐吐,迟迟疑疑,可他流畅的叙事能力,清晰的思维定势却使我感受到他的聪明,做为一个16岁的少年,无疑他应该算是同龄人中比较成熟的一种。
显然,这种流浪的经历已使他更加早熟,社会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使他的本质显现出来,在许多选择中,他还是很明确的选择要做个“好人”,这对姚成父母来说该是多么欣慰的事情。
是啊,做好人又不累是许多人的愿望,问题是这种机会到底有没有。
姚成离家出走做了四个月的乞丐是回事儿,可他为什么要放弃那么舒适的环境和父母无微不至的爱一次次远去,这更是一回事儿,对于我来说,我更看重后一个问题,虽然这有,久老生常谈,可我们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这是个并非话外的问号。
姚成的父亲我没有见到,他妈妈告诉我,丈夫在家烧儿子爱吃的菜,他知道儿子在外边流浪了这么久,肯定没吃过什么象样的饭菜。看得出姚成的母亲对儿子的归来有些喜出望外。她甚至没有责备儿子一声,只是不停的替儿子拽拽衣角,擦擦脸上的污垢。
已经长得比母亲还高的姚成显然已不太习惯这种抚爱,他的尴尬他母亲浑然不觉,这让我突然明白了姚成为什么与父母总要背道而驰,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相互了解和认识。
这无疑是现在许多家庭存在的痈疾,父母呕心沥血为了孩子,孩子却总要做出让他们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举动,譬如几次离家出走,甚至16岁便已经有了做过乞丐的经历的姚成,这已经并非是传奇。
第十二章
坐在11层的办公室里,老板台后面的他透过茶色玻璃的建筑幕墙,俯瞰下面街道上如蚁的人群,他笑着说10年前做乞丐时用的手推车他还留着,那皇他永远不会丢掉的东西。
——当过十年乞丐的今日企业家。
认识他是在一次企业家联谊会上,那一次到会的几十名大小企业家中,他50多岁,沉稳持重,一身乳白色的西装,浅灰的领带,得体的举止,惹得众记者频频与他接触,抢了不少风头。
我代表报社与他约好采访时间,但是,我非常幸运的知道,在我自己创作的书中,他是一个撞上来的目标,他的经历谈得上是真正的传奇,说得通俗一点,他是真正的从乞丐到富翁。
但是,由于事情已过去太久,加之他本人的身份与原先已经有天壤之别,他虽然不并算讳言过去的饥寒交迫,但在称呼上他说自己以前是拾荒者,也就是捡过破烂,而且,一捡就是10年,当然,一开始从四川来到北京时,他是一路乞讨而来,我想这两者本来就没有那么清晰的区分。
乞丐通常意义上以要两种生活为生,一种是乞讨,另一种便是拾荒了,另外还有一种是顺手牵羊,所以,它们之间是很难有概念的清晰,索性就不去管它。
因为他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所以,我只能赶快的让他口述,我来实录。
“我今年正好50岁,是49年生的,所以,不用告诉你,你都会猜到我的名字里肯定有个”国“字,我们那波儿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名字。但是,我们这波人幸运的并不多,国家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因此,说吃苦我们最有资格了。
我老家是四川成都的附近,那是个盛产竹子的好地方,我们那里生产的竹器非常有名,但是,过去不准搞副业,所以渐渐的手艺人都远走他乡了,慢慢地没人会再用这种办法赚钱。所以,我们那里穷得远处有名。
我兄弟四个,我排行老大,理所当然的得挑起家里的大梁,所以,我一天书都没读。
七、八岁便跟着乡亲出去做贩盐巴和大米的生意,一直到16岁,我才第一次穿上了布鞋。
18岁我同几个兄弟砍来了竹子,回家盖了新的竹楼,砌了新的火灶,可是19岁我便被公安抓了起来,说我私贩盐巴,投机倒把,判了我七年徒刑,等走出监狱我已经是26岁的人了,家里的兄弟都用我当时留下的钱娶了亲,而我这坐过大牢的人没人敢嫁,我一气之下便离开了家乡,到现在再也没回去过。
我到了成都,可当时的人都保守的很。一听我坐过牢也不分青红皂白什么地方也不留我做工,我在街上奔波了几天一无所获,最后只得拾垃圾箱里的烂菜叶吃。我那时还年轻,血气也旺,一心想找个地方做工挣钱发家,可是,那会儿是1975年,到处都是搞运动的人,经济也不发达,尤其是成都根本没有什么机会,为了填饱肚子,我开始捡破烂,收废纸,慢慢地赚了点钱,三年以后我回老家盖了竹楼,也娶上了媳妇,准备过安生日子。
可是1979年,一场大水使大半个四川省都受灾,我们那里成了重灾区,我新盖的竹楼在山脚下被冲得七令八落,媳妇在竹林里生下了我儿子,我们一家三口上无片瓦,下无寸地,31岁才得子的我内疚得几乎要去死,我想我这个人真是没用。连老婆孩子都安顿不好,我还算是什么男人。
当时,媳妇和没满月的儿子,还住在部队的帐篷里,我便拿着一根肩担,两条麻绳走了,我要出去闯世界,直到我能给她们一个象样的家。
那一年四川到处发大水,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处是灾民,根本没有人做生意,我又找不到事情做,连破烂也没得捡,我就是要饭也吃不饱,这时我听许多人讲,北京那地方有好大,在那里有的是活儿可以干,我把扁担、麻绳扔了,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火车票,从成都来到了北京,那是1980年。
在火车上颠簸了两天,我水米未进,到了北京下了火车便头晕脑涨,不知往哪里走好,我突然害怕起来,我一个外乡人,身上分文没有跑到北京来了,那时北京在我心里是最神圣最伟大的地方。
在火车站的角落里呆了两天我才敢试着往城里走,因为我已经四、五天只喝凉水没吃东西,我想就是要饭我也要到天安门去看看再回成都。
我那时头发、胡子老长,衣衫褴楼的不象个人样子,人人见了我都绕着走,我始终没有勇气走到天安门广场去,我怕警察怀疑我不是好人,把我抓起来送我回四川。
那时候北京管的也特别严,外地人很少有在这儿打工的,我问了几家建筑工地,人家都怀疑我的来历不明,不肯让我留下做工,我东游西逛的没办法蹲在墙角讨开了钱。
那会儿老百姓手里都没什么钱,每天讨个毛儿八分的刚刚够吃饱肚子,我想这下没指望了,如果这样讨下去,我讨到死也无法给老婆儿子一个交待,在北京讨钱我觉得自己是活得一点脸面也没有了,想想真是不甘心。
正在我绝望的时候,有一天我无意间拣到了一辆几乎无法再推着走的小孩推车,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那只不过是因为长期不用,小推车的轮子全部生锈了的缘故,我高兴极了,三弄两弄便把小推车修好了,我想我要用这个推车来做点事,哪怕是捡破烂。
北京那时的治安很严,大街小巷白天根本看不到捡破烂的,我也不敢轻易上街。一般都是晚上12点以后,我才推着小推车溜进居民区去掏那些垃圾,因为天黑我什么也看不清,只得摸索着装一车回到我住的地方,然后才去装一车,一晚上推个三四车,然后,白天我就仔细的翻拣,能够卖钱的纸和玻璃瓶都拣出来,真正的脏东西全部扔掉。
好在我那时住在农民房里,出了门就是沟,剩下的垃圾我都扔在那个沟里,几年下来我都把那个沟填平了,你说我得掏了多少垃圾。
开始这事就我一个人干,可慢慢地见我赚钱了,有些乞丐便也开始掏垃圾,居民楼里的老太太发现了我们这些夜里的拾荒者,报告了派出所,我们便被警告不准再进去掏垃圾,反正,北京大得很,这里不让进了,我们再换个别的地点儿,这样我一干就是三、四年,钱是赚到了一点,可要是想回趟老家还是不行,我舍不得把钱交给铁道部。
这时北京已经改革开放了很长时间,经济也搞活了,市场也繁荣了,外地人也多了,什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