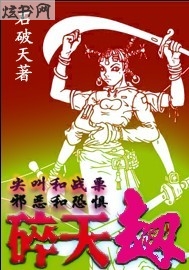花魁劫-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贺敬生之名与贺氏集团的威势,七十年代初期,简直震撼香江,人人趋之若惊。
故而贺家挑的儿媳妇,还会差到那儿去?
贺聪娶的是本城另外一个世家,阮云龙的十二小姐阮端芳。
阮家是著名米商,战前发的迹,战时更叱咤风云,战后的那十年八载呢,虽不如前的显赫,然,烂船尚且有三斤钉。
阮云龙本身一妻三妾,这十二小姐的娇贵在于嫡出。更得其母阮柳氏的宠爱,只为她最小,这其间的关键可大了。
理由简单得很,那怕阮云龙沾花惹草,三妻九妾,那起骚娘子,野狐狸且别自以为一旦迷倒了阮家老爷,他就会从此专心一志,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绝对没有这回事呢,还不是随他本人心情意趣,遍洒雨露,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阮柳氏怀了阮家十二小姐时,比她生下阮家的大少爷还要欢欣荣耀百倍。
这个恩宠不衰的铁证,使其余小妾,一律面目无光。
闺房恩爱,既是无人独专,那么,论到名位上头,正室自然更光芒四射,锐不可当。因此,阮十二小姐端芳从小就在阮家当公主般养。
嫁给贺聪之后,一举得男。且还陆续又生了两位少爷,使贺敬生乐不可支。
至于聂淑君,不消说,因有我的出现与存在,下意识地更喜欢炫耀门第家风,标榜明媒正娶。尤其阮端芳是正室晚年所出,更间接地帮助聂淑君出一口乌气。于是,对这儿媳妇,绝对的恩宠有加,呵护备至。
贺聪与阮端芳的三个儿子,比贺杰大几岁,现已分别在美国各有名大学就读,全部专攻商料。
看见这贺阮端芳的际遇,就真不难明白,女人的幸福完全主宰在命运之神手中。
谁一出生,就已口含银匙,谁又能一直金枝玉叶、万千爱宠地由父家转至夫家去,都是命定的,强求不得。
敬生的次女贺敏,适上官怀文。
上官家并不算显赫、贺敏嫁时,怀文只不过是港大毕业生,考进政府去当政务官。然,多年力争上游,官运享通、现今跟我一般年纪,已是政府内的红人,官职司完。
上官怀文与贺敏夫妇俩合起来、正好是富贵双全的一幅牡丹图。但见他们不时出席官绅云集的晚宴,即成影视画报周刊的抢镜人物。
若硬要挑他们的美中不足,那就是多年以来,膝下犹虚吧!
贺敏口里总不说什么,在大家庭内出身的人,根本习惯凡有忧喜之事,最上算还是三缄其口,免得惹人闲话。
所谓饱暖思淫欲,富贵人家,闲着的时间一多起来,就作奸犯科去,最流行的罪案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广播别人的苦与乐。要杜绝这种祸患,谈何容易?只有尽量不提供资料,所以人们没有凭借可以小题大做。如仍有无是生非的情况发生,则是防不胜防,只叫没法子的事了。
中国人传统的幸福家庭,一定有人传宗接代。所谓牡丹虽好,仍须绿叶扶持。
贺敏与丈夫,就是光秃秃的两枝牡丹,在人们眼中,也许是比较突兀的。
当然,贺敏的境况在一般人心目中,还要比贺家三小姐贺智来得幸福。
富家小姐们,在婚姻上头,全都是低不成、高不就。有人要高攀,她大小姐未必青睐。轮到贺智考虑迁就,对方根本没兴趣。
这年头,虽多耍尽手段谋求飞黄腾达之徒,也还有不少不屑裙带尊荣之士!
事实上,做贺家的二姑爷又比较上容易适应一点,毕竟贺敏没有出来社会做事,彻头彻尾,专心一志的当家庭主妇,这个单纯的身份,总易于讨好。
贺智不同,她自美学成之后,立即一头钻进贺氏企业去,非常投入于财经行业。
贺敬生任主席的两间上市公司,一间是专营金融经纪业务的贺氏集团,另一间是管辖发展地产的顺兴隆。现今,后者就由贺智一把抓。年来,在商界已甚负盛名。
一旦成了企业明星,品性自是硬朗,加上女强人的形象,通常很能吓跑有心求偶的君子,于是票梅已过,仍然待字闺中,实在跟贺智的相貌完全扯不上边。
贺家的四个孩子虽非临风玉树,国色天香,但出身与教养,往往能营造出高雅得体的风范与气质,很自然的非同凡响。
不是不可惜的。
私底下,敬生和我都颇替贺智叫屈。如果她不是贺敬生之女,不是顺兴隆的副主席,我相信,她老早就有个暖洋洋的幸福小家庭了。
大概每个人都有个暖洋洋的幸福小家庭了。
大概每个人都有他的选择,贺智跟她姐姐一样,从未试过在人前轻轻叹息。人海江湖内,各行各业各个圈子,都尽是惊涛骇浪,不一定在欢场才易见凶险。身处其间的人,无不步步为营,小心翼翼,谁个一下疏忽了,把时间用在长嗟短叹上头,轻则表现立即落在人后,重则招致难以预测的后遗症。
贺智明慧,一定晓得这番道理。
女人也就是在这男女私情上老吃亏。像贺智,一旦在豪门穿梭,在企业茁壮,就得在阴阳协调一事上让步了。不比男人,像贺家的四少爷贺勇。,三头六臂,既在父亲的羽翼下长袖善舞,又于欢场中左拥右抱,顾盼生辉。成了本城数一数二,最具名望的花花公子。
贺勇根本没打算结婚,他父亲催促他时,答说:“自盘古初开起,男人就是无女不欢,崇尚三妻四妾,乐此不疲,倒不如干脆打开婚姻的枷锁,放生蛟龙,让自己优游自在,为所欲为。”
贺勇还嬉皮笑脸地逗聂淑君说:“妈,你已有男孙三名,大嫂既已超额完成责任,你就免了我吧!”
任何人都拿这贺勇没办法,反正他在生意上头,把贺氏财务打理得头头是道,贺敬生也没什么话好说了。
每念到聂淑君的孩子们,老早在贺氏集团内生了根,我的心就直往下沉。
贺敬生的第二代与第三代,都在励兵秣马,磨拳擦掌,准备继承父业,在父亲的王国内争一日之长短。
轮不到我不惊心,不动魄。总有一天,贺杰要跟他同父异母的兄姐较量。
谁得谁失,象征着我和聂淑君权力斗争的最终胜败,无法不令人提心吊胆,虎视眈眈。
贺杰在长途电话里跟我说:“妈,是不是一定要我回来跟爸爸拜寿呢?”
“杰,你不想回来?”
知子莫若母,贺杰从来最怕出席贺家的喜庆场面。我当然明白他的苦衷。
站在一大堆聂淑君名下的亲朋戚友之中,我们母子俩是显得额外的孤伶伶的。
男孩子长到十五、六岁,正正是尴尬时期,一般情况下已不喜欢跟在父母身边出席应酬场合,更何况贺杰有如此不寻常的家庭背景。
我并非勉强儿子之所难,每要鞭策骨肉,自已心头往往先来一阵翳痛。
然,贺杰必须适应。我看准了在不久的将来,他就得加入贺氏集团,跟贺家的人更紧密的相处,甚而交锋。他逃避不了。
敬生从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有关遗产的分配,我也没问。
只是有一晚,我陪着他在露台看月色,他突然握着了我的手,问:“可记得从前,我每晚都到大同酒家接你下班,二人手牵手,在海旁漫步,举头望见的那轮明月,就跟现今的这个一模一样。其实,已经过尽二十多年了。”
我但笑不语。忆及前尘,感触大多,不谈也罢。
敬生依然情深款款地望着我:“你觉不觉得我老了?”
“你老了,我也老了,我们不就是老夫老妻!”
“不!你只是越来越成熟优美,认识你的那年我快四十岁,并不觉得彼此有不可接受的年龄差距,可是,如今……”
“都一样。你别胡思乱想。”
“你安慰我而已!总有一天,我要拋下你孤伶伶过日子,你就知道不一样了。”
“再说这种扫兴话,就太辜负良辰美景了。”
“我们需要正视现实。小三,你放心,纵使我遽然而逝,你下半生还是够享够长的。然,也要看你的本事及定力了。我深信你能应付得来,尤其为了贺杰,你的能量不可轻视。”
我没有追问。
敬生的脾气,我非常清楚,他肯说的话,不会收藏在肚子里;不肯讲的,任谁也无法使他屈服。
自那晚,我意识到敬生一定是要我带着贺杰,在他千秋百岁以后,仍在贺家撑下去。我虽没把这个猜测给贺杰提起,然,在行动上,我益发要迫使他好好正视贺家五少爷的身份。
我不容许他逃避,也不认为他需要自卑。
从敬生带我走进贺家来的那一天,我们母子就是名正言顺的贺家人了。
连聂淑君都已喝过我的一杯茶,好歹算把我承认了,旁人休得不尊重我和贺杰的身份。
杰仍在长途电话里支支吾吾,老给我解释,大考在即,不愿回程。
我咬了咬牙根,回头征询了敬生的主意,听到他说:“考试要紧,暑假才回来好了!”
我才放过了贺杰。
贺敬生的两头住家,其实是同在一条街上的两栋洋房,座落在薄扶林的沙宣道。
本城富豪住在这区的不多,贺家邻近是霍家、周家与赵家。敬生之所以买下这两栋洋房,则他个人对港岛西南的特别偏爱。
这两栋洋房,占地甚广,以每尺买入价而论,足足比市价便宜百份之三十。最难得的还是千金难买相连地。尤其敬生的环境,妻妾住在同一栋房子,朝见日晚见面,必定更多争执。若住得太远,害他两边奔跑。也是劳累。
如今的格局最为妥当。每晚除非有业务应酬。否则敬生和我必到聂淑君的房子去吃晚饭。饭后,我陪着他散步回到我俩的房子来。
这一夜,敬生回到家里来后,仍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小三,你来,我有件小东西送你。”
我笑盈盈地跟着敬生,走进书房去。
我有一个脾气,数十年如一日。对敬生的财产与生意,从不积极表达半点兴趣。连这放在家里的夹万,我都敬而远之。
我崇尚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道理。
如今我名下的物业,有价证券、外汇、珠宝,全是敬生在这二十多年来,陆续而主动地送给我的。
每个月贺氏集团给我一张基金投资管理的月结单,我都懒得多望两眼。
事实上,跟着敬生的这些年,老早看惯三更穷五更富的情势。本埠的富户,风云变幻,莫测高深,我都已见怪不怪,不大动心了。
单就是七三年股市狂泻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身为首席经纪的贺敬生,也遭遇过现金的周转不灵呢?
那一夜,对了,敬生辗转反侧,摹然握住了我的手,竟都是冷汗。他喃喃地说:“小三,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说:“商量些什么呢?你管自拿主意便成!”
“不。那些到底是你名下的资产,既给了你,就是你作的主,必须得你同意才能挪动。”敬生的表情痛楚:“我真没想过会输得这么惨!由七干点直跌破一千点,我仍能撑得住,反正是输掉了以前赚下来的钱罢了,谁会想到,八百点入货,仍然要出问题,再人货,再跌,直跌至三百点,差不多把一副身家押进去了,如今还落得这么个收场。”
我没有造声。
轻轻地吻掉了敬生脸上的泪。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唉!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真是的,谁会想到股市会有如今这百五点的收场?
“敬生,我本来就无一物,到大同酒家去上班时,口袋里只有一块钱,那袭旗袍还是预支月薪缝制的,每夜里回家去就要立即脱下来洗净,晾起来才敢上床睡觉,兔得翌日干不了。想想,纵使你现今把曾给予我的都拿回去了,跟那时比较,我仍然拥有很多。”
“小三!”敬生抱住我。
我稍稍推开了敬生,温柔地望住他说:“你断不会连我那一衣橱的旗袍都拿去典当了吧?”
“不!”敬生感动地说:“没有人穿起旗袍来,比你更好看!”
“那好,我要旗袍,你要其它!敬生,”我非常有信心地说:“我不懂股票,但女人有第六灵感,我觉得如果仍会在现今的一百五十点跌下去,也未免太过滑稽了。”
就是这样,我授权敬生,把他多年来赏赐我的一应资产,全部变卖,重整河山。
就这样,我带所有的旗袍和年纪小小的贺杰,带着群姐,搬离了跑马地蓝塘道几千尺的自置物业,以八千元顶手费用,将中环坚道一层千尺的唐楼承租下来,重头整理出一个象样的家来。
我并不觉得自己慷慨。那些年来,敬生自动给我安排资产,于我,只不过是账面上的游戏而已。我没有数股票与银纸的怪癖,也从不巡视那些散布在铜锣湾、北角与湾仔的物业,每个月的家用还是那笔数字。从跟在贺敬生后头的第一天,情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