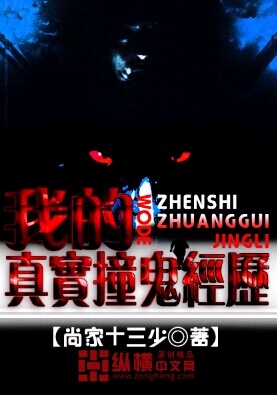幻色江户历-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搞不好……)
他们会认为阿信是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媳妇,当场写下休书!
万一事情演变到这种地步,肯定没有人会出面阻止。门不当户不对是造成离婚的根源,但是那不是专指门第而已。阿信认为,那也包括引发不必要的嫉妒或争执等,也就是外貌不相配的这种事。
若作祟消失了,我便无法继续当木屋的媳妇。
也就是必须跟繁太郎以及可爱的小姑们分离,也将结束少奶奶的日子。不仅如此,他们大概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何会迎娶阿信这种女人当媳妇,最后大概会对阿信指指点点,边嘲笑边将她赶出木屋。
因为,我比久美更丑,丑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啊,到时侯自己一定会受不了。阿信很喜欢木屋的人。她喜欢繁太郎,也喜欢七兵卫和阿文、阿静、阿铃,以及阿吉。
她不想离开这个家。
“所以嘛,我才在你面前出现。”久美过意不去地喃喃自语。“对不起啊……要怎么做,都由你决定好了。”
久美留下这句话便消失了,阿信则打着哆嗦惊醒过来。
之后,阿信感到十分痛苦。
在她的日常生活之外沉积着令人心痛、难过的感情。作祟还是不作祟,只有阿信能决定。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每当阿信与繁太郎并肩走在八幡宫祭典市集,内心充满幸福时。就会不经意地想起脸上挂着泪痕、垂头丧气的阿静。那种歉意和利己的感情纠缠在一起,总令阿信感到走投无路。
阿信有时也会凝望着有如小鸟般只吃—点东西、成天悲伤地躲在卧室的阿铃而下定决心,认为不能再这么下去,即使会被赶出这个家,也一定要除去作祟。可是,往往不到半个时辰,阿信又会想到。一旦离了婚,阿爸就算做到弯腰驼背,大概还是得一直挑着担子叫卖蔬菜,而自己也会坐在堆积如山的订做或缝补衣物中,毫无乐趣地老去,一想到这里,阿信就动摇了。她会觉得,啊,只要我装聋作哑就没事了;只要告诉阿静和阿铃,对女人来说容貌根本不重要,让她们尽量快活过日子就好了。这样一来,她就又不想放弃目前的生活。
如此大概过了—年,阿信怀孕了。
木屋的人得知长孙即将出生的消息时,高兴得天花板几乎要塌了。所幸,阿信的身子在这方面也很健壮,孕吐不严重,顺利地怀胎十个月,分娩时间也不长,生下了皮肤白皙、在阿信眼里简直像是人偶般可爱的女儿。女儿取名为“道”。阿信簌簌地流下幸福的眼泪。
然而——
“看来,孩子似乎长得像我这边了。”听到繁太郎苦笑着如此喃喃自语时,阿信暗吃一惊。不仅繁太郎,木屋的人反应都差不多。因疼爱长孙,大家在人前不会那样说,但阿信听到公婆和阿静、阿铃在暗地里窃窃地说:“啊,要是像阿信就好了。”
“好可怜。长得跟我们一样。为什么不长得漂亮—点呢?”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婴儿愈长愈大,喊她的名字“阿道”时,她也会笑了。不久,她开始会爬、站立,然后开始走路……
孩子会逐渐长大。阿信内心对此感到很担忧。孩子将长成妙龄姑娘。而且,这样下去的话,等孩子懂事了,也会跟阿静和阿铃一样,因自卑而难过,接着大概也会错过眼前的幸福。事实上,正值花样年华的阿静,对多得数不胜数的提亲全部拒绝,她就跟当初繁太郎来提亲时的阿信一样,她说:“看中容貌想娶我?那一定是开玩笑的,你们就拒绝吧。不要管我了。”然后每天哭泣。
对不起啊,阿信在心里向两位小姑道歉。对不起啊。你们的痛苦,正是阿道将来的痛苦。
事到如今,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了。我大概将会被赶出这个家,而繁太郎或许会休掉我,可是,即使这样也无所谓。阿道将来的幸福比较重要。
因此,阿信在院子摆设石灯笼,也在石灯笼下埋了蘑得光亮的镜子,祛除久美的作祟。
后来事情变得如何?
结果是:什么都没变。阿信不但没有被休,而且与繁太郎依旧过着亲亲热热的日子。阿静和阿铃则完全恢复了活力,再过不久,阿静也因对方恳切的求亲,即将嫁进旗本家。两人与阿信的交情一直很好——与昔日无异。
阿信依旧受到木屋大伙儿的敬爱和疼惜。
阿信请来磨镜的人将镜子磨得光亮,她照着镜子,有时会这么想:看吧,我或许也会渐渐变成美人吧?
注一:一贯为三点七五公斤。
【浴兰 皋月 夜着之鬼】
一
据说,庄助在马喰町旧衣铺找到那件夜着(注一),是稻荷屋过完每年惯例的七夕祭的第二天。
稻荷匿是家小酒屋,在深川小名木川的高桥东边桥畔静静地挂着招牌。铺子门面小,只要十个客人就足以挤得邻座的人手肘互碰,但因这家铺子已是老字号,光老板五郎兵卫一个人常忙得慌手慌脚。
庄助在稻荷屋帮五郎兵卫做事以来,这年夏天刚好是第五年。至今有关庄助的独居生活,五郎兵卫很少过问,但这回对庄助在旧衣铺买了夜着一事,却有点好奇。因为是平素沉默寡言的庄助主动提起的,而且他当时的表情显得格外高兴。
“老板,那看起来像是新的。是用上等麻布做的,盖着睡觉,干干爽爽的很舒服。”庄助如此说道,很得意自己买到好货。
庄助虽是个三十过半的大男人,有些地方却像个涉世未深的孩子。五郎兵卫当然深知这一点,但还是觉得有点怪。不过是一两件夜着,为什么这么高兴?
“喂,庄助,你是不是打算成家了?有了喜欢的女人,才买新夜着吧?”
五郎兵卫一边搅拌凉菜的调味味噌。—边套话,庄助耳朵微微涨红地摇着头说:“没那回事。要是有的话,怎么可能不告诉老板?我虽然很笨,但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家伙。”
庄助突然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明明没必要,他竟然四处搬动给客人坐的旧酱油桶。五朗兵卫扑哧笑了出来。
“已经扫过地了,你别再弄得到处是灰尘。你刚刚为什么转过去那边?”
“对了,我是想挂帘子。”
耳垂还涨红的庄助,搬下沉甸甸的绳帘走了出去。五郎兵卫强忍着笑。
那晚,庄助没有再提起“好货的夜着”。庄助本来就是一见到客人反而比平常更寡言的人,再说,五郎兵卫也没放在心上。话虽如此,五郎兵卫仍记得,自己当天边做生意边用眼角观察庄助。
(果然是发生了什么事。)
五郎兵卫怎么看都觉得是这样。他好几次看到庄助脸上一副幸福的模样,不论是送酒给客人或收拾盘子时,嘴角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浮现微笑。
那晚,铺子打烊后,五郎兵卫回到老伴儿阿高和独生女阿由等着的住处时,对庄助那暗自微笑的表情仍挥之不去。庄助的那个笑容,无邪、坦率且充满喜悦,五郎兵卫一想到不禁也浮出类似的微笑。
“你也真是的,怎么—个人边想边笑?”
“阿爸,你有毛病!”
在座灯旁紧挨着头缝制窄袖服的老伴儿和女儿,分别这么说道。
“唉,对不起。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五郎兵卫虽然觉得把庄助当成下酒菜有点过意不去,但毕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干脆就说出来吧。于是。五郎兵卫将庄助在旧衣铺买到麻布夜着的事,告诉了老伴儿和女儿。
“原来是这样。”阿高笑了出来,“庄先生一定有喜欢的女人了。这不是很好吗?”
“你也这么认为吗?我也这么认为,所以问了庄助。”
“难道他说不是?”
“耳垂都涨红了。”
阿由—听也微笑着说:“这点倒是很像庄先生。”
今年春天满十八岁的阿由,是五郎兵卫和阿高引以为傲的女儿。连说话刻薄的大杂院管理人都这么说,到底要怎样扭转你们夫妻的哪个地方,才会生出那么漂亮的女儿,实在想不通!
只要是说女儿好,别人那样说。五郎兵卫也不会生气。甚至他有时也会这么想,管理人说得没错,对他们夫妻来说,那的确是个容貌过于出色的女儿。
等今年夏天—过,秋风刚吹起时,阿由将嫁给川崎的一家干货大批发商。五郎兵卫的稻荷屋,只有那家批发商的招牌大。虽然两家的规模相差悬殊,但五郎兵卫认为,那没什么,反正自己的女儿到哪都不输人。
(我过去的苦没白吃。)
望着女儿的脸,他可以坦荡荡地这样想。五郎兵卫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父亲。
二十年前,五郎兵卫三十岁那年,独立经营稻荷屋。当时铺子比现在小,与其说是小酒屋,倒不如说是比摊贩稍好些要来得恰当,所以五郎兵卫一个人也照顾得来,但赚的钱也仅够他勉强糊口而已。
阿高是当时五郎兵卫进货的一家酒批发商的下女,因而与五郎兵卫认识。稻荷屋开店约—年后,两人才结为夫妻,当时两人费心商讨后,决定拜托阿高铺子的老板让她继续待下来,而五郎兵卫则负责经营稻荷屋。不久,阿由落地了,阿高依旧背着婴儿做事。那时日子仍苦得不得不这么做。
为了糊口过这样的日子,这对夫妻不知不觉竟也习惯了,二十年后的现在,即使稻荷屋的生意好到需要雇庄助帮忙,阿高依旧在酒批发商当下女,至今从未以老板娘的身份出现在稻荷屋。因此有些老主顾以为五郎兵卫仍是个单身汉。
每天天亮前起来一起吃过饭,阿高便到酒批发商做事,五郎兵卫则前往鱼市。晚上,五郎兵卫关上稻荷屋,从高桥桥畔通过两个町大门回到家时,阿高也回来了——大致都是这样。然后一起吃很晚才吃的晚饭,之后就寝。
然而,正因为阿高二十年来都在同一家铺子认真工作,才有阿由这回的亲事。这是阿高做事的那家酒批发商老板提起的。对方的干货批发商与阿高工作的铺子是老交情。这门亲事,阿由要嫁的少爷是日后的继承人。
这门亲事对阿高做事的那家酒批发商来说也很重要。老板认为,既然是阿高的女儿,一定没问题。而老板会这么说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阿高做事向来尽心尽力。虽然她是通勤下女,但是在铺子的下女中地位最高,掌柜们也对她另眼看待。过了七十七岁生日退隐的大老板身边琐事也都让阿高负责。他说非阿高不可。
话虽如此,阿高是个懂分寸的女人,最初老板提起这门亲事,她说不能擅自答应拒绝了。阿高说,我家女儿不是那种当少奶奶的人。
阿高认为反正—辈子都得做事,很早就费尽心思让阿由学得一技之长。因此,阿由现在已有一身卓越的缝纫技术,甚至往后可以靠此为生。但是另—方面。则完全没有让阿由学习礼仪方面的事,就这一点,阿高便不能答应这门亲事。
可是,酒拙发商老板和提亲的对方,都不轻易就此作罢。问了原因,才知道对方那少爷——也就是阿由日后的夫婿——本来就不打算娶只懂得礼仪规矩的花瓶女人,他希望娶个能和他一起管理铺子的聪慧媳妇,而且,当他听到是下女总管的女儿时,最初有点迟疑,后来偷偷看过阿由,据说所有犹豫全都一扫而空。
因此,首先是阿高被打动了,当亲事逐步谈了之后,接下来是五郎兵卫,最后连当事人阿由也被打动,才定下了这门亲事。
夫家送来十两巨款,说是给阿由准备嫁妆。眼前阿高和阿由忙着缝制的窄袖服,正是用那笔钱买的布匹。五郎兵卫认为出嫁前会很忙,干脆花钱请人缝制,但是阿由不肯。
“太浪费了。”阿由说道,“再说,我也可以练习针线活。我要自己缝。”
因为新娘嫁衣必须配合对方,无法由这边擅自决定,所以此刻媒人酒批发商老板夫妇正用尽心思替阿由准备。大概会订制与阿由相称,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新娘嫁衣吧。—想到此,五郎兵卫总觉得心里像是注入了热水。那热水,有时温温的,令人很舒服,但有时又稍嫌太烫,甚至会刺痛五郎兵卫的内心深处。当他想到阿由将离开身边时,有时会觉得像是划开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不行,不行。)
此时,五郎兵卫会努力说服自己。
(阿由抓到了意想不到的幸福,应该为她高兴才对。)
由于是母亲老板那方做的媒,万一阿由不满意对方,反倒会害了阿由。五郎兵卫和阿高起初很担心这一点。但阿由只是单纯地接受对方少爷的感情,似乎逐渐喜欢上对方了。这点让五郎兵卫非常高兴。
不知是否阿由比较晚熟,至今从未表示有意中人,再说,她本来就看似与恋爱无缘。虽然别人都说明明长得这么漂亮,但老实说,五郎兵卫曾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