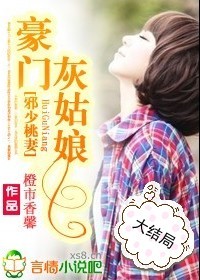忧伤黑樱桃-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的餐具,给他们拿来了更多热带饮品。他们寻欢作乐的兴致丝毫不减。他们隔一会儿就离开桌子,然后又从房间的滑动玻璃门回来。最初,我以为他们只是去盥洗室,但是后来,看到一个女人回来时,用她的指节触了一下鼻孔,用力吸着气,似乎一粒沙子进了她的呼吸道。十点时,服务生开始用一个长把筛子,把树叶捞出泳池。接着,我看到玛伯斯示意,让服务生去拿更多的饮料。服务生看了一下手表,拒绝地摇了摇头。他们又在外面坐了半个小时,吸着香烟,变得安静些了。他们从玻璃杯底吮吸着一个个冰块,两个女人倦怠的面孔看来很讨人喜欢。
突然,一阵雨敲击着汽车旅馆的木瓦屋顶,哗啦啦落在竹子和棕桐叶上,在游泳池里跳动着。魏德林、玛琅斯还有两个女人,都笑着跑向房间的滑动门。我一直等到半夜,他们仍旧没有出来。
我戴上雨帽,走进汽车旅馆的酒吧。这里几乎没什么人,雨滴顺着窗户流下。酒吧间男招待冲着我微笑着。
他穿着黑色长裤,白色衬衫在酒吧灯光的照射下,几乎有点紫红色,黑色的蝶形领结上洒满亮片。我坐进酒吧角落,从那儿可以看到他们房间的前门。然后我要了一杯饮料。
“今晚这里相当空。”我说。
“那肯定是。你一个人吗?”他说。
“现在是一个人。我正在寻找一些伙伴。”我笑着对他说。
他温厚地点点头,开始在一个马口铁水池中清洗玻璃杯。最后问我,“你住在这门汽车旅馆里吗?”
“是的,好几天了。伙计,告诉你,我有过一个伙伴呢。”我呼出一口气,用指尖摸了一下额头。“我昨晚遇到了这位女士,一个学校教师。你相信吗?她来到我的房间,我们开始大声地放音乐。我没和你开玩笑,在我们开始认真起来之前,她用酒把我灌醉,让我躺到了桌子底下。我今天中午醒来时,觉得就像一团火。”我笑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他转了一下头,咧嘴笑了。
“是的,那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说,“你再来一杯饮料吗?”
“当然。”
他转身继续洗他的杯子。他的眼睛很茫然,过了一会儿,心不在焉地用一条毛巾擦干了手,打开柜台上酒瓶中间的收音机,走进后面的门厅。他在那里拿起家用电话,背对着我。对着话筒说着,这样,我就无法在收音机的音乐中,听到他说了些什么。
十分钟之后,一个女孩从侧门进来,坐到我下方的一条凳子上。她穿着莱维牌高跟鞋,一件无背棕色毛衫,圆形耳环。她把湿发晃松,点了根香烟,要了杯饮料,然后又要了一杯,却没有付钱的意思。她说起话来,就仿佛和我和服务生都是老朋友。在霓虹灯下,她看上去还算漂亮。
我没让她感到轻松,我没提出为她的任何一杯饮料付费,也没对她做出任何建议。我看到她在看手表,然后眼光直接瞥向服务生的眼睛。他点了根烟,踱出门,似乎是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不喜欢大厅,你呢?它们都很阴暗。”她说。
“这是个非常阴暗的地方,对。”
“我宁愿和一位朋友在房间里喝点酒。”
“我买上一瓶怎么样?”
“我认为那非常棒。”她笑着说,与其说在对我笑,不如说是在自得地笑。接着,她抿着嘴唇,向我靠过来,并触摸我的大腿。“但是我和丹之间有点麻烦,比如七十五美元的酒吧账单。你可以借我这些钱吗?这样,他们就不会等我一离开这里,就开口跟我要八十六美元。”
“表演该结束了,老姐。”
“什么?”
我从后背口袋取出州长警员的徽章,在她前面打开。
这只是个荣誉徽章,我保留着它,仅仅因为它可以让我免费停车。但是她当然并不知道这些。
“不要再骗人了,回家看电视去吧。”我说。
“你这个杂种。”
“我告诉你,你还没有失败。你想继续留在这里,让他找你的碴儿吗?”
她的眼睛从我脸上转到服务生身上,他正从侧门返回来。她做决定没用多少时间。她从钱包取出车钥匙,把香烟扔过去,碑啪一声合上,踩着高跟鞋,很快就走到外面的雨中。我把徽章举到服务生的眼前。
“这是伊伯利亚教区,但是你都干了些什么?”我说,“你准备为我做些事情,对吗?你非常通人情的,丹。”
他咬了一下嘴角,从我脸上移开视线。
“我碰巧觉得她可以陪你聊聊,于是就给她打了电话。”他说。
“不只是今晚,你不会只在今晚这样。”
我可以看到,他的嘴唇由于牙齿一直咬着,渐渐失去了血色。他从鼻子里吹出一口气,似乎得了感冒。
“我不想惹麻烦。”
“你不应该拉皮条。”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他看着酒吧里剩下的两个顾客说。他们是年轻人,坐在远处角落的桌旁。
“你们的两个女孩在六号房间。你应该让她们出去。”我说。
“等等……”
“照我说的做,丹,别再浪费时间了。”
“那是玛琅斯先生,我不能那么做。”
“时间正在流逝,伙计。”
“瞧,那是你的工作,但我不能搅进这件事情里面。总之,那些女人不会听我话的。”
“那么,你不认为其中一个女孩可能会用鼻子吸毒?或者仅仅是因为她的鼻炎又犯了?”
“好吧。”他说,“我去告诉这些人,现在就关门,然后打电话给房间。然后我离开,从这里脱身,好不好?”
我没有回答。
“嗨,我得从这件事中脱身,对不对?”他说。
“我大概是脑子出了点问题,已经记不请你的面孔了。”
在酒吧服务生给房间打电话五分钟后,两个妓女从前门出来了。一个男人愤怒的声音在身后传来。我打开车上的木制工具箱,取出一条拔树桩用的五英尺铁链。
我把它对折一下,两端缠在手上。链环已经生锈了,在我掌上留下一道橙色的污迹。我穿过石板路,向六号房间走去。铁链碰到我的腿,发出了叮当声。闪电像白色的蜘蛛网一样,在黑色的天空上划过。
魏德林一定以为两个女孩又回来了,因为当他穿着短裤打开门时,面露笑容。在他身后,玛伯斯正在一个吧台旁,穿着睡袍吃三明治。床单和被罩凌乱不堪,通往另一问卧室的过道上,散落着毛巾、潮湿的游泳衣和啤酒杯。
魏德林的笑容消失了,他的面孔突然变得僵硬而光滑。玛朗斯把三明治放回盘子,舔着下嘴唇的伤疤,似乎正在冥思苦想一个抽象的问题,然后走向折叠行李架上一个敞开的手提箱。
我听到铁链发出叮当声,唱着歌在空中飞过,感觉到它一次又一次盘旋在我的头顶,感觉到他们的双手在我面前掠过。我的耳边咆哮着各种声音——墨西哥湾深处的隆隆声;钻塔平台剧烈颤抖并哗啦啦肢解;钻杆从井口爆炸脱离,成了一个红黑色火球。我的手被铁锈来回赠着,留下一道道痕迹;这是用来威胁一个六岁孩子的注射针头里干血的颜色;我抽打墙壁、床单、通往庭院的滑动玻璃门。外面的庭院里,杜鹃花瓣漂浮在明亮的青绿色湖面上。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天早上,阿拉菲尔醒来时,胃有点不舒服,我就让她果在家里,没去学校。我给她煮了半熟的鸡蛋和谈茶,然后带她去食品店。朝阳已经升起来了,路边的树经过一场雨水,显出了亮绿色,桃金娘灌木丛开满紫花。
“为什么你一直朝马路上看,戴夫?”阿拉菲尔问。
她坐在码头上一个线缆轴上,看着我从发动机上拧下一个淤塞的火花塞。
“我只是在欣赏天气。”我说。
我感到她从侧面看着我的脸。
“你感觉不太好吗?”她说。
“我很好,小家伙。我告诉你该干什么。我们开车去商店,看看他们有没有风筝卖。你认为今天能把风筝放起来吗?”
“今天没风。”
“那我们给德克斯买点苹果。你想喂它点苹果吃吗?”
“当然想。”她好奇地看着我。
我们走向山核桃树下的卡车,坐了进去,然后沿着土路,朝十字街头的破旧商店驶去。阿拉菲尔看着脚下。
“那是什么,戴夫?”
“别问那么多。”
她的眼睛眨了眨。
“那只是个链子,把它踢到座位下去。”我说。
她朝地板斜下身。
“不要碰它。”我说,“它很脏。”
“出什么问题了,戴夫?”
“没什么。我只是不想弄脏你的手。”
我吸了口气,停下车,打开车门,从地板上拾起铁链。它们就像涂了一层漆,还没有完全干透。
“我马上回来。”我说。
我沿着河岸向下走,把铁链抛进流水。然后,我在浅滩里的香蒲旁弯下腰,用水和沙子擦洗手掌。我把手插进沙子里,水在我的手腕处汇集。我走回岸上,用草把手上的水擦干,然后到工具箱取了一块布,又擦了擦。
十字街头的百货店里又黑又冷,木制叶片的吊扇在柜台上方旋转着。我给阿拉菲尔的马买了一麻袋苹果,还有火腿片、奶酪、法式面包,算是我们的午餐。
回家后,阿拉菲尔帮我清除绣球花和玫瑰花的杂草。
花床里密布夜爬虫,雨后,它们都到了地表,当我们从土里扯起杂草时,它们在强光的照射下,苍白而肥胖地翻腾着。阿拉菲尔来我身边之前的生活,我几乎一无所知,但劳动一定曾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把我安排的所有工作都当作游戏,快乐、天真、充满热情地去完成它。她以自己的方式,咻咻地用铲斗除去四行玫瑰中的全部杂草,一条眉毛上沾了块泥巴。绣球花和湿土的气息如此浓厚,几乎像是种药味。微风吹拂着前院的山核桃。树阴的外边,邻居的洒水车在阳光下旋转着,一阵彩虹般的雾气飘过栅栏。
他们恰好在中午之前到来。两名拉菲特的便衣侦探坐在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里,伊伯利亚教区州长开着一辆巡逻车跟在后面。他们靠着我的卡车停下车,踏着凋落的山核桃叶向我走来。两名便衣人高马大,他们把外套留在汽车里,徽章佩在腰带上。俩人的枪套里都带着一把镀铬连发左轮手枪。我站起身,从膝盖上拂去泥土。
阿拉菲尔已经停止除杂草,张着嘴巴盯着两个男人。
“你们已经有证据了?”我说。
其中一个便衣的嘴巴里叼着一根火柴杆,一言不发地点点头。
“好的,没问题。我需要几分钟,好吗?”
“你找到人来照看这个小女孩了吗?”他的搭档问道。
他的一只手臂上纹着海军陆战队徽章,另一只手臂纹着一支匕首刺穿流血的心脏。
“对,那就是我需要几分钟的原因。”我说。我拉着阿拉菲尔的手,转身朝屋子走去。“你想和我一起进来吗?”
“靠着走廊扶手站好。”叼着火柴杆的男人说。
“你们这些人能不能谨慎点?”我说,我看着我的州长朋友,他站在后院里,什么也没说。
“你他妈在说什么?”纹身的男人说。
“注意你的语言。”我说。
我感觉到阿拉菲尔的手紧紧贴在我的手心。另一个侦探从嘴巴里取出了火柴杆。
“把双手放到走廊扶手上去,张开双脚。”他说,然后抓着阿拉菲尔的另外一只手,要把她从我身边拉开。
我用手指点着他。
“你在粗鲁地对待这件事,退一边去。”我说。
接着,我感觉另一个男人从背后猛推我一下,推得我失去平衡,冲过绣球花丛,摔在台阶上。我听到他从皮质枪套里抽出手枪,感觉到他的手向下压着我的脖子,同时把枪戳在我的耳朵后面。
“你由于谋杀被捕了。你以为当过警察,就可以让你破坏规则吗?”他说。
我从眼角看到,阿拉菲尔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脸上带着一种从噩梦中醒来的茫然神情。
第二节
他们把我关在拉菲特古老的教区监狱里。监狱的年代非常久远,铁门上有横木,墙壁被漆成蓝灰色。在一间监狱门上,“黑人男性”的字样仍然模糊可见。从新伊伯利亚来的路上,我戴着手铐坐在车后,想弄明白我究竟把谁给杀了。他们的反应是沉默和冷淡,这几乎是所有警察对待一个被羁押嫌犯的态度。最后我放弃了,靠着椅垫坐回去,手铐咬人我的手腕。我看着橡树从窗口轻轻掠过。
现在我被取了指纹,并被拍了照,他们翻走了我的钱包、口袋里的零钱、钥匙、皮带、甚至还有我的肩衣链条。一名警员将所有这些东西放入一个大的吕宋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