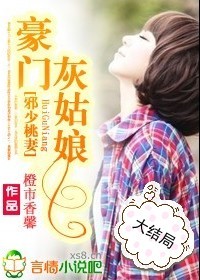忧伤黑樱桃-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迪奥一家是野兽,玛浪斯也是。普舍尔在新奥尔良为一些准军事性的疯子们杀过一个人。我不会低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可能性。”
“普舍尔为什么要杀她?”
他第一次很感兴趣地看着我,我垂下眼睛看着皮鞋,然后回望他。
“我和达乐涅关系密切。”我说,“她知道这件事情。”
州长点点头,没有回答。他拉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一个写字夹板,上面是验尸报告的复印件。
“你对淤痕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她的脖子和肩膀上有淤痕。”
我等着他继续。
“她的头后面还有一个肿块。”他说。
“是吗?”
“但这件事已经定论为自杀。”
“什么?”
“你第一时间知道了结果。”
“你怎么回事?你在怀疑你们自己的验尸报告吗?”
“听着,罗比索,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没有自杀。
另一方面,所有迹象表明,她确实是自杀,她可能用头撞击浴缸,她可能搞得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皮下淤痕。也许你不喜欢听这些话,但是这周围的印第安人不可理喻。
他们酗酒、在酒吧打架、家里人彼此抨击。我并不是在找他们的碴地,我没必要和他们作对。我认为他们只是运气不够好罢了。但那是事实。你看,如果我要怀疑某个人,那只能是普舍尔。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杀她。这个家伙真的被这件事情打垮了。“”亨利·迪奥怎么样?“
“你给我一个动机,你给我确实的证据,我会给你开搜查证。”
“州长,你在犯一个大错误。”
“请告诉我为什么,让我明白一下。”
“你在选择简单的处理方式,你正在让他们溜走。迪奥一家感觉到了你的软弱,他们会把你给生吃了的。”
他拉开办公桌下一个深层的抽屉,拿出了一根警棍。
上面的黑漆已经破裂了,把手在车床上开了槽,并且被钻上眼,扣上了一个皮环。他用力地把它扔到了办公桌上。
“在我接管办公室时,我接替的人给了我这八”他说,“他告诉我:”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进监狱。‘如果那不符合一些人的想法,那是他们的问题。“他捣碎他的香烟,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我想我该走了。”我站起身说,“验尸报告还有其他不寻常的地方吗?”
“在我和医疗检验员看来没有。”
“还有其他什么?”
“我想我们已经结束这次讨论了。”
“得啦,州长,我就快跟您告别啦。”
他又一次瞥了一眼夹纸板。
“晚餐她吃了什么,在阴道里有精液的痕迹。”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用手指掐了掐眼睛和鼻梁,戴上太阳镜。
“你在克莱特斯身上下对注了。”我说。
“你在说什么?”
“他没有杀她,他是性无能。在她被谋杀前,曾被强奸过。”
他吮吸了一下牙齿,对自己笑着,轻轻摇了摇头,然后打开他的报纸,翻到体育版。
“你得原谅我。”他说,“这是我可以读报纸的惟一时间。”
第四节
达乐涅的家人已经在那个早晨取走了尸体,葬礼是第二天下午在黑脚族保留地举行的。第二天是星期六,所以阿拉菲尔和我一起开着车,越过山脉去保留地南端的杜普耶尔。我从当地的报纸了解到,葬礼是下午两点在玛丽亚河上游的浸信会教堂举行。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吃午餐,我没有什么胃口,无法吃掉盘子里的东西。我凝视着窗外尘土飞扬的街道,阿拉菲尔在一边吃汉堡包。
酒吧生意很好,不时有整个家庭无精打采地走进来。前一夜没有休息好的人们坐在路边,他们的眼光茫然,嘴巴像那些安静的、新孵出的小鸟一样张开着。
我看到阿拉菲尔望着他们,眼睛半眯着,似乎一个摄像机镜头正在她脑海里打开。
“你看到了什么,小家伙?”我说。
“那些是印第安人吗?”
“当然是。”
“他们像我一样吗?”
“哦,不完全一样,但是也许你是半个印第安人。”
我说。
“他们说什么语言,戴夫?”
“英语,就像你和我一样。”
“他们不认识任何西班牙字吗?”
“不认识,恐怕不认识。”
我看见她脸上先是一个问号,然后滑过一个困惑的表情。
“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小家伙?”我问。
“我村子里的人们,他们坐在餐馆前面时,就像那边那些人。”她的眼睛看着路边一对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很胖,穿着军鞋和肮脏的运动袜,她的膝盖张开着,这样你可以看见她的内裤。“戴夫,他们不会把士兵带到这里,是吗?”
“把那些想法从你脑子里清除掉。”我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最好相信我的话,阿拉菲尔。在你们村子里发生的事情,不会在这里重演。”
她把汉堡包放在盘子里,垂下跟睛,嘴角向下翻去,刘海在她褐色的额头上直直地垂下。
“这发生在安妮身上。”
我从她的脸上移开视线,感觉到自己在吞咽。天空布满了云,起风了,正在吹动街道上的尘土。太阳看起来,像是南边一个薄薄的黄色华夫饼。
葬礼是在一个木结构的教堂里,教堂的白漆已经起了浮泡,剥落成鳞屑。教堂里除了棺材旁的克莱特斯和迪西·李之外,所有人都是印第安人。他们编着辫子,有着由于劳作起了皱纹的脸,和在零度天气不戴手套加工木材的双手。棺材用黑色金属制成,用白色丝绸镶边并加了衬垫,安装了闪闪发亮的黄铜把手。她的头发在白色丝绸的映衬下显得更黑,脸上擦了胭脂,嘴巴红红的,似乎她刚刚喝了凉水。她穿着驼丝棉衬衫,戴着有一只紫色玻璃鸟的珠状项链,玻璃鸟的翅膀伸展着正在飞翔,停在她的胸前。只有棺材顶部是开启的,我们看不到她的前臂。
克莱特斯脸上的皮肤发着光,紧紧绷在骨头上,眼睛带着一种凝视火柴时的神情。
我没有听牧师讲了什么。牧师是个推件。神经质的男人,他读着《旧约全书》中的片断,以他力所能及的最佳方式,说着安慰的话。雨又开始敲击屋顶和窗户,穿过地面和河流。在我内心深处,雨是一种更准确的感情。
我做了与众不同的祈祷。那是我不时说的祈祷,也许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上帝像我们一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相信也许他可以影响过去,尽管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有时当我独自一人,尤其是在夜晚、在黑暗中,我开始细想,人们也许在他们死亡之前,经历了无法承受的苦难。我请求上帝解除他们的疼痛,从精神和肉体上陪伴他们,麻木他们的感觉,冷却他们最后时刻的所有痛苦的火焰。我先为达乐涅做祈祷。然后又为我的妻子安妮说了一遍。
方形墓地被水泥柱子之间的铁丝包围起来,暴露在风中,长满杂草。玛丽亚盆地是个很奇怪的地方,河流的陡岸和阶梯状的沟渠就像用一把油灰刀切割出来的。
甚至颜色也很奇怪,带着铁锈一样烧焦的橙色条纹。在细雨中,乡村看来似乎在被有毒的垃圾溶液毒害。这就是达乐涅曾经对我讲过的地方,是所谓的1870年贝克尔大屠杀的地点。在这个下午,除了一株孤独的紫色山茱萸盛开在公墓栅栏旁,从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春天的痕迹,似乎这个地方像月球表面一样被诅咒了。这是一个纪念碑,用来纪念我们人类最惨痛的故事。
我看着护柩者将达乐涅的棺材沉人刚挖好的一个洞里。靠近墓穴酌层层泥土,被雨水冲刷得很光滑。
我走到小货车那里,阿拉菲尔开着车门在椅子上睡觉,我凝望着潮湿的土地。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汽车和卡车在土路上开走了,石块敲击在挡泥板上。接着周围又安静下来,只有两个挖墓者在达乐涅的棺材上铲土堆的声音。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风开始吹过地面,吹平了小草,吹皱了路面上的一滩雨水。风越吹越猛烈,出乎意料地强劲,风揭掉了公墓栅栏旁山茱萸的紫色花朵,将它们吹进一团空气中,像被撕成碎片的小鸟一样带到河面上。
接着一切都过去了。天空又成为灰色,风落下来,杂草在地面上坚挺地站了起来。
我听到有人站到我后面。
“这看来像是世界末日,是不是?”迪西·李说。他穿了一套灰西服,带纽扣的栗色衬衫。“或者说当耶稣结束世界时,地球看来会是这个样子。”
我看到克莱特斯靠在迪西粉红色的卡迪拉克敞篷车后面,等着他。
“谁为棺材付的钱?”我说。
“克莱特斯。”
“这是谁干的,迪西?”
“我不知道。”
“是萨利·迪奥吗?”
“我不相信有那样的事情。”
“别这么敷衍我。”
“他妈的,我不知道。”他看了看正在睡觉的阿拉菲尔。“对不起……”
我继续看着河面,看着河流中央的漩涡,还有远处带着橙色线条的陡岸。
“站在这里研究问题没什么好处。”他说,“和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会在林肯停留,顺便吃点东西。”
“我会多呆一会儿。”
我听见他点燃了一根香烟,喀财关掉打火机,放口口袋里。我可以闻到香烟的烟雾在我身后统绕。
“跟我到这边来,我不想惊醒那个小姑娘。”他说。
“什么事,迪西?”我暴躁地说。
“有些人说,生活就像个婊子,人总会死亡。我不知道那是否正确。但那是你现在正在开始考虑的问题,这不是你的风格,伙计。你看,你和她有亲密关系。所有事都瞒不过我,我知道你的感觉。”
“你很清醒。”
“所以,很多时间我都很放松。我有我自己的程序。你们这些人难得清醒一天,而我则是难得糊涂上一天。和我们一起走吧,让我离开克莱特斯身边一会儿,那个杂种快把我逼疯了。这就像挨着一个香烟头上的气球。我告诉你,如果他抓住做这件事的家伙,那个家伙就不用进监狱了。”
我跟在他们后面,朝大分水岭驶去。林肯镇的雾很浓很重,空气很冷,在黄昏的光线中泛着紫色。我看见克莱特斯和迪西在靠近咖啡馆的马路边停下来,回头看我。我换到第二档,加速驶过了红绿灯,继续穿过小镇。
阿拉菲尔在仪表盘的光线中看着我。
“我们不停下来吗?”她问。
“到了山那边,我给你买一个牛鱼夹饼怎么样?”
“他们想让你和他们一起停下来,是不是?”
“那些人想要的东西很多。但是当他们邀请时,我就是不想呆在那里。”
“有时候你并不是没感觉,戴夫。”
“我得和你的老师谈谈了。”我说。
第五节
星期一早晨,我起初想打电话给我的律师,然后决定,我不需要更多的电话支出或者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
如果他已经争取到审判延期,他会打电话给我。我带着阿拉菲尔走到学校,然后在厨房吃了一碗葡萄。之后,我努力思考一个合理的计划,来将哈瑞·玛珀斯和萨利·迪奥推到绝路上。但是很快,我就否定了每一个选择。
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尸体,更别说证明他们是被哈瑞·玛珀斯和达尔顿·魏德林杀害的了。总之,我不知当初自己为什么会认为,我可以解决一切的法律问题。我不再是一名警察,我没有权力接近警察局的信息、搜查、逮捕或者审讯。
我可以回到大分水岭的东坡,在县法院着手调查石油租契。也许我可以以某种方式,将迪奥和哈瑞·玛珀斯、明星钻探公司和印第安人联系起来。但即使他们之间存在联系,那会对我在路易斯安纳州的谋杀指控有什么帮助呢?还有,谁杀了达乐涅?为什么?我的思想像一群狗一样,彼此咬着。
我被突然传来的脚步声分散了思路。我从餐桌旁站起身,透过卧室门和屏风窗户看过去。在树叶的阴影下,我看到一个粗壮的金发男人,他戴着黄色、坚挺的帽子,穿着一件无袖的粗斜纹棉布衬衫,穿过灌木丛消失在后院。一条工具腰带在他身旁叮当作响。我迅速走到后门,看见他站在阳光照耀的草坪中央,手搭在屁股上凝视着电话杆。他的二头肌很大,被太阳晒得发红。
“需要我帮忙吗?”我说。
“我是电话公司的。线路有点问题。”
我点点头,没有回答。他继续抬头凝视着电话杆,然后再次回头瞥了我一眼。
“你今天早上用过电话吗?”他问。
“没有。”
“它响了一声就停下来过吗?”
“没有。”
“好的,那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