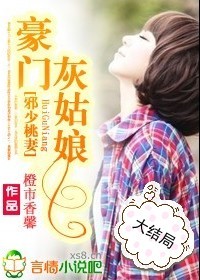忧伤黑樱桃-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拉菲尔在水泥字上坐着,紧挨着我。她从膝盖上弹掉泥巴,我看到她皱起眉头。
“戴夫,那是谁的帽子?”她问。
“什么?”
“在椅子上,靠近壁炉,那个黑色帽子。”
“哦。”我说,“我想一定是有位女士把它落在那里了。”
“我坐到帽子上了。我忘了告诉你。”
“没关系,别担心。”
“她不会生气吧?”
“不会,当然不会。不用为那类事情担心的,小家伙。”
第四节
第二天,我安顿好阿拉菲尔。如果我在晚上不得已呆在小镇外面,她就会和保姆呆在一起。然后我出发,去大分水岭另一侧的黑脚族保留地。在早晨的阳光中,我越过粉红色的岩石和松树,沿着溪谷驶向黑脚河。当我到达林肯伐木小镇时,空气变冷了,车窗被雾打湿。
接着我到了东部斜坡,除了落基山脉映射在我的反光镜中,到处是一望无际的小麦和成群的牛羊。我高速驾车,驶入丘窦和杜普耶尔,过了一会儿,就进入黑脚族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了。
我曾经去过好几个印第安人保留地,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好地方。这个也不例外。厄内斯特·海明威曾经写过: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比输掉一场战争更糟的命运了。如果他的读者中有人持反对意见,那他们只需参观美国政府安置原住民的一个地方就够了。我们夺走了他们的一切,反过来送给他们天花、威土忌酒、福利救济、联邦寄宿学校和收容所。
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我问到了部落议长办公室的方向。
部落议长是个和蔼的人,编着辫子,戴着珠宝,穿着西方的马甲、绿色条纹的长裤、黄色的牛仔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是一所社区学院的艺术大专毕业证书。
他很有礼貌,听得很认真,当我说话时,他眼睛很专注地盯着我的面孔。但是很显然,他不想谈论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或者他不认识的某个白人的石油生意。
“你认识哈瑞·玛珀斯吗?”我问。
这一次,他的凝视被打乱了。他望着窗外的街道。
“他是个租赁土地的人,他有时候到这里。”他说,“大部分时间,他在保留地边上工作。”
“关于他你还了解什么?”
他撕开一盒廉价的樱桃红雪茄。
“我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你得问问其他人。”
“你认为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微笑着以活跃气氛,然后点燃雪茄。
“他杀了他的伙伴,达尔顿·魏德林,在路易斯安纳。”
“我不知道那些,罗比索先生。”
“我认为他还杀了你们的两个人。”
“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什么,先生。”
“你认识失踪的印第安运动组织的两个人吗?”
“不是在保留地内,我被选举来关心的地方是保留地。”
“你说‘不是在保留地内’是指什么?”
“我不属于印第安人运动组织,我不掺和他们的事情。”
“但是你听说有人失踪了,对吗?”
他又望了望窗外,然后从鼻子和嘴巴中呼出雪茄烟雾。
“就在这儿的南边,在提敦村,克雷顿·代斯马丢和他的堂弟。”他说,“我记不起他堂弟的名字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说他们有天晚上没回来,但他们也许只是去别的地方了,这很偶然。你去和提敦村州长办公室的人谈谈,和克雷顿的妈妈谈谈吧。她就住在保留地外边。”
半小时之后,我把保留地甩在身后,沿着溪边一条狭窄的灰色土路行驶。随后地面向上倾斜,进入茂密的黑松林中。再向前,我可以看到平原在山脉脚下到达尽头。山峰很突兀地升起,就像巨大的地质断层,在天空下显得陡峭而参差不齐。
我找到了部落议长指给我的房屋。房屋用圆木建在一座小山上,木瓦屋顶,下陷的走廊,窗户上钉着塑料布用于保温。种满矮牵牛花的咖啡罐,放在走廊上和台阶边。这里的女人看上去非常老,白色的头发带着少许黑色,坚韧的皮肤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眼睛和嘴巴周围皱得像蜘蛛网。
我坐在她的客厅里,尝试着向她解释我是谁,我想知道她的儿子克雷顿·代斯马丢和他的堂弟发生了什么。
但是她的面孔很冷淡、难以捉摸,每当我直视她的眼睛时,她的眼睛都要转移方向。在靠近小壁炉的桌子上,是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士兵的照片。照片前是两个打开的毡盒,里面分别是一个紫心勋章和一个银星奖章,它们是由美国军队授予在战争中受伤军人的勋章和奖给作战勇敢者的奖章。
“部落议长说,你的儿子大概只是离开一段时间。”
我说,“大概他去寻找其他工作了。”
这次她看着我。
“克雷顿不会不告诉我就去其他地方。”她说,“他在镇上的加油站有一份工作。他每天晚上都回家。他们在离这儿两英里的一个壕沟里发现了他的汽车,他不会把汽车留在壕沟里消失的,他们对他干了一些事。”
“谁?”
“那些想危害他的组织的人。”
“印第安人运动组织吗?”
“他有一次被痛打一顿。他们总是想伤害他。”
“谁打了他?”
“那些不好的人。”
“代斯马丢夫人,我想帮您查清楚,克雷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曾经提到过一些人的名字吗,一些找他麻烦的人的名字?”
“联邦调查局。他们来到加油站附近,用电话召人打他。”
“哈瑞·玛珀斯或者达尔顿·魏德林呢?你记得他提到过这些名字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向外看着天空,从一个哥本哈根罐里,拿出了一小撮鼻烟,放在嘴唇和牙床之间。尘埃颗粒在光线中旋转着。我谢过她,开车沿着通往乡间宅第的道路返回。
州长离开小镇了,一位警员在法院接待了我。
“我们大概四个月前调查过那个案子。”他说,这是个高大、瘦削的男人,穿着卡其布制服,他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集中在香烟上,而不是和我谈话。“他的母亲和妹妹填了一份失踪人员报告。我们在壕沟里找到了他的汽车,轴承都坏了,钥匙不见了,备用轮胎不见了,收音机不见了,有人甚至从仪表盘上拆走了时钟。这说明什么?”
“有人拆毁了汽车。”
“是的,克雷顿·代斯马丢干的。那辆汽车正准备被回收。他和堂弟那晚在离那儿三英里的酒吧里,喝得烂醉,他们跑下马路。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之后他没有再回家?”
“能再问一遍您从哪儿来吗?”
“路易斯安纳州的新伊伯利亚。”
他将一团烟雾吹人窗前的阳光中。
“不管你相信与否,这种事情在这儿可不寻常。”他说。然后他的声音发生变化,带上一种平滑而疲惫的音调。“我们谈论的,是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两个人。其中之一,克雷顿的堂弟,曾在南达科塔蹲过牢房,现在他仍然由于不履行赡养义务而受到通缉。克雷顿也有他一些麻烦。”
“哪一类呢?”
“打架,非法携带枪支,还有鲁莽的言谈。”
“他以前曾经从家里和工作地点失踪过吗?”
“瞧,现在就是这样。在那条路上有个酒吧,他们在那儿一直呆到半夜。酒吧离克雷顿家只有五英里,他们在沿着马路三英里的地方毁了汽车。也许他们走到克雷顿的家,没有惊醒老妇人,然后在她起床前离开了。也许她记不起他们做了些什么。也许他们在拆掉汽车后,免费搭乘别人的车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你认为是熊吃了他们吗?“
“不,我认为你在告诉我,代斯马丢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的妈妈有不同的说法,而且那个人获得过银星奖章,你对此有何评论?”
“我不认为和你沟通得很好。你不了解这些人的生活方式。瞧,当一个白人雇用印第安人工作时,他雇了六个,可到早上也许只会剩下三个。他们在婚礼上砍伤自己的亲戚,在监狱牢房上吊自杀,他们加大马力开车,然后从侧面撞到火车上去。去年冬天,三个年轻人爬上一辆货车的车厢顶上,火车一直开到加拿大,在大风雪中停在侧轨上。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去取回他们的尸体。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说,他们冻得如此僵硬,你甚至可以用一把锤子敲碎他们的身体。“
我请他带我看一下克雷顿·代斯马丢汽车滚下马路的位置。他不太情愿,但还是同意了。他驾车带着我,沿着我早些时候经过的土路驶去。我们经过了代斯马丢和堂弟最后被人看见的酒吧,这是一个扁平的圆木建筑,窗户上有霓虹谷啤酒和大瀑布啤酒的标志。接着,我们在路上蜿蜒着,通过贫瘠、坚硬的旷野,最后看到小溪、棉白杨和一丛黑松。警员在路肩上停下汽车指给我看。
“就在那边的壕沟里。”他说,“他把一个轮子勾在侧面,然后掉进去的。就像折棍子一样折断了轴承。这没什么神秘的,朋友,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第五节
我很晚回到密苏拉,还来得及在阿拉菲尔睡着之前,去保姆家接她。保姆出去办事儿了,她的一个朋友,名叫里根的三年级教师过来陪伴阿拉菲尔。她们两个在封闭的门廊里看电视,一边从一个碗里抓爆米花吃。里根小姐是个漂亮的女人,快三十岁了,赤褐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尽管她的皮肤仍然苍白,但我可以看到她肩膀和脖子上的太阳斑。
“过来看,戴夫。”阿拉菲尔说,“里根小姐画了一幅德克斯的画儿,可她从来没见过它。”
“瞧。”阿拉菲尔说着,举起了一张图画纸,上面是一匹阿帕卢萨马的彩色蜡笔画。
“里根小姐画得非常好。”我说。
“我的名字叫苔丝。”她微笑着说。
“哦,谢谢你看护阿拉菲尔,很高兴见到你。”
“她是个很可爱的小姑娘,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她说。
“你住在隔壁吗?”
“是的,离学校只有两条街。”
“那么我希望能再见到你。谢谢你的帮助,晚安。”
“晚安。”她说。
我们在黄昏中走回家。天气很温暖,枫树在月光下显得很丰满。桥上的灯光映在打着漩涡的褐色河面上。
“大家都说她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阿拉菲尔说。
“我相信她是。”
“我告诉她去新伊伯利亚来看我们。”
“那非常好。”
“因为她没有丈夫。”
“她没有丈夫,为什么没有,戴夫?”
“我不知道,有些人就是不想结婚。”
“为什么?”
“你把我问倒了。”
在熄灯前我们吃了一张饼。我们的卧室相连,门开在两个卧室之间。
“戴夫?”
“什么?”
“你为什么不娶里根小姐?”
“我会考虑一下的。明天见,小家伙。”
“好的,大家伙。”
“晚安,小家伙。”
“晚安,大家伙。”
第二天早上,我打长途给巴提斯蒂、保证人和我的律师。巴提斯蒂把食品店经营得很好,保证人对我在审判日期前返回路易斯安纳的反应很平静。但是律师没能争取到延期,因此他非常焦急。
“你在蒙大拿发现什么了吗?”他问。
“没有确切的发现。但是我认为,迪西·李告诉我的关于玛珀斯的都是真话,他在这里杀了好几个人,大概是印第安人。”
“我告诉你,戴夫,那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如果你能让他在蒙大拿被关起来,那就不能在路易斯安纳作为目击证人,来和我们做对了。”
“我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也许不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辩护措施,就那么简单。我雇了一个私家侦探来调查玛珀斯的背景,他十七岁时在德克萨斯州的马歇尔,用一根高尔夫球杆打得另一个家伙屁滚尿流,但那是他曾经卷入的唯一麻烦事。他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然后在越南开军用直升机。他其余的生活是个空白,很难说明他是个1888年伦敦著名的开膛手杰克似的人物。”
“我们等着瞧吧。”我说。我并不想承认他话中的事实,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在快速地跳动着。
挂断电话之后,我在前面的走廊里端着一杯咖啡,试着读读报纸,但我的眼睛无法集中到文字上面。
第六节
我洗了碗,清理了厨房,开始给卡车换油。我不想去考虑和律师的对话,过一天是一天,放轻松些。我告诉自己,不要生活在明天的问题里,明天不会比昨天有更多的生存方式,至少你能控制“现在”,我们生活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