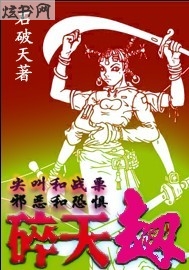甲骨碎-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切。”徐徐挥了挥手,带着一脸的笑容离开了。
她拐过街角,越走越慢,最后靠着一个电话亭停了下来。
她的笑容已经不见,呼吸也沉重起来,手指在电话亭的玻璃门上无意识地敲击着。
就这么站了一会儿,她把墨镜重新戴起来,整了整棒球帽的帽沿,顺着来路,慢慢走了回去。
经过海报的时候,孙镜又多看了一眼。和徐徐一样,他也选择了原路返回。小街的街口多停了两辆警车,依然有围观的人。
那个叫韩裳的女人当然已经不在地上,只剩一个白笔画的人形。
但血还触目惊心地凝在那儿。
旁边一个中年人被带上警车,临上车的时候还在用上海话解释着:“阿拉屋里的花盆都放的老牢的呀,哪能会掉下来,各个事体真是……”
“让开了让开了。”警官对围观的人群喊,然后他抬起头对四楼阳台上站着的警察叫道:“再试一次。”
阳台向外搭出块放花草的木板,在一盆吊兰和一盆月季之间,有个明显的缺口。缺口处留着泥印子,一块普通的红砖现在被竖着放在泥印上,一根手指点在砖后,轻轻前推。
红砖在空中缓慢地翻滚着,迅速坠落,和人行道碰撞的瞬间迸散成大大小小的碎块。
下面的警官转头问旁边的一位居民:“刚才真的没风?”
“好像有一点。”那老人又不确定起来。
落点不对?孙镜立刻明白了这个简单实验的用意。
现在警察的眼睛倒都很毒啊,居然发现了花盆原本位置和掉落位置并非垂直,有小小的误差。
从这块红砖来看,误差了小半米。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它因素影响,花盆该落在韩裳脚边,吓她一大跳。
但是可能有很多因素的,孙镜向小街的另一头走去,心里想着。
比如当时有一只鸽子落在花盆上,让它重心偏了,掉下去的时候撞了旁边的花盆一下;比如韩裳被砸中的时候踉跄了半步才倒下去,所以现在推算出的她原本所处位置是不准的。后者的可能性很大,人在行走的时候有向前的惯性,没那么干净利落地直接倒下去。
当然,还有风。
自己能想到的,警察当然也想得到。所以,这还是一宗意外。
孙镜忽然有些警觉,他发现潜意识里,自己似乎正在往非意外的地方想些什么。
“是鬼索命,是鬼索命,我要去讲!”
孙镜听见了一个充满恐惧的声音,转头一看,却是先前见到的烟杂店老妇人。她想要从店里冲出来,被死死拉住。
“侬有毛病啊,侬阿是毛病又犯了。”拽着她的年轻女人凶她。
孙镜的脖子上又立起了鸡皮疙瘩,他忽然想到一件事,在店门口停了下来,转回身去看。
没错,这儿虽然离出事的地方不远,但小街弯曲的弧线,让他无法看见韩裳倒下的位置。他都看不见,呆在后面烟杂店里的人当然更看不见。
老妇人伸出一只手对他用力招:“侬阿是警察同志,我跟你讲,是鬼索命啊,警察同志,我看见的。”
“唉呀,我妈有神经病的,不好意思哦。这个老神经,侬真的要进医院了。”女儿用力把妈拉回店去。
孙镜用手慢慢捋了捋后颈,温热的掌心把凸立起的毛孔安抚了下去。
只是恰好和死亡事件同时发作的神经病。
或者,这事情不那样简单。
他感觉内心正被某种情绪冲刷着。这情绪并不完全陌生,令他想起从崖上高速坠下时,把整个胸腔都塞满的恐惧,迫在眉睫的死亡危险会不断提醒他,快拉开降落伞。但他偏要再等一等。
心灵就像沙滩。汹涌潮水一次又一次把沙变得更细更坚硬,不过要是扑过来的浪足够凶猛,也许会挖出沙滩下埋藏的宝藏。比如二○○四年末的那次海啸,在印度马哈巴利普兰的沙滩上洗出了一尊尊千多年前的石雕。
人都很贱,只是各自不同。孙镜自嘲地一笑。
“弗弗弗”,孙镜嘴里发着奇怪的声音,走进了自家的小楼。
曾经这幢带着院子的三层小楼都是他家的,洋楼的外墙铺着马塞克,八十年前这相当摩登。院子里有一棵很粗的广玉兰,开花的时候关紧窗户都挡不住郁郁的香。四十年前楼里搬进了好些不请自来的邻居,在当时这没什么道理好讲。现在孙镜拥有的,是二楼的三间房,外加一个厕所。
今天的信箱很正常,孙镜关上小门,穿过狭窄的过道,走上楼梯。
“弗弗弗”,他又开始了。韩裳临死前的一刻,想要对他说的会是什么话?
不,只是一个字,孙镜觉得,韩裳反复想要说出来的,只是一个字。
哪个字这么关键?
孙镜叹了口气。汉语里有太多同音字,并且韩裳说的不会是“弗”的同音字,而是以“弗”为开始音的字,只是快速消亡的生命让她再没力气发出后面的音节。
三间房。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兼收藏室,剩下的就是孙镜正呆着的这间。
阳光被百叶窗割成碎片,落在龟壳上。
许多龟壳。
层层叠叠,堆在一起,成了座龟壳山。
龟壳山上的龟壳,都是没有字的。这不是殷商甲骨,只是龟壳而已,里面最古老的一块,其原主的死亡时间也不会超过五年。
屋子的其它角落散落着些面貌全然不同的龟甲。它们相貌古旧,或多或少都有些残缺,上面有一排排钻凿的痕迹,有些被火烤过,在另一面爆成一条条的细裂纹。在殷商时期,这叫作卜纹或兆纹,贞人、巫师根据其走向,来判断占卜的结果是一个吉兆,还是一个凶兆。
它们看起来就像是自殷墟出土的珍贵古物,当然,只是看起来像而已。这已经足够了,孙镜觉得,自己不仅是最好的甲骨专家,应该也是最好的甲骨造假专家。在这一行,他没几个像样的竞争者。
孙镜看着堆成小山的原料,这里面有山龟有泽龟,原本商朝各地进贡给王都的卜龟,就各有不同。
“喀啦”。
孙镜立刻扫视了一圈,哪里发出来的声音?
“喀啦”。
又是一声,是那堆龟壳。孙镜死死盯着龟壳山,就在他目光注视之下,小山里继续发出声响,然后“哗啦啦”倾倒下来。
孙镜肩膀一松,他想起来自己把那封活的龟甲信扔在这间屋里了。两天没喂它,看起来活力还不错,只是寄信的人已经死了。
孙镜一时懒得去把龟壳重新堆好,反正这间屋子就够乱的了。他靠在工作椅上,往下一压,半躺下去。
几秒钟后,他就猛地挺直身子,直愣愣盯着倒下的龟壳。
有道闪电在脑海中划过,瞬间把原本没看到的角落照亮。
孙镜双手用力撑着扶手,慢慢站起来,走到塌了一半的龟壳堆前,蹲下。他把手伸进龟壳堆里,摸索了一阵。
“见鬼。”他低声咒骂,忍不住在手上加了力量,野蛮地搅动起来。龟壳四散,飞得到处都是。
等他总算停下来的时候,屋里已经找不到几处可以落脚的地方了。他无声地笑着,低下头,开始端详手里这只吓得把头脚缩进壳里的乌龟。
他记得韩裳在这封龟甲信里犯了个可笑的错误,她把“余”字写反了。这是任何一个对甲骨文稍有涉猎的人都不会犯的低级错误,然而韩裳却是准备出两百万,借巫师头骨做研究的人。也许韩裳并不是要做什么学术研究,她不是甲骨学者,多半另有目的。可她会是嫩到犯这种错误的菜鸟?
她写反了。
孙镜眼前浮现韩裳最后的那几个口型。
就是“反”!
孙镜把乌龟转了个方向,没有发现。没有任何犹豫,他把乌龟翻了过来。
余就是我,把我反过来,这是个隐语。
“嗬……”孙镜长长吐了口气。
龟腹甲上有字。不是甲骨文,而是刻得很工整的小楷。
前几个字就让孙镜一惊。
“如因不测让我无法和你见面……”
那不是意外!一声霹雳在心头炸响。
茶几上放着今天的晚报,最上面一张是社会版,头条就是话剧女演员中午当街被花盆砸死的新闻。
不出孙镜的意料,新闻里说,韩裳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咽气了。死讯确认,他不禁叹了口气。
时钟指向十一点,孙镜从沙发上站起来,换鞋出门。
白天人多眼杂,现在的时间,去韩裳家正好,那儿有一件专门留给他的东西。
有夜风,吹得行道树一阵阵的响。一辆空出租驶过来,放慢了速度。孙镜冲司机摇摇手,他要去的地方步行可达。
龟腹甲就那么点地方,韩裳又不会微雕,当然不可能在上面说明是什么样的东西。但这必然是个关键线索,孙镜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知道,韩裳为什么会死。同时这也意味着,自己被完全牵扯进去了。
或者自己可以看过之后放回原处,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孙镜笑了笑。
韩裳租的房子离这里很近。附近的几片居民区都是老房子,到了地方孙镜才发现,这幢小楼和他自己家非常像,只是院子小了些。
韩裳住在三楼。晚报的记者把这宗意外报道得很详细,所以孙镜知道,韩母已经晕倒进了医院,所有事情都压在韩父身上,没有谁现在有空来这里整理韩裳的遗物。
不过孙镜还是绕着楼走了一圈,记下了三楼亮灯房间的方位,然后转向花坛走去。
这样的时间,一楼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孙镜走到花坛前,再次确认四下无人后,摸出小手电照了照,在左侧外角找到了根插得很深的木筷子。
木筷子下面埋了个小塑料袋,里面有两把钥匙。
孙镜用其中的一把打开了大门,反手轻轻关上,陷入完全的黑暗里。
在这样住了许多户人家的楼里,大门入口处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过道灯开关。每家都有一个,韩裳当然也有。孙镜不知道哪一个是韩裳的,他也不准备开灯。
借着手电筒的光,他走上楼梯。尽管已经足够小心,每一步踩下去还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木楼梯老朽得厉害,好像踩重一点,就会陷出个洞来。
三楼,孙镜站在韩裳的房门前。先前看见亮灯的屋子是另一间,这让他彻底放下心来。
关了手电,孙镜摸着锁孔,把钥匙插进去。
转动的时候感觉很别扭,孙镜用了几次力,心想是不是搞错了大门的钥匙,就又拔出来换一把。
还是开不了。
孙镜换成最初那把再试。黑暗里转钥匙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刺耳,这时候如果邻居的门突然打开,看见他摸黑在开死人家的门,就麻烦了。
韩裳不可能搞错钥匙吧,怎么会开不了。孙镜手里加了把力,觉得有点松动了。是这把钥匙没错,开老旧的锁常常需要一点技巧,比如得往左压或往右压。
孙镜试着把钥匙压向左边,门突然打开了。
孙镜猛吃一惊,这不是他打开的,有人……
念头才转到一半,脑袋上就被硬物狠狠砸了一下,天旋地转倒在地上。
这一击并没能让他完全失去意识,但头晕得一时回不过神来。给他这一下的人飞快从旁边蹿过,“腾腾腾”跑下楼去。
糟糕,这动静太大了。孙镜知道不好,可他还在恍惚中,从地上爬不起来。
邻家的门打开了,灯光照在他身上。
“哦哟。”一声惊叫。
“老头子,侬快点出来。”受了惊吓的老太婆回头往屋里喊。
邻居老头跑出来的时候,孙镜用手撑着靠墙半坐起来。这暂时是他能做到的极限了,脑袋又晕又痛,摸一下额头上起了个大包,还有血。旁边地上掉了根金属棍,正是打他的凶器。实际上这是根中空可伸缩的室内晾衣杆,幸好如此,否则他的下场可能和韩裳差不多。
不过他现在这副样子已经很吓人了,韩裳家的门又洞开着,把后出来的老头也吓得不轻。
“你是谁,怎么回事?”老头紧张地问。
然后不等他回答,就对老伴说:“快点报警叫公安来。”
“我就是警察。”孙镜说。
“啊?”
“我就是警察。”孙镜镇定地重复,“后面这间屋的主人今天中午死了。”
“从晚报上看见了,小姑娘真作孽啊。”老太婆讲,但看着孙镜的眼睛里还是有些怀疑。
写在老头脸上的疑问更多。
“你是警察?”他问,“那刚才是怎么回事?你真的是警察?”
“我同事很快就会过来。”
孙镜在两个人的注视下摸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徐警官,行动出了点问题。你立刻过来,对,我还在……”孙镜把这里的地址飞快报了一遍,挂了电话。
“你们也看见了,她的死不那么简单。”孙镜说,他见到老头老太满腹疑问的模样,又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