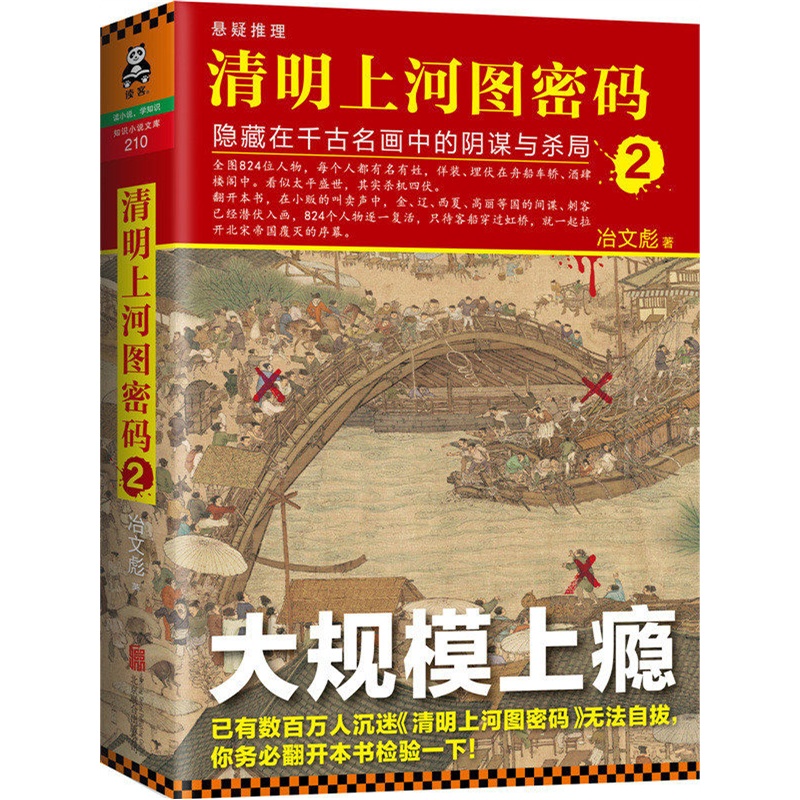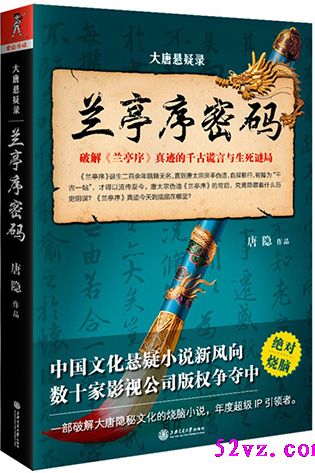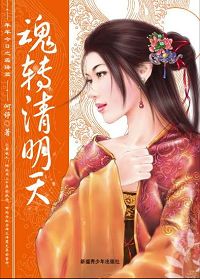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第6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万福连声叹道:“他去杀那客人,却被客人躲开,葛大夫当时恐怕也站起来了,正好在客人身后,那一刀刺到了葛大夫身上。葛鲜误伤了父亲,自然要跑过去查看父亲伤势,便跪到葛大夫的左边,所以才挡住了溅出来的血迹——”
正在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哭喊声:“父亲!父亲!”
一个矮瘦的年轻男子奔了进来——
赵不弃告别了何涣,骑着马赶往开封府。
关于何涣杀阎奇,这件事恐怕毫无疑议,不过他想着堂兄赵不尤的疑问,又见何涣失魂的样儿,心想,还是去查问一下吧。虽然据何涣言,赵不弃在应天府所见的是那个丁旦,但有人在跟踪丁旦,若是何涣这杀人之罪脱不掉,难保不牵连出来,这样何涣的前程便难保了。
他找到了开封府司法参军邓楷,司法参军是从八品官职,执掌议法断刑。邓楷是个矮胖子,生性喜笑诙谐,和赵不弃十分投契。他走出府门,一见赵不弃,笑呵呵走过来,伸出肥拳,在赵不弃肩膀上一捶,笑道:“百趣这一向跑哪里偷乐去了?也不分咱一点?”
赵不弃也笑起来:“这一阵子我在偷抢你的饭吃。”
“哦?难道学你家哥哥当讼师去了?”
“差不多。无意间碰到一桩怪事,一头钻进去出不来了。今天来,是要向你讨教一件正事。”
“哈哈,赵百趣也开始谈正事了,这可是汴京一大趣话。说,什么事?”
“你记不记得前一阵有个叫丁旦的杀人案?”
“杀的是术士阎奇?记得,早就定案了。”
“那个丁旦真的杀人了?”
“他是自家投案,供认不讳,验尸也完全相符。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有任何疑点?”
“没有。你要查案找乐子,也该找个悬案来查。那个丁旦暴死在发配途中,这死案子有什么乐子?”
“我能不能看看当时的案簿?”
“案簿岂能随便查看?不过,念在你还欠我两顿酒的面上,我就偷取出来给你瞧瞧,你到街角那个茶坊里等我——”
邓楷回身又进了府门,赵不弃走到街角那个茶坊,进去要了盏茶,坐在角落,等了半晌,邓楷笑着进来了,从袖中取出一卷纸:“快看,看完我得立即放回去。”
赵不弃忙打开纸卷,一页页翻看。果然,推问、判决记录都如何涣所言,过失误杀,毫无遗漏。他不甘心,又翻开阎奇的尸检记录,初检和复检都记得详细——阎奇因脑顶被砚角砸伤致死,身上别无他伤。
赵不弃只得死了心,将初检和复检的两张验状并排放到桌子上,心里暗叹:这个呆子,竟然用砚台尖角砸人脑顶,你若是用砚台平着砸下去,最多砸个肿包,根本伤不到性命。
“如何?找到什么没有?”邓楷笑着问。
赵不弃摇摇头,正要卷起两张验状,却一眼看到一处异样:关于阎奇脑顶伤口,初检上写的是“头顶伤一处,颅骨碎裂,裂痕深整”,而复检上却只有“头顶伤一处,颅骨碎裂”,少了“裂痕深整”四字。
他忙指着问道:“这初检伤口为何会多出这四个字?”
邓楷伸过头看后笑道:“初检验得细,写得也细一些。”
“‘裂痕深整’四字,恐怕不只是写得细吧?”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初检的仵作姚禾是个年轻后生,才任职不久,事事都很小心。”
“‘深’字好解释,可这‘整’字怎么解?”
“恐怕是别字,不过这也无关大碍。”
赵不弃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便问道:“这个仵作姚禾今天可在府里?”
“东门外鱼儿巷发生了件凶案,他去那里验尸去了。”
“他家住在哪里?”
“似乎是城外东南的白石街。怎么?你仍不死心?”
“我想去问问。”
“好。我先把这案簿放回去。你慢慢去查问,我等着瞧你如何把一桩死案翻活,哈哈——”
葛鲜正哭着要扑向父亲的尸体,却被顾震下令,将他拘押起来。
看着父亲躺在地上,胸口一摊血迹,他哭着用力挣扎,要冲开弓手阻拦,却被两个弓手死死扭住他的双臂,分毫前进不得。随后被拖出院门,押往城里。
沿途住户及行人纷纷望着他,有些人认得他,低声议论着:“那是鱼儿巷葛大夫的儿子,礼部省试第一名,才考完殿试,说不准今年的状元就是他。前两天枢密院郑居中才把女儿许给了他。人都说前程似锦,他这前程比锦绣还惹眼,他犯了什么事?这个关口犯事,真真太可惜啦……”
他听在耳中,又悲又羞,却只能低着头、被押着踉跄前行,脚底似乎全是烂泥。以前,他始终觉着,生而为人,一生便是在这烂泥里跋涉。这一阵,他以为自己终于跳出了泥坑,飞上了青云,再也不会有人敢随意耻笑他,谁知道,此刻又跌到烂泥中,任人耻笑。
他父亲是个低等医家,只在街坊里看些杂症,勉强糊口。母亲又早亡,父亲独自带着他艰难度日。他才两三岁,父亲便反反复复告诉他:只有考取功名,你才能脱了这穷贱胚子。七八岁时,父亲带着他去金明池看新科进士,那些进士骑着高马,身穿绿锦,头插鲜花,好不威风气派!从那一天,他便暗暗发誓,自己也要这般。
于是,不用父亲督促,他自己便用心用力读书。童子学的教授说,读通《三经新义》,功名富贵无敌。他听了之后,其他书一眼都不看,只抱着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一遍又一遍熟读默诵,读到每一个字在哪一页哪一行都能立刻记起。除此之外,他便只央告父亲买了王安石文集,没事时反反复复地读,读到自己几乎如王安石附体一般。
苦功没有白费,从童子学开始,他便始终出类拔萃,张口成诵,提笔成章。尽管同学都嘲笑他生得瘦小,在背后都叫他“猴子”,他却毫不在意。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这只瘦猴子能踏上集贤殿。
直到进了府学,他遇见了劲敌——何涣。
何涣生于宰相之家,家学渊深,儒雅天成。最要紧的是,何涣从不把这些当作一回事,待人平易诚恳,吃穿用度和平民小户之子并没有分别。学业上,也和他一样勤力。从求学以来,葛鲜无论站在哪位同学身旁,都绝不会心虚气馁,但一见到何涣,立时觉得自己穷陋不堪。
他知道自己这一生无论如何尽力,为人为文都做不到何涣这般。
他恨何涣。
去年冬天,蔡京致仕,王黼升任宰相。
葛鲜听人议论,说王黼要大改蔡京之政,废除三舍法,重行科举。葛鲜原本正在一心用功,预备考入太学,这样一来便免去了这一关,直接能参加省试、殿试。论起考试,他谁都不怕,只怕何涣。
那天何涣邀他出城闲逛,一直以来,他既厌恶何涣,又极想接近何涣。每次何涣邀约,他虽然犹豫,却都不曾拒绝。两人一路漫行,偶然走进烂柯寺,无意中发生了一件小事——在寺里,何涣看到阿慈,竟然神魂颠倒。
起初,葛鲜看何涣露出这般丑态,只是心生鄙夷,嘲笑了一番。但回家跟父亲讲起时,父亲问了句:“你说的何涣,是不是那个和蓝婆家的接脚女婿丁旦长得很像那个?”他听了十分好奇,阿慈他是认得的,家就在汴河边,父亲和她夫家是多年旧交。阿慈的丈夫弃家修道,又招赘了个接脚夫,但葛鲜因常年在府学里,从没见过。
为此,他特意去蓝婆家附近偷看,第一眼看到丁旦,让他吓了一跳,简直以为是换了件衣服的何涣。
他回去又向父亲打问丁旦,听到丁旦是个赌棍,丝毫不管家务,不惜妻子,葛鲜顿时心生一个念头:何涣家有钱,丁旦有美妻阿慈,设法让他们换过来?
他把这个主意说给父亲,父亲起初还连连摇头,但知道将来省试、殿试时,何涣会和葛鲜争夺名位,便不再犹豫。父子两个商议了几天,最了当的法子无疑是取了何涣性命,让丁旦去顶这个缺。不过毕竟人命关天,始终不敢下这狠手。最后终于定下计策,只要让何涣和丁旦互换两个月,让他无法去应考就成。
父亲又找来丁旦试探,丁旦正在为没有赌资而着慌,一说便上钩。
于是,葛鲜邀了何涣去赏雪吃酒,为避嫌,另还招呼了几位同学。丁旦和他的朋友胡涉儿则躲在茅厕旁边,葛鲜的父亲已经教好他们,如何打伤面容和腿骨又不至于伤到性命……赵不弃去见了几个朋友,喝酒玩笑了一场,下午才骑着马出了城,到白石街去寻那个仵作姚禾。
到了姚家,开门的是个素朴温和的年轻后生,彼此通问了姓名,才知道这后生正是仵作姚禾。姚禾听了来由,便请他进去,姚禾的父母都在家中,见他们要谈正事,便一起出去了。
赵不弃直接问道:“姚仵作,我读了你给术士阎奇填写的初检验状,见上面记述他的伤口,写的是‘头顶伤一处,颅骨碎裂,裂痕深整’,复检时,去掉了‘裂痕深整’四字,这是为何?”
姚禾回想了一阵,才道:“这事当时在下也曾有些疑虑,向司法参军邓大人禀报过,回来还讲给了家父听,家父也觉着似乎有些疑问,不过丁旦是投案自首,前后过程供认不讳,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便没有再深究。”
“哦?你说的疑虑究竟是什么?”
“据那丁旦自陈,他用砚台砸了阎奇头顶,不过只砸了一下,但从伤口边沿来看,颅骨碎裂处似乎要深一些。”
“请你再说详细一些?”
“请稍等——”
姚禾起身走进里间,不一会儿就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方砚台和一个葫芦。他来到桌边,右手握紧葫芦,圆底朝上,左手握住砚台,尖角朝下,用力向葫芦砸去,葫芦应手被砸出个破洞。
“请看这破口处——”姚禾放下砚台,指着葫芦上那个破口,“砚台尖角有三条棱,破口边沿裂得最深的是这三道,其他都是连带碎裂,破口很细碎。”
赵不弃见那三道裂痕旁边细碎处甚至落下一些碎屑,便问道:“你在验状上写的‘整’字,可是说裂痕边沿没有这些细碎,很齐整?”
姚禾点了点头,但随即道:“不过颅骨不像葫芦这么脆,碎也不会碎到这个地步。”
“但仍该有些细碎骨屑?”
“是。除非——”
“除非下手极重,用力越重,碎处越少?”
“嗯。阎奇头顶伤口不但裂痕深,而且边沿齐整。我见过那个丁旦,不过是个文弱书生,按理说不会有这么大的气力。”
赵不弃心头一亮:“或许有另一种办法能让这伤口既深又整?”
姚禾点点头,重新拿起那方砚台,将棱角按原先方位,对准葫芦的裂痕,上下连击了几次,而后将葫芦递给赵不弃。赵不弃再看那个破口处,果然齐整了一些,原先边沿的细碎处都被挤压平整。
他越发惊喜:“这么说,丁旦只是砸伤了阎奇,并没有砸死?他曾慌忙离开那只船,有人乘机用这个法子,又在伤口处连击了几次?”
姚禾犹豫了片刻,才道:“我当时的确这么想过。不过,丁旦亲口证明,当时船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另外,若要证实这一点,得重新检验,伤口裂痕虽然齐整,但若是反复击打过,骨头碎屑应该会被挤压黏着在裂口边沿的血污中。但阎奇尸首早已火化——这怪我,当时若再仔细些,便能查得出来——”
赵不弃笑道:“不怕,有疑点就好,我去找到其他法子验证。”
第九章暴毙、复活
到底须是是者为真,不是者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程颢赵不弃骑马来到汴河边,黄昏细雨如丝,河上并没有几只船,柳雾蒙蒙、炊烟淡淡,四下一片寂静,似米芾的水墨烟雨图。他向来爱笑话文人骚客的酸情,这时竟也有些诗情意绪,自己不觉笑起来。
他记得鲁膀子夫妇的小篷船一向在虹桥东头等客,便驱马来到那里。果然,那只乌篷船泊在岸边那株老柳下。汴河两岸的柳树枝杈每年都要砍下来,填进岸泥中,用以紧固堤岸,因此被称为“断头柳”,这株老柳却因紧靠虹桥,并没有被砍,枝干粗壮,新绿蓬然。
一个妇人正蹲在船头的一只小泥炉边,用扇子扇着火口,忙着烧火煮饭。赵不弃见过这妇人,是鲁膀子的浑家阿葱。他来到岸边,下了马,一眼看到阿葱鬓边插着一支银钗,钗头上缀着几颗珍珠,少说也要值三四贯钱。随即又看到阿葱脖颈下粗布外衣内,露出鲜绿簇新的绣衫,衫领镶着银线锦边,看质料绣工,也至少值两贯钱。这一钗一衫被她的粗容粗服衬得十分刺眼。
赵不弃心想,证据就在这里了,他夫妇俩靠这小篷船营生,每月最多恐怕也只能赚五六贯钱。那鲁膀子又是个酒糟的浑人,怎么肯拿出这么多钱给浑家添买钗衫?
“阿嫂。”赵不弃笑着唤道。
阿葱抬起头,看了一眼赵不弃,红紫的面膛扯出一些笑:“这位大官人可是要搭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