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有闲-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收回了手,盯着自己的掌心。
“李翊轩。”我斗胆直呼其名,只因还将他当作朋友,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他若知道我被缚在你这里,必定不会就此罢休。大夏虽不如大覃横跨九州,兵强地广,但也绝对不容忽视。你知他用兵诡谲,就算不联手其他三国,一样可以搅得你边关不宁。连年征战是你想看到的么?而且若是还有其他三国的任何一个帮手,岂不是更麻烦?”
他双唇微微一掀,被我伸手打住。“你先听我说完。”
“你登基在即,届时朝内一番更迭的气象,又逢边陲时局不闻,必然□乏术,更何况战事若起,损耗巨大,要想过上只手遮天的帝王生活,只怕还要再等上十年八年。你本可以大权在握,高枕无忧,眼下却要因我一个市井平民而挫伤抱负吗?我值得与你的江山相权吗?你最好的年华,等的起吗?”
他定定望着我:“你觉得他杜云锦会为了一个女人而与我为敌,甚至不惜两国交战?!”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会来的…”我脸上泪痕交错,不住重复这句话。
“你就这么肯定?”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显得动摇。
“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人在哪里,但只要他还活着一天,就一定会来找我。他说过要娶我的…”
李翊轩只手握拳,用孤注一掷的决绝口吻道:“我得不到的东西,必然也不会叫他人得到。”
“那好。”我抹干眼泪,“该说的我都说了,随你吧,嫁给薛煜琛也好,把我丢去北疆的军营也好。都随你。”
言尽于此。该说的该做的我通通尽了全力,独自坐到床沿听候发落。
不日,李翊轩便下旨赐婚,将我许配给辞官不成,新近又升官的大理寺少卿薛煜琛。
窈窕来看我,今次还多带了一个口才了得的司徒婉儿,都是来做说客的,劝我良禽择木而栖,不如从了太子吧!我怒发冲冠,“良禽?你们才禽!”过了两天,又把伤愈刚能下床的四娘也给请来了,点着我的脑门骂:“怎么跟石头一样,食古不化!”
我叉腰:“老子就是石头怎么了?!”
她们都拿我没办法,直到薛煜琛现身才一起借故遁了。
房中点着冷花香,是名为炙苏的乌溪特贡,可以安魂催眠,量多了又形同于麻药,令人四肢无力。李翊轩以此限制我的行动,乃至于我每天有大半时间神智不清,陷于昏睡。后来我想到一个办法,偷偷的放血…
薛煜琛从小与我一起长大,闻见这股味道,嫌恶的皱起眉,在看到我手腕上的伤之后,神色黯淡,叹了口气道:“如此自伤…没想到竟需要出动这样的手段,才能令你嫁给我。”
我咬着唇不知该说什么。
他伸出手揉了揉我的发心,“小石头还是这么倔…”
我捉住他的袖摆,哽咽道:“你帮帮我…帮帮我好不好…”
他看着我,眼底有伤痛。我想我可能错过了一个大好人,可…我也曾真心,那段时间,我都是真心想要嫁给他的。
我认真地读过女戒女则,通宵达旦。认真地学过绣花,根根手指红肿带伤。练武行医都不曾这样笨拙的我,笨拙的在他身后蹒跚学步。可我的心不是石头做的,他于万佛寺山崖上放手的那一刻,于大庭广众下任我被人羞辱的那一刻,在楼船上对我出手的那一刻,即便我明明知道一切都是假的,都是在做戏,可我的心还是会痛。
真的。
我的心不大,装不下那么多阴谋算计。
薛煜琛仰天长出一口气:“我以为自己抢在了别人前头,你就怎么也跑不掉。可原来不是…他住在你这里。”一手指了指我的心。
“对不起。”我嗫嚅道:“是我不好。是我辜负了你。”
“不。”他摇头,“是我不好,怎么就会把你给搞丢了呢…”
“杜云锦出现的时候我就该把你抢回来,而不是放任他和你在一起,等我想起来时,才发现一切早已不在我的控制之内…”
尽管如此,薛大人最后还是冒着抗旨的风险答应替我牵线搭桥,联络司徒梦,也就是司徒婉儿的兄长,老不正经的鬼面兄弟。
做买卖要公平,我没有金银财帛高官厚禄可以许给他,只不过告诉他司徒婉儿有一个心仪之人,我可以助她妹子如愿以偿。
他笑:“丫头,你要我做什么?”
我说:“杀了我。”
人生就像下棋。谋定,落子,机变,事成。
这话是李翊轩说的。
“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机变,讲求遇事随机应变,见招拆招,个中快感,难以言表。唔,小妞,你就是那个机变。”
本阁主为此受教了,现学现卖,不敢说能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我素来有一个优点,不喜欢从机变中找寻任何快感,我只喜欢稳扎稳打,凡事买一个双保险。
司徒梦是我最后的机会,不容有失。
大婚当日,如我所预料一般,没有重兵把守。
☆、甜水乡风云——真人露真相
芙蓉帐子内;白纱帏幔搭在金钩上,斜眼望去;不远处的梳妆台上竖着一枚菱花镜子。四折屏风适时掩住入口;每一扇面上分别用翠玉,红珠点出不同的花儿;恰是春夏秋冬,长长久久;延绵不息。
我想起小时候的夏夜里,流萤飞舞,星点之中我靠着小勇哥的肩头哼唱曲子;他时不时击掌为我起调和拍;唱词依稀…
【三月里;人面桃花相映红。
六月里,双双池边赏白莲。
身处泥中质洁净,亭亭玉立在水间。
……
八月里,是中秋,桂花飘香阵悠悠。
十月里,是寒天,冬青花开叶儿鲜。
……
什么花姐什么花郎什么花的帐子什么花的床
什么花的枕头床上放什么花的褥子铺满床
红花姐,绿花郎。干枝梅的帐子,象牙花的床。
鸳鸯花的枕头床上放,木樨花的褥子铺满床。】
屏风上的花儿恰是桃,莲,丹桂和冬青。微微侧目,手指抚过浮屠凹凸的木雕香床,还有颈后的鸳鸯枕,这一切都是按着我小时候的要求临摹,不知这间新房,小勇哥哥花了多少心思准备…
不同于李今在香炉里针对我下的迷香,此时房间里的安魂香镇定馨宁,我的手被握在自己亲哥哥的手里,大块头的脑袋一耷一耷,正打瞌睡。
“子涵。”我轻轻叫了一声,因着口渴,有些嘶哑。
他‘呀’地一声睁开眼,“醒了?”
说着,凑近坐了些摸摸我的脸颊。“走的时候还是小矮子,现如今个头是高了,人怎么这么瘦?是骁勇不给你饭吃吗?回头我揍他。”
我扯了扯嘴巴,勉强堆了个笑。“他对我很好。”
子涵微低着头,轻轻拍我的手。“别想太多了,往后和骁勇好好过日子吧。我算过了,三天后正是黄道吉日。”
“这么急?”我很是惊讶,“可…苏奶奶不是刚…”
子涵打断我,“别忘了奶奶在世的心愿是什么。你这个孩子从小脾气倔,我也知道你的心思,可杜云景已经死了,你想再多,日子还是要过。这世上再寻不到比骁勇对你更好的了。”
我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哥哥继续说道。“刚被派去查大云经的时候,实在是毫无线索,这才托骁勇去接近白雅问。你也知道那小妮子从小就和你过不去,骁勇起先不同意,后来实在拗不过我。所以这事,你要怪就怪大哥,不能把这笔帐记在他头上。”
我狠狠白了子涵一眼。“好得很么…为了破案,出卖妹妹。”
子涵挠了挠脑袋,“这个…没办法中的办法。”
“郭大炮,白鹤扬,还有徐敬业,三人利用大云经互通有无,传递消息。若是能找到线索,就是抓到了谋反的证据。你找不到破译的方法,就让小勇哥前去接近白雅问,要是白鹤扬有意将他招婿,便能探悉□。”说着,我拘起手指,敲了敲他脑壳。“笨!要是小时候懂得跟着爹爹看一会儿佛经,哪怕真真只有一会会儿,大云经的案子早破了。也就不用让小勇哥…”
我说着说着,声音渐轻,虽是无奈,却又不得不承认,正因为这些小事积累在一起,才使得我和小勇哥越走越远,走到今天,颇令人唏嘘。究竟是子涵高估了我和骁勇的感情,还是我们的感情本来就经不起推敲…
时至今日,割断祭台绳索的真正理由浮出水面:英雄救美。
桥段是老土了些,却胜在拐用。白雅问似乎是很吃这一套的,当时还狠狠的数落了我一番,看戏逛街更是没少给我颜色看,以为小勇哥对我弃之若敝履,她这才相信我的青梅竹马是对她上了心。
“谁知道你和杜云景随随便便就找到了破译大云经的方法,也就是从那天起,骁勇打死不干了。”子涵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别怪我罗嗦,这世上再找不到第二个人待你这样好。误会解释清楚,以后时日久长,你们还会和当初一样。女儿家的心都不是石头做的,你总有一天会懂得。”
我垂眸握住他的手,“你还记得宝儿吗?”
子涵被我问得一头雾水,“怎么?”
“小时候宝儿最喜欢缠着你,哥哥你喜欢过她吗?”
子涵摇了摇头,一脸狐疑地看着我。
“宝儿后来还缠着小勇哥,你说她又喜不喜欢他呢?即便是喜欢的,可就在去年底,宝儿嫁到碧玺去了。嫁给一个老实的手艺人,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自家的哥哥能有多少水平当然只有我最明白,即便如此循序渐进,子涵还是瞪大了眼睛等我揭晓答案。“虽然小时候我也爱缠着小勇哥,可是子涵你明白吗,到头来这层亲厚并不见得是爱情。”
窗外路过的小鸟唧唧啾啾,引得我目光向外看向蓝天,是飞鸟如常。
“子涵,天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武夫难得百般耐心,顺着我的神思,歪头想了一会儿。“不知道,但是大凡男人,都是喜欢做翱翔的雄鹰吧。”
我笑笑,不再说话。
困乏的靠着床沿喘息,目视可见之处是合欢花的刺绣。无人能懂,没有星星的天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走了,我的天也就塌了。
子涵知道我心里想的是谁,却又一再自私的希望我能做一个对大家都好的决定,能轻松的过后半生。但是,我能吗?
“子涵。”我指了指桌上的茶壶,他为我倒了一杯水。
“帮我一个忙,替我把福贵叔找来。天这么凉,他还停在院子里,我想早些回去将他安置,好吗?”
子涵看着我发红的眼眶,点点头替我传话给福贵叔。
之后,福贵叔随我回到江汀阁,李念出资买的那套上好积阴木棺材里躺着我的心上人,于□之中偏安一隅。
我推开棺盖,趴在檐边,想起去年早些时候,他受伤从屋顶上落下,像一只折损了翅膀的大鸟,气息浅弱,莫名其妙的在我手里活过来。彼时嘴角含笑步步逼近的大色狼说,“我只有色,没有财。” 他说的这种无耻话,和我干的那些乌龙事,现在回想起来,就像蜜糖里渗出砒霜,令人肝肠寸断。
当时唇红齿白的少年,眼下唇色苍白的吓人,血色尽失。胸口还插着由镇魂弩射出的箭,在他心口的位置留下一滩血,凝固之后,隐隐泛黑。
我大可以假手于他人来做这些事,省得伤心,其实是个好法子。但偏偏又容不得别人碰他,于是只好亲自动手替他整理仪容。
吩咐富贵叔烧了点热水,我动手除下他上半身的衣裳,从高处坠落,骨头尽碎,可以说血肉模糊。
不停告诉自己要专心,可我硬是没忍住,手指情不自禁顺着他的额头,流连到脖子上。这地方,留有我太多的印记,每夜的亲吻,始于此,终于此。
只是,我的手指滑倒肩胛骨之处突然顿住,心里有一根芽儿,轻轻冒了头。
我猛地低下头来,死命盯住肩颈部位,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看。确认,确认,再确认。
夜探金记那回,小勇哥射过一箭,箭头断在萝卜的肩胛骨。当时他死活不肯上麻药,还取笑我。为了不给他留疤,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肩胛骨这里的皮肤还是能看出一些细小的不平整。而眼下这个部位,干干净净,白白嫩嫩,最重要的是,没有红痣。
按照正常逻辑,如果多了一颗红痣,我们可以解释为从高处摔下,血肉模糊的细小伤口。或者被人用针刺过之类的,总之,可能性有很多。而要凭空消失一颗红痣,这就不正常了。萝卜的肩胛骨稍微向上一些的地方,有一颗小的不能再小的红痣,这种事情别人不知道,只有当事人,和我这个与他脱光了上半身蹭来蹭去的人知道。从上药,包扎,甚至到事后大色狼要求呵痒痒补偿他,这个地方我没少亲…自然,这种话没办法对别人说,是属于我和他私密的不能再私密的事儿了。
可以想象,当福贵叔提着热水来的时候,发现这个破绽的我,正捂住脸蹲在地上嘤嘤的哭着。这是喜极而泣,喜极而泣!
但却有口难言,像一个黑暗里的路人突然看到了曙光,像溺水的人突然被捞上了岸,各种心酸袭来,抵不住希望的憧憬,夹杂着一丝不安惴惴。总之,情绪很复杂。
身后的嫣红的海棠随风摇曳,我坐在那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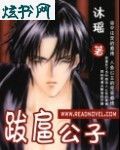



![[红楼]世家公子贾琏封面](http://www.cijige2.com/cover/1/138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