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有闲-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图古本尊有口难言,若是让人家晓得他乌溪国以医蛊之术横行于世,到头来皇子竟不慎败于本阁主之手,颜面何存啊!乌溪国国体何存啊!
两害相较取其轻,这个哑巴亏阿图古是吃定了。
或许有人觉得同白雅问比起来,我对阿图古十分宽容,只不过稍稍改变了他喜好的方向,将他从一个有正常爱好的普通青年变成了有特殊爱好的文艺青年,其实不然,本阁主对于他的未来,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我与他初次相遇,并非在茶楼而是在枭山上,他亲自带了一队兵围剿黑风寨,意图放火烧山。当时马上那个小官儿,便就是阿图古了。只不过由于我仅仅是看到了他的背影,而未看见正脸,所以往后哪怕觉得他脸熟,也一直没有认出来。
其次,我与小伙计夜探金记时,他不但下令放火,还让薛煜琛放箭射杀小伙计。而薛煜琛长期受制于这个狗腿子,自然也是憋屈的很。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因为百里红。
这三笔帐,滚雪球般的结成了一个大梁子,压在了本阁主的心头,时时提醒我要将此人除之而后快,但我一直隐而不发,为的便是有朝一日他图谋什么,我毁什么,他越是想得到,我越要令其求而不得。
既然笨蛋皇子痴人做梦,希冀着有朝一日乌溪国可以铁蹄踏上我大覃疆土,他作为皇子,继承大统,坐拥江山,外加后宫三千,那本阁主便十分不小心的将他如今断袖的事情宣扬出去,成了整个九州大陆上人尽皆知的秘密,就算燕王不打他乌溪国了,他老爹也不会把皇位传给他,成不了君王,又何来所谓的早朝呢?称霸九州的梦想终归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春秋大梦。
再者,阿图古好色无耻,我便因材施教,对他说,只要他断了袖,不再亲近女色蛊毒就不会发作。他听信了我的话,接受了一辈子都要当一个断袖的事实,但我其实是诓他的。就在他一连十日都宿在四季坊的男风馆后,终于不支暴毙,化成了一滩血水,为坊间野史轶闻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了一个流芳百世的断袖。
‘朕与将军解战袍’这首歌谣因为阿图古的死而红透大江南北,本阁主顶着窈窕的脸面,前后略赢了一些薄名,连带着窈窕君的字画,春宫图也一并畅销,生意做得蒸蒸日上,活得还挺滋润。
而窈窕以前为了接单方便,一直住在四季坊的后门杏花巷子,说的好听叫满楼红袖招,说的难听便是乌烟瘴气。自我住进窈窕的居所以来,四季坊的老鸨更是快将门槛踏破了,次次来的目的都一样,就是不停撺掇‘窈窕’,即现在的我,下海卖身,勇敢的投入到青楼事业中去。我不能断了窈窕的财路,只能勉强与其周旋,当真苦不堪言。
除此以外,终日无所事事。
白天将一个纨绔扮演得惟妙惟肖,夜深人静之时,却难免会胡思乱想。
尤其是转眼过了仲夏,入了秋,小伙计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消息,我心里便生出很多疑问。
虽然不愿意相信,但事实却容不得我不信,或许真如白雅问所言,小伙计就是徐敬业他们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所以即便在金记那样的重重包围下,他也能逃出升天。只是这样一来,他所受的伤就全是为了瞒骗我的苦肉计么?
那我先前的所作所为该有多傻啊?!
为了他掉眼泪,为了他夜不能寐,眼看我越陷越深,他乐在其中。
想到这些,我时常夜里睡不着觉,屡屡告诉自己断了不该有的念头,可偏偏那些零星的片断细节一股脑往心里钻,钻得有些疼,只好独自一个人提着酒壶夜深了还在外头游荡,稀里糊涂的醉生梦死。
秋日夜凉如水,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城楼,登上了朱雀台。
一切都不再是老样子。
以前来这里,他还在我身边,指给我看各处的风景,告诉我那里的风土人情,还说好要一起走遍天涯。
以前来这里,徐敬业还未起事,天下太平。
如今从城楼上看出去,大覃已被分成两块,整个江南成了徐敬业的囊中之物,平州,包括甜水乡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
而我蹲坐在地上,抹了把眼泪对着月光下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影子哭诉:“你说过卖身契永远有效的…你说的…骗子。”
无人回答我,只有风,呜呜的低吟。
在城楼上傻傻站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我踉踉跄跄的滚下来,见到往来的路人都聚集在一张布告前面,便停下来打探一二。
原来是徐敬业命白鹤扬拟了一份讨伐檄文,洋洋洒洒的对武皇作为一名女性进行了深度的人身攻击,曰: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秽乱春宫,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惑主。……神人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
末了不忘点题,大声疾呼:试问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更多的还有人群里流传着关于大夏三皇子加入徐敬业阵营的传闻。
据说三公子是如何如何巧施连环计夺了江南数城,又据说是如何如何连克坚城,拯救黎明免于女帝的暴力统治,还有他八岁那年随手画了张图,便不费吹灰之力令甄萱亡了国的往事…
男女老幼听了连连摇头称,“大覃看来气数已尽,是要玩儿完了…”
我默默从人群里退出来,一个人往回走。
我想,他必定是将我当作一个笑话。
抱的时候也好,亲的时候也好,都是做给别人看得。
无关真心。
☆、江汀阁内幕——稍息生波澜
回到杏花巷子;一头栽倒在床上睡了会儿,再起来时已过了正午;天边的云慢悠悠的飘着;泛着淡淡的金。四季坊的老鸨再度登门造访,见我肿着一双核桃似的眼睛;关切的问。“嫣然啊,你这是怎么了?”
窈窕的真名叫做纪嫣然。虽然我冒充她有一段时间了;但每次听到人家唤我‘嫣然,嫣然,’我始终有些反应不过来;愣了片刻才呐呐嗯了几声;摆手道:“无妨。”
她挥着团扇;笑的神秘兮兮:“嗳,别说妈妈我不提携你,今晚上可有好些个大人物要来四季坊呢。我着了锦瑟作陪,那丫头饮酒作乐,唱歌跳舞是样样使得,唯独亏在肚子里头晃不出丁点儿的墨水,论到吟诗作赋,更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一个闷屁来,唉,你瞧我这也不是没办法么,整个甜水乡,女子之中,再找不出与你一般的造诣,我这不,连七弦琴都替你备好了!所以…呵呵…”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还是为了劝我卖身…
我叹了口气,酝酿着今次不知该用什么样的借口推诿,老鸨却已等不及,凑近了我耳语道:“我知你素来眼高于顶,一些个纨绔子弟是皆皆瞧不上的,可那三公子哪里就是普通人,如今整个九州哪个姑娘不盼着他的垂青…”
我一愣,没有直接回绝,而是问道:“三公子?哪个三公子?”
老鸨用扇子轻轻拍了拍我肩膀:“傻姑娘,还有哪个三公子,大夏顶顶俊的那一个呀,眼下这样的世道,谁也说不好,保不准明天就改朝换代了。听说这杜三公子是个厉害角色,我琢磨着若是伺候的好,荣华富贵自然不在话下。”
她还待继续劝说下去,却哪里料到我并非似往日那样与她打太极,反而十分顺从的点头道:“妈妈说的有理,且容我梳洗一番,晚些时候就到。”
老鸨张大嘴巴,愣了好一会儿,怕我反悔似的,赶忙拉着我的手往外拖。“你哪里懂得打扮,来来,随我去,我差人替你张罗。”
于是本阁主便被无良的老鸨拖进了四季坊的某一处上好厢房,胭脂水粉涂了一脸,抹胸罗裙套了一身,通通都是里三层外三层,导致我照镜子的时候险些认不出‘自己’。
老鸨验收成果的时候,笑得好像一朵风中摇曳的喇叭花,拉起我的手横看竖看,最后还乐呵呵的在我发间插了一支金步摇,闪的我睁不开眼。
对于自己花花绿绿的脸我着实不大习惯,一直垂着脑袋失落伤情,她却一直赞不绝口:“唔,要的就是这种欲拒害羞,楚楚可怜的神态。”
我:“……”
好不容易熬到傍晚时分,橘红的流霞映得人面似轻薄的桃花,我着实闷的慌,便起身踱出阁楼,沿着九曲桥缓缓行走,水池里有成群的红色锦鲤,争相扑食,我在假山一角的石头上坐下,问路过的下人们讨了些米糕,掰碎了一点点往湖里投。
有熙熙攘攘的喧嚣声从身后传来,自远及近,我始终没有回头,直到许多人行至身边,我才发现,竟是一人在团团包围之中,似众星拱月一般,从我身边经过。霎那,我怔怔的望着他,米糕自手中脱落,整块掉入湖中,引来一群鲤鱼争先恐后。
那人鸦发高束,脚缠金蟒,眼睑开阖的扇动如同振翅的凤凰,眉目冷峻,带着一股不可高攀的桀骜。以前,他的身份是我的小伙计,现在,他的身份是大夏皇室的杜三公子。
除了有几个贴身的扈从在他近旁之外,还围了一群莺莺燕燕,沿路叽喳个不停,企图获取他的注意力,锦瑟便是其中之一,当听见另外几个稍许可以舞文弄墨的歌姬将他的举手投足比作天上的星辰日月,当即不甘示弱,别出心裁的指着池中的红鲤鱼道。“瞧,这些小家伙见着三公子也忍不住想要亲近呢。”
几个姑娘连忙称是,他却不过是闲闲地朝池中的锦鲤望了一眼,抿了抿唇,就这样沿着九曲桥走过,自始至终不曾看我一眼。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觉得一定是因为他没有认出这张画皮背后的,我的真面目。
黄昏日暮,地上万物的倒影逐渐湮灭,是时候该要出席高官们的聚会了。我掸了掸裙摆,起身也要向水榭去,突然又听闻一阵狗吠,是再熟悉不过的狗吠,我朝思暮想的狗吠啊——!
转过身,见到李翊轩摇着一柄折扇施施然向我走来,衣袂迤逦,翩若行云。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朝他张开双臂,那个瞬间,他脸上闪过一抹诧色,随即凤眼轻轻弯起,眼角似挂了一株桃花,徐徐绽放。
池畔的垂柳轻轻荡漾,他倏的收起折扇,也朝我这个方向羞涩的张开双臂。
“彪彪——!”我深情的呼唤。
“汪汪——!”
顷刻,一只大狗朝我飞奔而来,眨眼间已扑入我的怀中。“嗷呜!”
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以窈窕的名义生活了这么久,每每思儿心切,我都恨不能立刻去瞧一瞧它,可如今整个甜水乡的人都以为本阁主去见了阎王,哪里能轻易露出破绽,是以我无论如何都只能想想,不能付诸于行动。
眼下与丧彪久别重逢,如此感人肺腑的一幕,如此催人泪下的一幕,李翊轩竟然不为所动,反而是阴沉着一张脸,恨恨的将我望着,止步不前。
随后,也不理会我与丧彪嬉闹,径自向水榭而去。
我跟在他身后压低嗓门说:“谢你照顾了它这么久。”
不知是不是我多疑,仿佛是听到他一声冷笑,尔后再无声息。
九曲桥尽处的听香水榭,四面临湖,支开窗棂便可见到不远处的假山旁种着红枫,开的如火如荼。
李翊轩推门而入,引得斜阳入户,我紧随其后便刚好看到落日的碎金点点映在那人的背脊上,似镂空雕琢的窗花。
徐敬业手执一杯酒将将抬起至唇边,还未饮下去,却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站在身后的薛煜琛说道:“啊,煜琛啊,你也来坐吧。”
这暗示的意味很明显,是将薛煜琛看作自己人了。
只不过李翊轩偏偏此时步入,位子又只有三个,该谁坐好呢?
杜阿三,徐敬业和薛煜琛眼中,李翊轩是君,该要上座,但还有其他一干包括龟奴,琴师,丫鬟等等在内的不明真相人士,他们眼中公子轩虽然有钱,却是个帅哥暴发户,薛煜琛是带着官职的,且还是徐大人开口邀请入座,所以该入座的是薛煜琛。
一时间,室内气氛尴尬。
谁也不说话。
倒是背对着我们的杜三公子原本正津津有味的听着锦瑟唱琵琶曲,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扣着桌子与曲调迎合,闻言却冷冷开口。“凡事可都有个先来后到。”说完,向李翊轩伸出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道:“你来啦。”
李翊轩一掀袍角,坐定后笑答。“恩。”
三角的圆桌已无空位,薛煜琛站的笔直,对徐敬业毕恭毕敬的颔首。“卑职站着就好。”
徐敬业不再说话,专心听曲。
我站到李翊轩身后,替他斟酒。
丧彪一直跟着我们。狗的灵敏度是天生的,即便我易了容,它都能轻而易举的认出来,但此刻却不敢靠近杜三公子,可见,它也晓得眼前的人再也不是江汀阁中那个会拿鸡腿逗它的小伙计了。
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见风使舵的狗才是好狗。哀哀的低呜一声之后,丧彪果断钻到了李翊轩的袍子底下。
我默默叹了口气,真是一只没节操的狗啊,这么快就改投阵营了…
大约正是这一声满腔愁绪的低叹,让人以为是对于锦瑟所弹的苍山误有感而发,因这首曲充满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小女儿的情思,徐敬业听了便不大喜欢,让老鸨换上一曲助兴。
无良的老鸨乐呵呵的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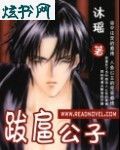



![[红楼]世家公子贾琏封面](http://www.cijige2.com/cover/1/138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