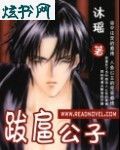善解公子衣-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有他一半的离经叛道,我早和商陆在一起了,指不定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没意思,没意思。 接下去两日我都在山客居里窝着。到第三天,长歌海月传来消息,说云氏与长歌的契约成立了,他不日将发兵玉璧城,以匡复云氏皇朝为名,攻打白玉京。 这是大家都开心的结果。长歌海月说为了庆祝,于山客居中摆下一桌宴席,大家同乐。 金需胜和包金刚欢欣鼓舞,欣然赴约,并勒令我盛装出席,以显云氏诚意。 这两个蠢货,长歌海月他又看不见。 宴席间觥筹交错,所有人都喜气洋洋,除了我与长歌海月。长歌海月是一贯那懒洋洋欠抽的表情,我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个我从前不敢深想也不敢细想的结局终于到来了——我和商陆,彻底地对立了。 又或者从一开始,我与商陆就站在相反的歧路上,以为走在一起了,其实不过是擦肩而过的一个聚点,然后各自越走越远。 怀着这样的惆怅,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便分外萧条,第二日爬起来的那张脸惨不忍睹,我随意抹了一把便走出房门。自从离开商陆后,我已经不上妆打扮了,性别模糊,形容猥琐,看得金需胜直摇头。 厅堂里,金需胜、包金刚、长歌海月,还有一夜之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谋士,齐聚一堂商讨大计。 不过把长歌海月算进去真是拉低这一屋子聪明人的平均智力了,他斜躺在榻上,眼睛半睁半阖,榻下一个侍女正替他捶腿,捶着捶着,长歌海月一只手就伸进人家衣襟里,在侍女高耸的胸脯上捏了一把。 我假装没看到,寻了一个椅子坐下,打算好好学一下他们的纵横捭阖之术。 我听了半日,听出个大概来。他们是想自玉璧城发兵,先攻下靠海的即墨城,而后自水路登陆白玉京。 自我父皇那一辈起,云氏皇朝在海上的作战能力就一直低下,船只设备简陋,士兵不服水土,打起仗来,丢盔弃甲一泻千里。所以自海路进攻,是最好不过的选择。 决定定下来后,他们开始探讨详细的作战计划,在地图上指指点点。我等他们结束后,拉住包金刚问:“包金刚,那啥呢?” “那啥?”他目瞪口呆地盯着我。 我伸出两只指头互相碾磨:“就是那啥啊……消息!” “哦哦!”他恍然大悟,自荷包里拿出一张小纸条,“公主,这是最新的消息。” 我接过那个小小的纸卷,小心翼翼忐忑不安地展开来,纸上寥寥几个字:东川王安好无虞。 我有些喜忧参半,喜的是商陆看似情况不错;失望的是昨日白天碰到的那个求药的公子,果然不是商陆。
正文 三十五
三十五 我们到达即墨城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了。 时年三月,天下尽春。即墨城靠海,种柳,柳絮被海风一吹,毛茸茸的往人鼻子里钻,我每打一个喷嚏,就喷出一团白乎乎的絮状物来,像是鼻涕一样,街上行人避走不及,我的苦闷无处发泄。 包金刚和金需胜奔走于各个谋士之间,要见上他们一面还得事先预约,我就无语了。 我也不想去找长歌海月打发时间。他永远是即墨城一朵奇葩。行军打仗的日子里,物资有限,人人只求温饱,我某日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面黄肌瘦,像是一朵小白菜,我都这样了,可想而知底下的人。 可长歌海月不同,他在他豪华的车辇里醉生梦死,我几次去找他,不是看到他腰上跨着一个起伏的女人,就是看到他背对着我,面前高椅上一个女人大张着双腿娇喘连连。 姿势之丰富,态度之豪放,令我瞠目结舌面红耳赤,不知不觉竟学会了几种,只是一想到再也不能与商陆一试,顿时觉得自己心思龌龊。 所以我说长歌海月是一朵奇葩,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在车辇里吃喝玩乐,他的部下门客谋士却在出生入死给他卖命,不起义造反简直是个逆天而行的奇迹。 我现在唯一的乐趣便是收白玉京那个眼线关于商陆的消息,自我提出非议,说上回那消息太简短以后,这回来的消息有些长:东川王近日安好,只昨夜于月下饮酒,烂醉。 我整颗心都揪了起来,又不知道具体情况,只觉得心尖像爬满蚂蚁,急得上火。 我冲到包金刚那里,劈头把纸条扔给他:“下回!让那眼线再详细点!为什么饮酒,为什么烂醉,在哪里饮酒,旁边有没有女人,统统写清楚!” 包金刚呆若木鸡,反应过来以后,无奈道:“公主,要不我把那眼线调到东川王府去?” “好啊。”我高兴地点头,“反正商陆也是我们对头,调查清楚总没坏处。” 包金刚用一种看朽木的眼神看我,像是在说,朽木都还能孵朵蘑菇什么的出来,你连朽木都不如。 我觉得如果能得到商陆的具体情况,别说孵蘑菇,让我孵豆芽都行。 长歌海月的部队浩浩荡荡从玉璧城开到即墨城的时候,以为会招到抵抗,谋士们准备了三套方针,准备见机行事拿下即墨。 只是我们都没想到,即墨人见了这秣马厉兵,毫无抵抗,即墨督护亲自开了城门迎接,我们就这么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即墨城。 后来我才知道,即墨,江湖人称小桃源。百姓没受过什么战乱,每日出海捕鱼靠海吃海,且督护又是个爱月下饮酒花前作诗的雅人,哪里见过这等阵仗。于是打着为民着想的旗号,不战而降开了城门,还特意为长歌海月在海边滩涂辟了一块平地,供军队操练。 我前几日似乎看到了这位督护的身影,他出没于长歌海月的帐中,两人像狗见了屎一般,相亲相爱地互相交流饮酒、耍乐和玩女人的心得体会。 几日过后,军队亦操练齐备。今日,便要出海了。 这一日晴空万里,长歌海月几十支船舰排在港口,桅杆与风帆将碧蓝天空都遮了半边,天地间寂然无声,只有咸湿的海风吹来兵戈金属的气味。 我站在甲板上,看着底下将士三万,铁甲银枪,仿佛天地间都回荡着一股豪气,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即墨城的督护在港口给我们送行,依依不舍地对长歌海月道:“长歌公子,待下官酿出那仙芝美酒,再来同你痛饮一场。” “好说,好说。”长歌海月笑呵呵的,眉眼弯成了月牙儿,假若他不是瞎子,笑起来该是何等绝色风采。 不过他自上了船以后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晕船了。 我笑死了,我不能想象像长歌海月这样自大自傲的人躺在床上作死的样子。 船上颠簸,晕船少不了呕吐,他又有洁癖,想必这几日肯定过得生不如死。 果然,送到他船舱里的食物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他带上船(床)服侍他的几个侍女也被骂得狗血淋头,成天一副苦大仇深地里黄的小白菜样儿。 我心里阴暗,莫名高兴地笑了几日,后来发现不对劲了。 长歌海月虽说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公子,但在他手下眼里,有一种神奇的威望。这几日他因为晕船几日不曾现身,底下的士气都有些动摇。 虽说自我们出兵海上以来,鲜少碰到商敬之手下军队的抵抗,即便有也不过零星几个不成气候,但士气这事可大可小,史上以少胜多以寡敌众之事亦不是没有,长歌海月再这样闹脾气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我想了想,决定亲自去服侍这位爷。 刚踏进他船舱,他便冷道:“滚出去。” 眼盲之人,其他感觉会比常人敏锐,这话确实不假。 我默不作声地绕过地上狼藉的物件,看到了躺在床上的长歌海月。他几日未进食,整个人看上去苍白而虚弱,只是脾气还是大得很。 “我说滚出去,你耳朵聋了?” 说话声音微弱,中气不足,但颐指气使的嚣张还是在的。 嘁,这个纸老虎。 我走过去,把他从床上拖起来,趁他开口怒斥之时将一勺白粥塞进他嘴里:“吃下去!” “滚!”他大怒,想抬手乱挥,结果因为气力不足,趴在床上喘了几口气,又干呕了几声。 我在床边上嘲笑他:“看吧,谁让你不吃东西,连胆汁都吐光了。” 他缓过来,惊怒道:“你是云小茴?!” 我觉得好笑:“不然你以为还有谁愿意来撞你枪口?” 长歌海月顿了一下,而后简直是暴怒:“你给我出去!” 我又趁机塞勒一勺粥。 他怒不可言,吧唧一口吞下去,又开口骂我。 他想推我,但又因为看不见,只能胡乱挥着手。 我有些内疚,觉得自己在欺负一个残疾人,但这个念头在我看到他生龙活虎破口大骂的样子时打消了。 “来人!” 一勺粥。 “滚开!” 一勺粥。 “云小茴你狗胆包天以下犯上罪不可赦!” 嗯?这么多词儿?好吧,三勺粥。 我就这么在他骂人的间隙喂完了一碗粥。 我猜长歌海月从小到大都没有被人忤逆过,一定是众星拱月娇生惯养地长大,依他这么心高气傲的性子,被我折辱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大概也没有别的心思想晕船不晕船、呕吐不呕吐这种事了。 所以这一碗粥喂得出奇顺利。 我把空碗一放,道:“行了,我其实很能理解你。可我既不是你喜(…提供下载)欢的人也不是喜(…提供下载)欢你的人,所以你是得体也好失态也好,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至于这么装吧。” 何况你恶心人的行径我见得还少吗。 长歌海月安静下来。 我见他有些萎靡,也好言相劝:“你喝了一碗粥了,感觉好点没?” 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半晌转过头来:“还有吗?” 这别扭的死样子呦。 我乐呵呵地吩咐下去再煮一碗米粥,几日未进食的人,果然是挡不住香喷软糯的白米的诱惑。 我对长歌海月说:“等会儿你自己吃啊。” “我看不见。” “少诓我。看不见也不影响吃饭。” 他立刻做出一副傲慢的神情:“我吃饭都有人服侍。” 我破口大骂:“滚你娘的!商陆抖没被我喂过,你知足吧!” “商陆?”他忽然神色一整,而后沉吟良久。 我为自己的失言而后悔,也沉默不语。 “原来你说的那个人是商陆,真是可惜啊。你们两一个是前朝公主,一个是当朝东川王,真是……孽缘!” 他抚掌大笑:“有趣极了!”然后想了一下,“改日要叫我的戏班子以你们为原型编个戏本子,演出来我瞧瞧。” 我愤然起身,白喂这只狗了! 长歌海月开始进食后,整艘船上下欢欣鼓舞,就差放几支烟花普天同庆了。 但他不知又开始作什么,指明要我去服侍。 我嗤之以鼻,翻了个白眼,就当没听见。然而后来又转念一想,何苦与一个残疾人过不去。他再让人讨厌,究竟只是个瞎子,只能放纵自己通过别的感觉来获得满足,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就当为我和商陆积德吧。 于是我开始每天去他船舱报道一次。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难度的挑战。 你要如何向一个自出生便看不见的瞎子解释红是什么,妃红品红海棠红,黄又是什么,鹅黄杏黄樱草黄。你能做到吗?反正我不能。 所以我们的对话一般是以下这样的: “红是什么颜色?” “太阳的颜色。” “太阳是什么颜色?” “红色。” “所以问你红是什么颜色啊。” 我怀疑他是故意的,这样的对话几次下来以后,我的脑筋络大批阵亡,深感疲惫。 第二日我带了个暖手炉过去,在长歌海月又一次问起红是什么这个千古难题后,恶狠狠地拿这个烫了他以下,不耐烦道:“红就是这种感觉!” 长歌海月瑟缩了一下,沉默良久,笑吟吟地问:“那松花色和秋香色呢?” 我愤而起身。 我们在海上行船七日后,到达沿海一个港口。 不是每一座城池都如即墨那般品性温良,迎接我们的是港口上排列整齐的一万大军。 我做公主时,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我清楚云氏皇朝的兵力分布与强弱,商敬之不费一兵一卒发动宫变,他的傀儡皇帝上位以后,三年来也没有什么大的动荡与武力斗争,所以如果我没预料错的话,商敬之现在有的兵力,数量应与我父皇在位时无多大出入。 一万兵力,大概是商敬之所有军队的五分之一,且因海上行军比陆地快,为了赶在我们之前,他肯定是就近调入了这支军队。 兵家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们如此仓促,后方供给未必比我们好到哪里去。 我把这个情况告诉长歌海月,他点头表示知道了,而后与我登上甲板观战。 说是观战其实不妥,看的只有我一个,他只是站立在那里,神色肃然,时而侧耳倾听兵戈交接的声音。海风将他宽大垂地的长袖吹得猎猎鼓胀。 有那么一刹那,我有点理解为何他的部下对他敬若神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