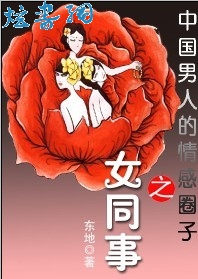中国散文-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着急和焦虑。但是,着急和焦虑并不一定要悲观。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第一,当代青年并非铁板一块、都是一个模子制成的,青年中间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先进和后进,英雄人物和犯罪分子都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个方面就断定其时代和队伍的全体。第二,五十年代的青年很好,这是事实,我们要发扬那个时代的好传统;但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青年即使有动乱留下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一些收获,虽然这些收获说来痛苦得很,花的代价太大,但毕竟是新收获。比如说张志新一类的青年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我是远不如这些青年的,在探索真理勇气上,我比这些青年差好多。再比如说有些青年,在别人武斗、打派仗时,埋头苦干一种事业,至今已成令人瞩目的人才。所以不能说现在青年“一切不如过去了”。过去有过去的好,今天有今天的好,明天还有明天的好。第三,一时之间的社会风气、社会思潮,自有产生它的社会根源、社会条件,比如实行经济上开放、搞活政策后,一些人失足落水、走向反面,或者本来就是反面的,这一回暴露了出来,这些问题不只是青年中有,壮年、老年中也有,党员干部中不也是有一些人很不象样子吗?所以发生一些问题,不能只是责怪“小青年”。持悲观情绪的同志的最大错处,就在于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朱伯儒、李燕杰同志就不悲观,他们深入到青年中扶正祛邪,乐观地工作,越做越有信心。
另一种偏颇是对青年问题的严重性估量不足,看得太简单,说严重些是掉以轻心,任其自流,不管不问,或者是不敢管,不敢问,怕麻烦,只是讨好他们,迎合他们,不认真地进行规劝和引导。
还有一些人利用青年轻信、好奇的心理,以售其奸,以有害的思潮影响青年,把“一切向钱看”“人格商品化”的腐朽东西兜售给青年,对这类二道贩子、奸商要警惕,要打击,当然这种人已不属于认识上的偏颇了。
我的交心话人贵知己,知己必须交心。终日相聚,客客气气,但从不交心,并不算认识,更谈不上是知心朋友和同志。同志的“志”字底下有一个“心”字,人和人的距离是以心的距离来计算的。
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单写一段交心的话,并没有什么私话,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一生的痛苦、蹉跎太多,我总觉得形之于文,也说不尽我心中的衷曲。比如,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许多亏,这些亏教训过我。老了的时候,如有可能,就告诉后来者,向他们说一句:“小心上当!”当然,这只是愚者千虑之一得。
为了把话说得简捷了当,我把这些交心的话用短语形式写一写,说得不谦虚一点,也算自我杜撰之格言吧:一、自己看,自己想。书上的话,先生的话,要看、要听,但可悲的是自己无主见,不加分析判断,不管正确与否放开脑子叫人家来跑马。
二、敢爱敢憎,爱憎分明,愈分明愈好。不要做模棱两可的人,虽然这种人活着更保险一些,还可能飞黄腾达、万事亨通。但这是中了西方人的滑头哲学、实用主义和中国人中庸之道的毒。宁死不当这种人。这种人好象优点很多,可是只有一条缺点就够了——这种人对社会没有好处。
三、兴趣要广,精力要专。对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有兴趣,有可能就学一点。学多少,算多少,皮毛点也不可怕,只要有自知之明就行。但在学一样、干一样时,要专心致志,集中全力,不到一定程度决不罢手。广与精有矛盾,又可统一。
四、对知识如干海绵,要残酷地向对象榨取。在学业上我坚信这样的经验——浅尝辄止,一事无成;锲而不舍,金石可断。
五、对生活要热爱。人生的道路宽阔得很,人活着很有意思,何况又是“万物之灵”。生活里充满乐趣。当然,对于自己羡慕的东西要多想一想:值得羡慕吗?
如真值得,那不只是羡慕,自己也要做。
六、有雄心、有抱负,但不骄不躁。不要怕别人说长道短,只要认准方向就干下去。但不可任性,不可违反社会公德;那不是雄心,是私心。
七、随时准备赴大义。灾难会有的,祖国和社会,同志和朋友,都可能遭遇灾难。比如敌人来了,或者坏人在干坏事,或者自然灾害,就要勇于赴义,甚至不惜一身性命。
八、朋友要多。但一生中真正的知己也许不多,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很有道理。连祖国和人民、生你养你的土地都不爱的人,不必和他交朋友。
多好啊!活得很美
皇冠
刘墉
“我最近好为难。”有个条件不错的男学生对我说,“我有两个女朋友,都很爱我,我也很喜欢她们,不知该选哪一个。”
“表示两个条件差不多。”我说。
“不!条件差满多的。”学生瞪着我说,“一个很有钱,家里放了一架史坦威的大演奏琴。另一个很穷,我常给她打电话,打一半,就没法说了。因为她的卧室正靠着铁道,火车过,整个房子都震动,什么也听不见,只好拿着电话发呆。”
隔了半年,遇到那学生,他已经结婚了。
“娶了有史坦威钢琴的?”我笑道。
“不!娶了铁道旁边贫民区的。”
“噢!”我点了点头,“不简单哪!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有!有一天,我到她家去,坐在她卧室聊天,突然火车过,好响!带起一阵风,把窗帘都吹起来了,那是一块很便宜的薄棉布的窗帘,她自己用手缝的。这时候,阳光射进来,我看见窗台上放了一个宝特瓶切一半做成的花盆,里面开着一丛不知名的小黄花。我问她那是什么花。她很不好意思,挡在前面说,是不值钱的花。我又问,很漂亮啊!是什么花吗?她吞吞吐吐半天,才说,“是野地里挖来的小草花,不值钱!”学生脸上露出一种好特殊的光彩,“你知道吗?我那时突然产生一种感动,冲上去抱住她,叫她不要那么说,不要说不值钱,美的感觉是不能用钱衡量的!就在那一刻,我发觉,我深深爱上了她。”
动心灵的美,不见得华丽学生的话,常浮过我的脑海,我常想象那个浴着午后阳光,被风拂起的窗帘,和窗台上逆光看去的那丛野草花。多么平凡,多么美!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去花店定花,花店老板随手拿了一枝玫瑰送我。
回家,我把那枝玫瑰插在细细的小瓶子里。隔两天,情人节的花也送到了,是24朵玫瑰。我又找了一个大大的水晶花瓶,放进去。
奇怪的是,那24朵馥郁的玫瑰,和旁边孤零零一枝,有种特别的感动。觉得好精巧、好细致、好有慧心。
也想起有一次到前历史博物馆馆长何浩天先生家去。他的家布置得很清简,案上没花,只有一盆番薯冒出的青苗。淡红色的番薯皮,翠绿弯转的藤叶,给人一种特别的雅致。让我回到童年,记忆中父亲用小水皿养的蒜苗,在冬天的窗前,盎出一片新绿。
真正会心的美,常像是简简单单的禅宗水墨画,不必华丽的色彩,也无须复杂的构图,却能在那“空灵”处引人遐想,给人美。
美,帮我们度过人生的苦难自从女儿上幼稚园,也常常给我这种美。
她有个放劳作的篮子,乍看好像垃圾桶。里面有用超级市场上的牛皮纸袋做的帽子,用衣服夹子和钮扣组成的小人,用纸盘做的面具,用黄豆组成的图画。
学校动不动就发通知,要家长给孩子准备空的鲜奶盒子,或卫生纸用完剩下的“纸轴”。跟着就让孩子从学校带回用那些废物组成的玩具。
问题是,大人眼中的废物,却成为孩子的宝贝。他们不在乎世俗的价值,只在乎自己有没有感动,有没有想象。
于是,常看见小丫头举着她的劳作炫耀。先觉得她傻。想想,才发觉是自己俗。她让我又想起那个学生的女朋友,窗台上放的宝特瓶花盆,和里面的小草花。更让我想起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一段话:“你们将来教美术,目的不应该是造就几个专业的艺术家,而是培养一批有美感的国民,让他们能从最平凡的东西上,见到美,也懂得利用身边平凡的东西,创造美;使他们对生活有一种积极快乐的态度,而不只是现实的价值;更使他们能以美的感觉,面对人生的苦难。”
人,就是一种美记得初到纽约的时候,去苏活区看一位艺术界的老朋友。进入他的工作室,我差点窒息。
只见一片烟尘飞扬,四处弥漫着浓浓的油漆味,他正埋头修理古董。
他把顾客送来的瓷器碎片,慢慢拼起来。先用胶水黏合,再用瓷粉填补、打光。然后把断缺的花纹,照原来的样子画好。再用喷飞机的罐装油漆,将表面喷成釉彩的光亮。
朋友摘下口罩,陪我走出工作室,小心跨过残雪的泥泞,步上曼哈顿昏暗的街头。
“多美啊!”他一面呵着手、吐着白烟,一面抬着头,看那四周像要围过来的高楼,近乎咏叹地说,“纽约!一个真正看到人的城市。”指指高楼,又指指蹲在街角的浪人,“都是人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人,多美!”我看着他的脸,看那脸上的感动,也从心底产生一种感动——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那么不如意的时候,他依然快乐,依然生活得很美。
二十年前的女性
常州日报
苏童
对于女性的印象和感觉,年复一年地发生着变化。世界上基本只有两类性别的人,女性作为其中之一,当然也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因此一切都是符合科学原理和我个人的推测预料的。
20年前我作为男童看身边的女人,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恰适70年代的动荡社会,我的听觉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脆的宠亮的女人的高呼声×××万岁,打倒×××,那是街头上高音喇叭里传来的群众大会的现场录音,或者是我在附近工厂会场的亲耳所闻。女性有一种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特别适宜于会场领呼口号的角色,这是当时一个很顽固的印象。
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衣裳,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也是蓝、灰黑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
女孩子过了18岁大多到乡下插队锻炼去了,街上来回走动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妇女,她们拎着篮子去菜场排队买豆腐或青菜,我那时所见最多的女性就是那堆拎着菜蓝的边走边大声聊天的中年妇女。还有少数几个留城的年轻姑娘,我不知道谁比谁美丽,我也根本不懂得女性是人类一个美丽的性别。
我记得有一个50岁左右的苍白而干瘦的女人,梳着古怪的发髻,每天脖子上挂着一块铁牌从街上走过,铁牌上写着“反革命资本家”几个黑字,我听说那女人其实只是某个资本家的小老婆,令我奇怪的是她在那样的环境里仍然保持着爱美之心,她的发髻显得独特而仪态万方。这种发型引起了别人的愤慨,后来就有人把她的头发剪成了男人的阴阳头。显示着罪孽的阴阳头在街头随处可见,那剃了阴阳头的女人反而不再令人吃惊了。
那时候的女孩子择偶对象最理想的就是军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才能做军人的妻子,退求其次的一般也喜欢退伍军人,似乎女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崇尚那种庄严的绿军装、红领章,假如街上的哪个女孩被挑选当了女兵,她的女伴大多会又羡又妒得直掉眼泪。
没有哪个女孩愿意与地、富、反、坏、右的儿子结婚,所以后者的婚配对象除却同病相怜者就是一些自身条件很差的女孩子。多少年以后那些嫁与“狗崽子”的女孩恰恰得到了另外的补偿,拨乱反正和落实政策给他们带来了经济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处。多少年以后,他们已步入中年,回忆往事大多有苦尽甘来的感叹。
有些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的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她们的照片几乎如出一辙,站在农村的稻田里,短发、戴草帽、赤脚、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隐约可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圈红字。
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这样的傍晚时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们或者会到免费开放的公园里去,假如女孩无法抵御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