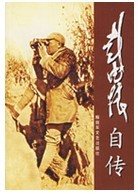巴金自传-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十年来在一些学校或者农场里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园艺人材。他在当时的朝鲜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台北都曾见到他。今天我还没有中断同他的联系。他在湖南农学院教书,有时还托人捎一点湖南土产来。我还记得四十几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到上海来,总是住在马宗融的家中,几个月里他的头发就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妇就是后来发表短篇小说《生人妻》的作者罗淑。抗战初期罗淑患病去世,我们在桂林和重庆相遇,在一起怀念亡友,我看见他几次埋下头揩眼睛。
过去像梦魇一样给朝阳驱散了。朋友柳已经年过八十,他仍然在长沙坚持工作,我仿佛看见他的满头银发在灿烂阳光下发亮。听说他从解放了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得了鼓励,我应当向他祝贺。《火》第一部出版时我在后记的末尾写道:“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我不曾实现这个愿望,但我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朝鲜人民已经用行动写出了光辉诗篇,也一定能完成统一朝鲜的伟大事业。
关于《龙·虎·狗》
在以前几篇《回忆录》里我谈过了中、短篇小说和童话,这次我想谈谈我的散文,我就从《龙·虎·狗》谈起。《龙·虎·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在昆明编成,寄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陆圣泉,由他发排出版的。我手边还有这个集子的两种版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上海“初版”和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渝二版”,不用说,重庆版是用很坏的土纸印刷的。
重庆版第一辑中少两篇文章(《寂寞的园子》和《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原因,重庆版和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一般书刊一样,是经过了所谓“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的,封底还印着“审查证图字第二○三○号”字样。但是那两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军的,不会得罪重庆市的审查老爷,而且他们也没有胆量抽掉它们。现在想不起不要紧,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我用不着在这件小事多花费脑筋。
我在抗战时期到昆明去过两次,都是去看我的未婚妻萧珊。第一次从上海去,是在一九四○年七月;第二次隔了一年,也是在七月,是从重庆去的。《龙·虎·狗》中主要的十九篇散文是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只有第一辑里收的四篇文章中的前两篇是第一次在昆明小住时写成的,后两篇则是到四川以后的作品了。今天我重读这本集子,昆明的生活又非常显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寂寞的园子里,大黄狗是我的一个和善的朋友。
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这年暑假萧珊去昆明上大学,我在上海写小说《秋》。那个时候印一本书不需要多少时间,四十万字的长篇,一九四○年五月脱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书店发卖了。我带着一册自己加印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成的一章《火》的残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海轮,离开了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那天在码头送行的有朋友陆圣泉和我的哥哥李尧林。我在“怡生轮”上向他们频频挥手,心里十分难过。
我一去就是五年。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多陆圣泉就遭了日本宪兵队的毒手,我回到上海只能翻读他用陆蠡笔名发表的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而李尧林呢,他已经躺在病床上等着同我诀别,我后来把他的遗体埋葬在虹桥公墓,接着用他自己的稿费给他修了一个不太漂亮的墓。然而十年浩劫一来,整个公墓都不见了,更不用说他的尸骨。
一九四○年从上海去海防毫无困难。需要的护照,可以托中国旅行社代办,船票可以找旅行社代买,签证的手续也用不着我自己费神。那次航行遇到风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但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海防。在海防我住在一家华侨开设的旅馆里。上船时我是单身一个,在旅馆里等待海关检查行李时我已经结交了好几位朋友。我随身带的东西少,一切手续由旅馆代办,我只消出一点手续费。同行的客人中有的东西带得较多,被海关扣留,还得靠旅馆派人交涉,或缴税或没收,由那里的法国官员说了算。还有人穿着新的长统皮靴,给强迫当场从脚上脱下来。总之,当时从上海到所谓“大后方”去的人大都经由海防乘火车进云南,去昆明。我经过海防时法国刚刚战败,日本侵略军正在对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侵占越南,形势紧张,这条路的命运不会长了,但这里还是十分热闹、拥挤,也正是旅馆里的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等在旅馆里。同行的人被海关扣留的东西都一件一件地给拿了回来。这样大家就动身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自动地组织起来,身强力壮的人帮忙管理行李,对外交涉,购票上车,客栈过夜,只要花少许钱都办得顺利。我们从海防到河内,再由河内坐滇越路的火车到老街,走过铁桥进入中国国境。火车白昼行驶,夜晚休息,行李跟随客人上上下下,不仅在越南境内是这样,在云南境内一直到昆明都是这样。但是靠了这个自发的组织,我在路上毫不感到困难。跟着大家走,自己用不着多考虑,费用不大,由大家公平分担。所谓大家就是同路的人。他们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还有到昆明寻找丈夫的家庭妇女。和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职员和一位昆明商行的“副经理”,我们在海轮上住在同一个舱里。“副经理”带了云南太太回上海探亲,这条路上的情况他熟悉,他买了好几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酒要带出去,为了逃税,他贿赂了海关的越南官员,这当然是通过旅馆的服务员即所谓接客人员进行的。我看见他把钞票塞到越南人的手里,越南人毫无表情,却把钞票捏得紧紧的,法国人不曾觉察出来,酒全给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干脆,这样的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们真想得出来,也真做得出来。
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在河口住进了客栈,安顿了行李,就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去登记。这机关的全名我已经忘记,本来在一九四○年我用过的护照上盖得有这机关的官印,护照我一直保存着,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中,从我家里拿走后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连这一段“回忆”差一点也写不出来。机关的衙门并不堂皇,官员不多,然而他们有权威。他们检验了护照,盖了印,签了字,为首的官员姓杨。大家都给放过了,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我的护照上写明:“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长官问我在哪一家书店工作,我答说“开明书店”。他要看证件,我身上没有。他就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他们把护照留了下来。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对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么不幸似的。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英签了名,放我过去了。
这是上午的事。下午杨先生和他两位同事到客栈来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们见到商行副经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晚上几点钟请我吃饭,并约了我那两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时候三位主人又来客栈寒暄一通,同我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铁桥,拿出准备好的临时通行证进入越南老街,在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们还把我们送到客栈门口,友好地握手告别。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那个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后再也没有同那三位官员见面,他们也没有给我寄来过片纸只字。他们真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过的那一两个钟头,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愉快。
从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车,晚上宿店,我们还是集体活动,互相照顾,因此很顺利地按时到达了终点站。萧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台来接我,他们已经替我找到了旅馆。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后来不久在昆明同我见过一面,其余的人车站匆匆一别,四十年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馆里只住了几天。我去武成路开明书店取款,见到分店的负责人卢先生。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还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具。我和卢先生虽是初次相见,但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和最近一本小说(《秋》)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知道我,因此见一两面,我们就相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我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
我在《静寂的园子》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次在昆明我写的散文不过寥寥几篇,但全都和敌机轰炸有关,都是有感而发的。几篇随感和杂文给我编在杂文集《无题》里面了。书在《龙·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讲过的那两篇(《静寂的园子》和《狗》)。有些数字在我的脑子已经模糊。我说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庆的,只记得是沈从文同志介绍一位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买的飞机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挤进了越南(河口铁桥早已炸断),他们的飞机就是从越南飞来的。
对于和平城市的受难,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广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上飞机的前一两天,我和开明书店的卢先生闲谈,我笑着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他点头同意。
他的经验更丰富。前一两年他坐公路车在贵阳附近翻车,左膀跌断,在中央医院治疗,左膀上了石膏给绑在架上,发了警报后他不便下洞躲避,人们给他一把剪刀,准备在危急的时候剪断绑带逃命。贵阳市遭大轰炸时,他正在医院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关于他,我还有话可说。以前我只听见别人谈起他,例如翻车断臂的事。在昆明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见过我)。听说他本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在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一类职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