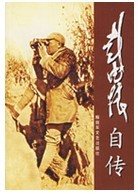巴金自传-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重宝塔来。”
他的确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宝塔的。我们第三次在学校里看见“耶稣”,他显得更瘦、更弱了。他过着更勤苦的生活。
他穿着更破烂的衣服。他花去不少的时间和学生们谈话。他热心地对几班学生讲授数学的功课。这一次我们谈了不少的话,商量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提到他的病,说起他应该休养的话,他总是打岔地说:“我们不会活到多久的,我们应该趁这时候多做一点事情,免得太迟了。”
我看见他用过度的工作摧残自己的身体,我看见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点点工作成绩。我不能够责备他。我倒应该责备自己。我们的确太需要工作了。我自己不能代替他工作,别的空话便都没有用。这个学校里充满着殉道者的典型,但是他比别人表现得最完全。在他们的面前我显得太渺小了。在他们中间我做了几天的美丽的南国的梦。
一个多月以后我游历了广东乡村回来,路过鼓浪屿,我们的船停在海中,在开船前的六七小时,两个朋友从古城赶到了。他们到船上来看我。我们三个人坐划子到那个美丽的岛屿去。这一次我们攀登了日光岩。在最高的峰顶上眺望美丽的海。我们剥着花生,剥着荔枝,慢慢地吃着,慢慢地把荔枝皮和花生壳抛到下面海滩上去。我们听着风声,听着海水击岸的轻微的声音。我们畅谈着南国的梦。我们整整谈了两个钟头,我们愉快地笑着。我的眼前尽是明亮的阳光和明亮的绿树。在这个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上我们做了两小时的南国的梦。但是吃过中饭我应该回轮船去了。
这两个朋友把我送到船上。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把剩余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耶稣”,要他用来治玻这只是一个关心他的友人的一点敬爱的表示。
船到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厦门。它掉转身的时候,我还留恋地投了一瞥最后的眼光在那形状奇特的岩石上,还有岩石中间的小桥,先前我们明明走过的,现在它显得这么高,这么校但是船再一转动,鼓浪屿便即刻消失了。我的眼前只有花和树、海水和阳光。
在上海我得到“耶稣”的信,知道他不曾医病,却用那笔款子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读书。第二年在北平朋友告诉我“耶稣”带了二十多个学生到上海,预备作徒步旅行。又过一年在东京我知道“耶稣”又带着十几个学生第二次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个患痔疮的人简直在戕害他自己了。
我从东京回来,不久他也从北方旅行归来了,这一次他坦白地说出他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话。这是第一次。话进了我的耳里,倒使我的心发痛了。我以为我们有理由说服他留在上海医玻但是他依旧坚决地跟着这一班学生走了。临行时他还留恋地说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话。
一九三七年夏天他离开了古城,到广州去。他也许是抱着医病的目的去那里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八·一三”民族解放的战争爆发,点燃了他的沸腾的血。他怀着不能抑制的热情回到那个古城去了。我知道在那里有着更忙碌的工作等待他。我相信他会把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在那里还有不少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朋友给他帮忙。
这一次我不能再拿疾病作理由来劝阻他了。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我们民族的生存和自由受到侵害的时候,保卫它们便是我们的第一件工作。他就是这样地主张的。现在轮到他来实现他的这个主张了。以他那样的毅力和能力,一定可以做出比过去更大的成绩来。
我去年十月从广州出来以后,走了不少的地方,始终没有直接得到“耶稣”的信息。不过我从别处知道他忙碌地在古城里工作。他准备着有一天用有组织的民众的力量来歼灭侵略者的铁骑。
现在鼓浪屿骚动起来了。铁骑踏进了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那个培养着我的南国的梦的地方在敌人的蹂躏下发出了呻吟。
然而使我激动的是行动的时刻到了。鼓浪屿的骚动一定会引起更大的事变。铁骑深入闽南的事情是可以想到的。敌人也许不会了解,但是我更明白,倘使敌人果然深入肥沃的闽南的土地的话,那么在那里得到的一定不会是胜利,而是死亡。那时我的南国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便会出现了。
我怀念着南国的梦中的友人,我为他们祝福。
………………………………………………
第六辑:日本之旅
关于《神·鬼·人》
最近我在看我的两卷本《选集》的校样。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
这三个短篇都是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则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会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是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景)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
于是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我买的是二等舱票,客人不太多,中国人更少,横滨海关人员对二等舱客人非常客气,我们坐在餐厅里,他们打个招呼,也不要办什么手续,就请我们上岸。不用我着急,武田副教授和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打着小旗在码头等候我了。以后的情况,我在《关于〈长生塔〉》里也讲了一些,例如每天大清早警察就来找我,问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等等,每次问一两句,都是突然袭击,我早有准备,因此并不感到狼狈。我在当时写的篇一个短篇《神》里面还描写了武田家的生活和他那所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小山坡上的“精致的小木屋”。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了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也说明武田君是一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的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我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里面,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地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的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了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是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可以,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武田君就说过:“在我们这里宗教常常是家传的。”)他想用宗教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拚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跳进深渊”去。我当时是这样判断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难说了。我在武田君家里不是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只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光景。以后我在东京、在上海还接到他几封来信。我现在记不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他来过上海,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过“黎德瑞先生”。他写下一个地址,在北四川路,是他妹妹的家。当时有不少的日本人住在北四川路,但我在日本时,他妹妹不会在上海,否则他一定告诉我。我按照他留的地址去看他,约他出来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大东茶室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像老朋友似地交谈,也回忆起在横滨过的那些日子。
他似乎并未怀疑我的本名不是“黎德瑞”,也不打听我的生活情况,很容易地接受了我所讲的一切。他的精神状态比从前开朗,身体也比从前好。我偶尔开玩笑地问他:“还是那样虔诚地念经吧?”他笑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他不曾讲下去,我也没有追问。我知道他没有“跳进深渊”就够了。以后我还去看望他,他不在家,我把带去的礼物留下便走了。他回国后寄来过感谢的信。再后爆发了战争。抗战初期我发表两封《给日本友人》的公开信,受信人“武田君”就是他。一九四○年我去昆明、重庆以后,留在上海的好几封武田君的信全给别人烧毁了。现在我手边只有一幅我和他全家合摄的照片,让我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小说里描写了武田君住宅四周的景物。可能有人要问这些景物和故事的发展有没有关系?作者是不是用景物来衬托主人公的心境的变化?完全不是。我只是写真实。我当时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我喜欢这四周的景物,就把它们全记录下来。没有这些景物,长谷川的故事还不是一样地发展。
它们不像另一个短篇《鬼》里面的海,海的变化和故事的发展、和主人公堀口君的心境的变化都有关系。没有海,故事一时完结不了。小说从海开始,到海结束。
我在《鬼》里描写的也是武田君的事情。我写《神》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还要写《鬼》。要不是几次同武田君到海边抛掷供物,我也不会写出像《鬼》这样的小说来。《神》是我初到横滨时写的,《鬼》写于我准备离开横滨去东京的时候,因此我把堀口君老实地写作“商业学样的教员”,就是说我不怕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疑心我在写他了。
《鬼》不过是《神》的补充,写的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在两篇小说中我充分地利用了我在横滨三个月的生活经验,这是一般人很难体验到的,譬如把供物抛到海里去,向路边“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行礼吧,我只有亲眼看见,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我说:“在堀口君的眼里看来,这家里大概还是鬼比人多吧。”有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