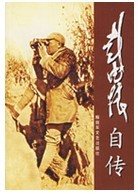巴金自传-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颓中的大家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的一本书写出来对于一般年轻的读者也许有点用处。但是多忙的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写它,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我三年前就预告了要写一部《群》,直到今天才动笔写了三页。另一本《黎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明天的事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说不定我写完了这文章就永远地搁了笔。说不定我明年又会疯狂地写它一百多万字。但我不能够再给谁一个约言。那么对于那个不知道姓名的青年读者,就让我把李佩珠介绍给她做一个朋友罢。希望她能够从李佩珠那里得到一个答复。
为了这三本小小的书,我写了两万以上的字。近年来我颇爱惜自己的笔墨,不高兴再拿文章去应酬人。许多做编辑的朋友向我要文章,都被我婉辞谢绝了。这一次我却自动地写了这么多的字,这也许是近于浪费罢。然而我在这里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话,都是在我的心里埋藏了许久的话。我很少把它们对别人倾吐过。它们就像火山里的喷火,但是我用雪把火山掩盖了。
我自己这个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在平静的表面下,我隐藏了那么强烈的火焰。别人只看见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火。那火快把我的内部烧尽了。我害怕,我怕将来有一天它会爆发。
这是我的灵魂的一隅,我以前不曾为任何人开放过,但是现在我开始慢慢地来启这门了。
那么我就率性把我两年前写的一段自剖的话引用在这里来作我这文章的收尾罢:…………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欺骗,没有宽恕的。让我再来打开我的灵魂的一隅罢。在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没有别的声音和景象来缠绕我。一切人世的荣辱毁誉都远远地消去了。那时候我就来做我自己的裁判官,严格地批判我的过去的生活。
我的确犯过许多错误了。许久以来我就过着两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挣扎,我像一个战士那样摇着旗帜呐喊前进,我诅死敌人,我攻击敌人,我像一个武器,所以有人批评我做一副机械。在夜里我却躺下来,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抚着我的创痕哀伤地哭了,我绝望,我就像一个弱者。我的心为了许多事情痛楚着,就因为我不是一副机械。
“为什么老是想着那憎恨呢?你应该在爱字上多用点力量。”一个熟识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在过去我曾被视为憎恶人类的人,我曾宣传过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种种错误的头衔加到了我的身上。为了那恨,我曾求过樊宰底的宽恕,因为他教过我爱;为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鲁泡特金,因为我使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那憎恨所带给我的苦痛确实是太多太多了。……许多人指摘过我的错误了。有人说世界是应该用爱来拯救的。又有人说可憎的只是制度不是个人。更有些人拿了种种社会科学的术语来批评我的作品。他们说我不懂历史,不懂革命。他们说这一切只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哀,他们说我不能够体验实生活。
我也曾将这些批评仔细考察过。我并且早已用事实来回答了他们:我写过十三四万字的书来表示我的社会思想,来指示革命的道路,我在许多古旧的书本里同着法俄两国人民经历过那两次大革命的艰苦的斗争,我更以一颗诚实的心去体验了那种种多变化的生活。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着我。
我是浅薄的,我是率直的,我是愚蠢的,这我都承认。然而我却是忠实的,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的,无终结的。我不掩护我的弱点,但我不放松它,我极力和它挣扎,结果就引起了一场斗争。这斗争是激烈的,为了它我往往熬尽了我的心血,而我的矛盾就从此产生了。
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这里面,它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让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始终不能够弄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缚得太紧了。……没有人能够了解我,这因为我自己就不肯让人了解……人只看见过我的笑,却没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来养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强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对象描画成一个可恨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它变成了一个极其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爱极力摧残使它变成憎恨。然而我的这种努力依旧没有大的效果。
这一切在别的人看来也许全是不必需的,他们也许会以为我是被雾迷了我的眼睛。其实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不能够免掉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我的生活的态度。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生活在这黑暗的混乱时代里面。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我固然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但我却不是像克鲁泡特金那样纯洁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亚叶夫那样意志坚强到了极点的人;我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青年。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就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痛苦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然而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了。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来的。对于这个我不能有什么抱怨。
我承认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强项的。我承认我已经犯过许多错误。但这全不是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过。那责任应该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来负担。也许我会为这些过错而受惩罚。我也决不逃避。自己种的苦果就应该自己来吃。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做了过渡时代的牺牲者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甚至在像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柏洛夫斯加亚,妃格念尔这般人中间发现和这类似的悲哀,虽然他们的成就是我万万不敢想望的。
然而不管这些错误,我依旧要活下去,我还要受苦,挣扎,以至于灭亡。那么在这新年的开始就让我借一个朋友的话来激励自己罢:“你应该把你的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里(奋斗中所受的痛苦,我这样解释悲剧),在悲剧中振发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创造。只要你不为中途所遇的灾变而覆船,则尽力为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挡一切痛苦,串演无数悲剧,这才算是一个人类的战士。”
给E.g
五年很快地就过去了。这其间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在你常常接触的那些报纸上报告过一点消息。也许你以为我已经死了。在混乱的国度里死掉一个年青人,这是很平常很容易的事情,你会这样想。不然为什么我回国以后就像石沉大海般没有一点影响呢?
E.G,我没有死,但是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我一回国就给种种奇异的环境拘囚着,我没有反抗,却让一些无益的事情来消磨我的精力和生命。于是我拿沉默来惩罚了自己。在你们的milieu里我是死了,我把自己杀死了。我想你和A.B有时候在工作的余暇也许会谈到我的死,为这事情发出一两声叹息罢。
E.G,这五年是多么苦痛的长时间呵。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是怎样把它们度过的。然而那一切终于远远地退去了,就像一场噩梦。剩下的只有十几本小说,这十几本书不知道吸吮了我的若干的血和泪。
但是这情形只有你才了解。你会知道在这五年里我贡献了怎样悲惨的牺牲,这牺牲是完全不值得的。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当我十五岁的时候你曾经把我从悬崖上的生活里唤了转来。以后在一九二七年,两个无罪的工人在波士顿被法律送上了电椅,全世界的劳动阶级的呼声被窒息了的时候,我曾经怀着那样的苦痛的,直率的心向你哀诉,向你求救,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语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你的那些美丽的信至今还是我的鼓舞的泉源,当我有机会来翻读它们的时候。E.G,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你曾经允许过我这样称呼过你),E.G,你,梦的女儿(L.P.Abbott这样称呼过你),你应该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现在人家在谈论我的教养,生活,意识了。那些人,他们不曾读懂我写的东西,他们不曾了解我的思想,他们不曾知道我的生活。他们从主观的想象中构造成了一个我,就对着这个想象的人的身上放射了明枪暗箭。虚无主义,人道主义,人家把这样的头衔加到了我的名字上面。我的小说给我招来了这许多误解。我的小说完全掩盖了我的思想,我的为人。虽然我曾经写过一本三百多页的解释我的思想的书(这书里面没有一个玄学的术语,完全是人人懂得的话句),但那些谈论我的思想断定我为某某主义者的人是不会去读的。他们根据一篇短篇小说就来断定我的思想,然后再从这里面演绎出种种奇异的结论。这几年来我就陷落在这样的泥窖里面爬不起来。
我憎恨我自己,憎恨我写的这些文章,我决定把自己来惩罚,我便用了沉默这刑罚,几年来我没有和你们通过一次信,我自己塞断了鼓舞安慰的泉源,这惩罚也使我受够苦了。
我就是这样地在痛苦中活埋了自己。
今天读着你的两厚册的自传LivingMyLife,那两本充满着生命的书把我的灵魂猛烈地震动了。你的那响彻了四十年的春雷般的吼声通过了全书来叩我的活葬墓的墓门了。
这时候沉默也失掉了它的效力。生命之火燃起来了。我要回到那活动的生活里去。我也要去历尽那生活的高峰和深渊,历尽那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悦,历尽那黑暗的绝望的热烈的希望。我要以你所教给我的态度从容地去度那生活,一直到饮尽了杯中的最后的一滴。
E.G,我现在开始来打破那沉默了。同着这封信我愿意把我的最近的这本小说集献给你,它也是我的沉默时期中的产物,它也浸透着我的血和泪。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我的最近一年的苦痛生活。而且从《在门槛上》一篇里你也可以看见你自己的面影。我因了你的介绍才读到屠格涅夫的那首伟大的散文诗,才认识亡命巴黎的那些柏洛夫斯加亚型的女性,在我的脑筋里她们的形象也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我盼望着在最近的将来我和你,和她们能够在地中海畔的巴斯罗纳见面。那时候我决不会再向你絮絮地谈我的苦痛的生活了。
………………………………………………
第五辑:南国的梦
黑土
乔治·布朗德斯在他的《俄罗斯印象记》的末尾写过这样的话:黑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悒郁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我只记得这两句,因为它们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知道一些关于黑土的事。
我在短篇小说《将军》里借着中国茶房的嘴说了一个黑土的故事:一个流落在上海的俄国人,常常带着一个小袋子到咖啡店去,“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从袋子里倒出了一些东西……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眼泪。”他有一次还对那个中国茶房说:“这是俄罗斯母亲的黑土。”
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在巴黎听见一个朋友对我讲过。他在那里一家白俄的咖啡店里看见这个可感动的情景。我以后也在一部法国影片里见到和这类似的场面。对着黑土垂泪,这不仅是普通怀乡病的表现,这里面应该含着深的悒郁和希望。
我每次想起黑土的故事,我就仿佛看见: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这幻景我后来也写在小说《将军》里面了。我不是农人,但是我也有对土地的深爱;我没有见过俄罗斯黑土,不过我也能了解对黑土垂泪的心情。沉默的,肥沃的,广阔无垠的,孕育着一切的黑的土地确实能够牵系着朴实的人的心。我可以想象那两只粗大的手一触到堆在沾染着大都市油气的桌面上的黑土,手指一定会触电似地颤动起来,那小堆的黑土应该还带着草原的芬芳罢,它们是从“俄罗斯母亲”那里来的。
不错,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的国籍如何)都从土地里出来,又要回到土地里去。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但是我想到了红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