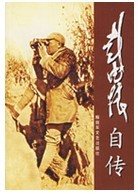巴金自传-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屋檐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底写作以后,在这一年里我又写了《复仇》,《不幸的人》,《亡命》,《爱底摧残》……等九篇。
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底朋友,都留着我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亚丽安娜》两篇是我所最爱的,它们表现着当时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亚丽安娜,这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要回到华沙去。那一天我和吴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带着含泪的微笑和她握手,说几句祝福的话语,就这样分别了她。当她底背影在一个旅馆底大门里消去的时候,我底精神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底心里充满着一种献身的渴望,但愿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那受苦的人类牺牲,为那美丽的理想尽力。我底眼里贮满着这青年女革命家底丰姿,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赛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底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我颤抖地握着吴底手诚恳地说:“吴,不要失望,我们底理想一定会胜利的。”这时候他正用着留恋的眼光看那躺卧在我们下面的巴黎,他便掉过头来回答我一个同志底紧握。他忘记了他自己和亚丽安娜一样,也是因了国际大会底事情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
以后因了驱逐令延缓了一些时候的缘故,我们还和亚丽安娜见过面,吴和她过往得很亲密。后来吴回了国。她也离了巴黎。我就再没有得过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一点她离开巴黎以后的消息,我便带着悲痛的怀念续写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甚至到现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别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感到心情的高扬。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愿把那小说献给她。
翻过来就是一九三一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差不多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去了。每天每夜热情在我底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底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它们使我底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底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的: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那张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送阳光进来的窗户,还有那张开始在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圆凳。这时候我底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纸上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底笔来申诉他们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简直变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万字的《新生》(《灭亡》底续篇)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十多个短篇。
因了这些文章我又认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迫我写出更多的小说。
………………………………………………
第四辑: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号
谈《新生》及其它
我一九二八年八月初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
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省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里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老古然和他的妻子。古然夫人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她还要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也就是古然夫妇的小客室)里坐得舒适,吃得愉快。那一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
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在那三四个星期里面,我们起得早,睡得早。早晨,天刚亮,我们三个中国人先后走到学校后院空地上,在那里散步聊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走出校门,有时走到古堡脚下,有时在街上逛逛,有时顺着河岸,走到田畔小路,有时便走上古堡,在那里喝瓶啤酒……我们回到学校以后,便回各人的房间,看书写信。晚饭后我们又到河边田畔,散步闲谈,常常谈到夜幕落下,星星出现的时候。路上我们又会遇到一些熟人,互相道一声“晚安”。我们走到校门,古然夫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听到她那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
那位好心的贫苦老太太,她今天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我写到她的姓名,还像听见她的声音,见到她的面颜,虽然有些模糊了,但是“麦歇李”这两个字(两个法国字)和满是皱纹的十分和善的瘦脸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里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桥头一家花店和正街上一家书店是我们一年来常去的地方。我和那位安徽朋友过一些时候便要去买一束花,或者买几本书。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我们也要到花店买花束送礼。校长姓“赖威格”,他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叫“玛丽—波尔”。我后来在短篇《老年》里借用过校长的姓,还把“玛丽—波尔”这个名字写进了另一个短篇《洛贝尔先生》。书店里有些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花店里有一个十七岁的金头发、苹果脸的姑娘,名叫曼丽,是我们的熟人。我们走过花店门前或者在路上遇见她,她总要含笑地轻轻招呼一声:“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
在巴黎,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止一次地遭受人们的白眼。可是在这个小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把我们看作远方来的亲戚。我为了那一个时期的安静而愉快的生活,至今还感激、怀念那些姓名不曾上过报章的小人物。在那种友好的气氛中,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又在正街格南书店里先后买到十本硬纸面的练习簿,用整整五本的篇幅抄录了它。《灭亡》的原稿早已毁掉,可是那样的练习簿我手边仍有两册,我偶尔翻出来,它们仿佛还在向我叙述法国小城生活的往事。
我在沙多—吉里最后两三星期安静的日子里,看了好些小说,我在这里不用“读”,却照我们的老习惯用个“看”字,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匆匆地翻看,并非逐字细读。此外我和那两个中国朋友在一起聊天,虽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个山西朋友在法国住得久,看过不少的戏,他还向我们介绍那些戏的内容。有一次他谈起根据左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酒馆》,他讲到柔尔瓦丝的丈夫,那个盖屋顶的锌板匠,听见女儿在人行道上叫“爸爸”,失脚从屋顶上摔下地来,他讲得有声有色:幕怎样轻轻地落下,报告灾祸的音乐还在观众的心上回响……好像那个惨剧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以前读过两三本左拉的小说,这时又让朋友的谈话引起了兴趣。下一天我就到格南书店去买了《酒馆》。我在饭厅楼上我那个房间里看完了它。我接着还看过左拉的另外两部作品《萌芽》和《工作》(那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柔尔瓦丝的两个私生子)。因此我一连几天向朋友介绍左拉的连续性的故事。安徽朋友不久以前才读过我的小说稿本,便带笑问我,是不是也想写有连续性的小说。他也许是开玩笑,然而这对我却是一个启发。这以后我就起了写《新生》的念头。故事倒还不曾认真考虑,书名却早想好了。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那么《灭亡》之后接着出现的当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里想来想去也不出以上的范围。
《新生》里应当有些什么人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静淑,我在《灭亡》的最后就预告过她的行动了。
后来我从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又看了好几本左拉的小说,都是收在《卢贡一马加尔家庭》这套书里面、讲两家子女的故事的。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多读了几本小说,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也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小说了。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照我当时的想法,杜大心的父亲便是觉新一类的人,他带着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内喊“痛”,别人都不许他进去。
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徘徊;他的妻子并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丢下爱妻和两个儿子离开了人世。
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马赛,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我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十二天。马赛的生活我已经老老实实地写在短篇《马赛的夜》里面了。连海滨的旅馆和关了门的中国饭馆也是真实的。我在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吃饭,在风景优美的“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读其实是“看”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整套书中的二十部长篇我先后读过了一半以上,在马赛我读完了它们。我不相信左拉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可是他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仅一本接一本热心地读着那些小说,它们还常常引起我的“创作的欲望”。在等待轮船的期间,我只能写一些细节或片段,因为我每天必须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听消息,海员罢工的问题一旦解决,我就得买票上船。否则我会在马赛老等。然而我的思想并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写得少,却想得多。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虽然我看到海的各样颜色,听见海的各种声音,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