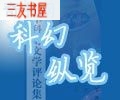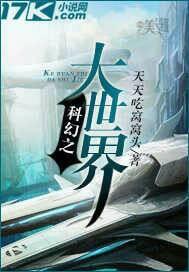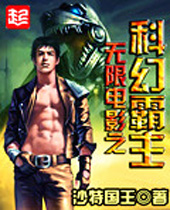科幻纵览-第1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你为什么还那么胖?”
“……”
老板没有挖苦我的意思,只是心直口快。我只好告诉他,或许是因为生来骨架宽大,再加上肠胃好,吃点什么都长肉的缘故。后来,大概正是我的身材配合了我的支支吾吾,挡回了许多到会者对我生存状况的好奇。
每天晚上,附近会出现一些小吃摊。虽然会议安排的宴会和一日三餐中不乏大鱼大肉,但金华这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食品,倒是这些小吃摊上的冷饮。说是冷饮,但完全不是大工厂里出来的机械产品,而是一些自家熬制的小吃,有米仁汤、红枣汤、清凉糕、凉粉等十余种。熬好之后放在冰柜里,出售时再加些冰块端到顾客面前,一勺入口,清凉甜润的感觉就会渗入全身各处,抵挡住闷热的暑气。每天晚上我都会来到这些小食摊前,要上一到两种冷饮细细品味和休息。四天下来竟成了习惯,以至于回到天津的当晚,还禁不住想到外面看看有没有银耳汤卖。
不过,尽管我已经在家门口与许多金华人打过交道,但我对金华的地理仍然一无所知。
直到第二天我买到一张金华市地图,才发现,望江饭店确实是在一条大江边上。晚上,我走过其实只有一个街口远的距离,来到被称为金华外滩的金华江边,在清爽的风中欣赏夜景。金华江虽然比不上黄浦江,但天津的海河与之相比,只算是一条小水沟。金华附近也有一些高峻的大山,但直到我离开的那天,它们才把真面目从浓雾中透出来。
(二)
在这次会上,我平生头一次与文学界的名家大腕们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他们和我以前的想象既吻合又不同:冯骥才象我想象得那么高,但比我想象得白晰;陈忠实脸上的皱纹象我想象得那么多,但身材没有我想象的魁梧;和航鹰第一次朝面,我就感觉出她是谁,但她一开口,那响亮的嗓音和独特的天津味普通话还是让我很吃惊。
开幕式那天,下起了绵绵细雨。人们在雨雾中走进浙江师范大会的会议厅。北方来的客人自然感慨南方的雨水之多。当地的主人则更正说,这里往年雨水确实是多,但今年这还是第一场雨。浙江师大人文学院的头牌学者金汉老先生在开幕式上说,这样的天气正适合呆在屋子里作学问。结果,四天的会议就一直是在时停时起的雨中度过的。
第一天上午是开幕式,来自各方各面的领导在台上讲话。开幕式上听到的惟一学术性的讲话,出自冯骥才之口。他讲的内容是现代化传媒的发展控制了文学创作和评论,大家都成为传媒制造新潮的工具。不光是文学作品,就是文学批评也逐渐走向市场。身为民进中央常委和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的话有许多高层次、大背景下的经验作论据。
在下面,我开始散发我带来的小册子。我很快结识了一位老年朋友,文艺报的彭华生老师。彭老师对科幻文学的重要价值完全理解,但不知道中国有哪些科幻作者,写了些什么样的作品。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从不少人那里听到彭老师这样的话。
开幕式后,浙江师大的校车载着与会代表在金华市里转来兜去。一位漂亮的组委会女教师充任导游,很自豪地介绍着她的学校和她的家乡。我则和身边的一位上海来的博士研究生聊了起来。这位四十来岁,叫裴毅然的老哥很有些江湖豪气,听到我介绍自己的情况,就热心地把上海出版中心的一位编辑介绍给我。第二天,裴毅然发现我和这位编辑没有深谈,埋怨我没有抓住机会推销自己。在一群斯文学者中间,他那风风火火的“另类”样子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那一天我赠送了若干本出去。一位老师把拿到手的小册子又递到我面前,让我写点什么。我以为是要我留下地址,忙说封三上印着有。他说不是要地址,希望我能写些什么赠言之类的文字。我写什么呢?这些位老师的“笔龄”大于我的年龄,什么样的精妙修辞在他们眼里恐怕都不值一晒。于是,我只好写了句“敬请某某老师指点”。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成了我写在小册子上的套话。
当天下午,大会发言开始。头一次参加这样高级的学术会议,我自然很是新奇。更重要的是,中国小说协会的秘书长汤吉夫先生告诉我,第二天上午要给我安排十分钟时间,让我介绍一下科幻文学。所以,了解什么人上台讲,讲的什么,以及怎样才算得体的发言,对我来说就更为重要。
不过,刚听了两位先生的大会发言,汤吉夫老师又走过来告诉我,他安排了上海文汇报的记者采访我。自从认识汤吉夫老师以来,我与他直接打交道的时间,连打电话都算在内,恐怕也不超过一个小时。但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关注和对年轻作者的关心,汤老师给了我许多实质性的支持。这次会议完全是他把我带到会场上来的。我赶快来到饭店的大堂里。那位名叫李鹏飞的记者正等在那里,一旁还坐着一位浙江师大校报的学生记者。李鹏飞是我的同龄人。采访机打开后,我们很快切入正题。他向我了解科幻界的现状,特别是国内有哪些人在创作科幻小说。我告诉他,把一些充数的少儿文学或科普作品排除掉,国内能创作真正的科幻小说的人很少。其中有质有量,半职业化写作的不超过十个人;有质无量,业余写作的大概能到一百;建国以来至少发表过一篇科幻小说的,或许有一千个人吧。说实话,就是这个十、百、千的判断也是我壮了壮胆子才说的。然后,他拿着我编写的那个小册子,让我在《中国科幻艺术一百人物传》一文中把这十个人找出来。我根据自己的了解为他一一划了圈。
李鹏飞走了以后,那位估计上大二的学生记者继续问我一些关于科幻的问题。他不是有备而来,只是正好坐在那里。不过,和大学生谈科幻是这几年我的家常便饭。相比之下更自然一些。最后他问我,如果会议中有时间,能不能给师大的同学们作个关于科幻文学的报告。我欣然应允,这是我的老本行呀,随叫随讲!可惜时间太苍促,直到我走的时候,这场临时讲座也没有安排好。
晚上,汤老师又告诉我,原定第二天我的讲话取消了。他不无歉然地说,你多找找记者们,跟他们接触一下也是有帮助的。我连说没关系。到会前我并没有奢望能得到一个发言时间,主要是想通过这个会,结识一批主流文学工作者。印小册子就是为了能在私下里让个别人呼我的“书面发言”。
第二天上午继续大会发言。这次大约有近十位代表谈了自己的观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每当主持人念到请某位教授、博导上台时,走上去的往往是三十左右的兄长。便是几位师范院校的校长,也没有超过五十岁的。每个人都有一头不用染起的黑发。十年前我读大学时,教我们的还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们。看到文革后的一代人已经全面接班了。
不过,姜还是老和辣。上午发言者中最有意思的,还是河北作协主席,老作家陈冲。听陈冲的发言,就象是听马三立的相声,充满了机智的冷幽默。陈老先生发言中有一段话,使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主流文学不关注通俗文学,所以通俗文学大多由一些爱好者自己来创作。爱好者的文字功底差,作品粗糙,主流文学人士看了后,更觉得通俗文学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水平,对通俗文学更不重视,如此恶性循环。其实通俗文学并非不可以达到很高的文学水平。我觉得,把这段话中的通俗文学代换成科幻文学,正好可以表达科幻文学的生存环境。
我继续着广交朋友的预定任务。一位来自锦州师院的老师在听大会发言时坐在我身边,聊天中他问我,老舍的《猫城记》算不算科幻小说?我说当然算了,或者可以反过来说,科幻小说就是类似《猫城记》这样的作品。中午吃饭的时候,两位唐山师院的老师告诉我,他们那里有一位老师专门研究“大幻想文学”,还准备就此开一门选修课。他们问我“大幻想文学”
和“科幻文学”是什么关系。这个词我以前听说过,是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制造并炒作的一个概念。正是上届年会上,这家出版社的社长还亲自参加,并询问过与会代表有没有科幻小说作品。
当天晚上,我得到了大会组委会印制的通讯录,发现天津来了两位“津源影视中心”的制片人。这也是本届年会中惟一来自影视界的人。两天来,不止一个大会发言或小会讨论的人感慨电视夺去了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力。不知道他们听这样的论点时有何种心情。我敲开他们的房门,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十分钟后我得到了极为重要的一条消息:天津电视台准备搞一个科幻电视剧,正在作论证!
当天晚上是分组讨论。我刚走进饭店大门,一群浙江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就围了上来。头一天他们就坐在会议厅的后排听大会发言,我还把一些小册子送给他们。于是,我们坐在大堂的休息区随便聊了起来。除了讲科幻文学以外,我还向他们谈了我对主流文学的一些总体看法,如文学的真正职业化和世俗化,文学创作动机中的现世主义和来世主义等。后来,这群学生分成三组,分别旁听三个分组讨论。在我这组里,面对着名家大腕们,几个中文系的学生很自信也很认真地谈着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们的发言是我在小组讨论中听到的最有价值的发言。
望着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刚刚从大学校门走出来不到十年的我觉得自己确实有些老了。
那天晚上,汤老师给了我一个确切的消息,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时,肯定会安排给我十分钟时间。于是,我赶快回到蒸笼一样的小旅馆,把笔记本垫在厚厚的教材上,伏在床板上用一个小时写下了发言稿。我离开知识分子群落已经十年了,今天中国文化界最流行什么“话语环境”、“符码系统”我全无不知,所以只能让八十年代的陈词旧调充满我的发言稿。然后,即将进行的大会发言便一直纠缠着我,使我到凌晨才昏昏睡去。
(三)
转天早上,密集的雨点把我挡在旅馆里。于是我又反复修改和准备讲话稿。中午时分,我趁着雨稍微小一些的时候,跑到旁边的商场里买了把伞。然后,拎着全部剩下的手册走向望江饭店。中午饭后,我又呆在大堂里,一遍遍地看着讲稿。资料手册的印费、会费、旅费加上其它钱,我一共花了一千五百块,用一千五百块买下的十分钟发言机会,如何能不珍惜。
这是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几天来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的代表们都有些倦了。一位记者后来告诉我,以前的年会她也来采访,都是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对我这个门外汉来说,仍然是新鲜的。前两天的大会发言我都作了记录。不过,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我只能用一半精神去听了。
我的发言被排在倒数第二个,这实际上是相当好的时间。如果大会组委会事先询问我想什么时候发言,我一定会要求排在倒数第一个。心理学上有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概念,意思是说,在一大堆同类事物中,最初的或最后的都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排在中间的才倒霉。
连日来我在下面搞的“小动作”已经使不少人产生了兴趣,于是,当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便迎着人们期待的目光走上台去,进行了肯定超过十分钟的发言。最后的掌声告诉我,大家对我的超时没什么反感。
我正准备走下台去,主持大会的陈公重老师叫住了我。作为会议主持,陈老师的任务就是把一块手表放在讲台上,随时提醒每一位发言人注意时间。三天近二十人的大会发言中,我是惟一被叫回去作补充的。不过,补充的这个问题,恰恰是我最尴尬的:你作自由撰稿人,是怎样种生存方式?连日来,许多人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了,而且往往是直截了当地打听,你的稿费收入能不能养家糊口?他们抱着很大的兴趣,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基本上都是有铁饭碗的人。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都只好搪塞过去。要说在中国大陆作自由撰稿人,王朔是“龙头老大”,他最有资格讲这个问题。大会期间我也经常听人提到一些百万元级作家的名字。就是在国内同龄的科幻作者中,也有比我更成功的自由撰稿人。听到陈老师的要求,我只好对大家说,我的与文学有关的经历都印在小册子的封三上,就不多说了。后来我想,下次年会,与科幻有关的发言最好由能到会的科幻作者们去作,我自己则专门谈一谈作自由撰稿人的体会。
下台之后,我回到座位,准备拎着装满小册子的旅行包去会议厅门口找个位置,以便在散会后代表们走出去的时候把手册塞到他们手里。但我还没等起身,已经被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