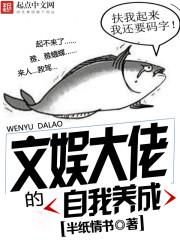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么我没有被捕,尤其是当拘捕是很草率、没有充分的根据的时候?我一直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当人们夸大我的知名度和我的意义的时候,我很不喜欢,那种自大感觉与我格格不入。 但是,我在欧洲和身国,特别是在德国的大的知名度是原因之一。 在没有重要理由的情况下拘捕我被认为是不利的。 我开玩笑地说,这表现了德国人对哲学的尊重。 后来我又说,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高层中有人自认为是我(作为哲学家)的敬仰者,他不准许拘捕我。 在这些可怕的年代里,我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积极性。 我呆在自己的家里,偶尔到巴黎去,在被认作危险地方的巴黎咖啡馆里
366
253自我认识
我一般是不回忆过去的。 在20年中我可能到咖啡馆去过三次。 按自己的特点来说,我仿佛是个封建主,住在自己的有升降桥的城堡里。 对发起任何事情,尽管与德国人的联系很松,我一概拒绝参与。 因此,我不能作报告和演讲,我用这些时间集中精力于写作,进行哲学创造。 但是在我家里星期天还是集中了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俄国人,有时甚至作报告。我们的家是爱国主义感情的中心之一。也常有法国人参加。在被占领的年代,有意思的集会是在莫列举行的主要讨论神秘主义和精神问题的集会。 我作了两次报告:关于弥赛亚说和关于尼采的宗教悲剧。 除了在莫列家里的集会外,还有在达维小姐那里举行的集会,她是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女人,我们的新朋友。 这是致力于精神探索的学习班,在那里我就以下题目作了一些演讲:“弥赛亚思想和历史问题”。这主要是左派天主教徒的学习班,但是有新教徒、东正教徒和自由的探索者参加。达维还在巴黎的富丽堂皇的庄园里举行集会,第一次集会只是讨论我在法国出版的书《精神与现实》。
在这次会上我与某些天主教徒,特别是马赛尔(他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存在着思想冲突。在这些年里我认识了罗曼。 罗兰,他有一个俄国妻子。 在罗曼。 罗兰身上我感到道义上的个性的重要意义。 他对苏俄和对俄国共产主义的好感并不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好感。 相反,他是唯灵论派。 他带着很大的好感读我的书《精神与现实》,并且对于我的书中论佩吉部分写了很好的评论,他在我关于客体化的思想中发现了与佩吉的某些同源关系,尽管他只部分地相信这种思想。
367
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353
G这些年代是艰难的与痛苦的,这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 这是内在的精神斗争、矛盾、怀疑探询的时代。 我已经说过,按自己的素质说,我完全不是怀疑论者,对我而言,体验怀疑完全是特殊情况,而且怀疑具有道义上的而不是知识性的性质。 我不想在我这里出现简单地否定上帝存在的时刻,但是存在这样的时刻,那时我排斥上帝;存在那样的痛苦的时刻,那时在头脑中出现的上帝可能是恶的,而不是善的,是比我、比罪孽深重的人还要恶的。 这些沉重的思想含有正统的神学理论、关于赎罪的审判学说、关于地狱的学说和很多其他的学说。 我在非创造性的自由的思想中找到了结论,但是并不想承认它。 永恒的宗教问题以完全新而又新的方式对我提了出来,我经历了与全部官方的正统学说相冲突的时刻,不过,这对我并不是新的事情,有时,我感到,比起那在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来说,我更信奉其他的宗教。然而,如果对的不是我,那么我在反对谁?当我自己说,这意味着上帝是恶的,是没有人性的,他在永恒中想要的是恶、苦难和地狱。 上帝的预见同样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过,要知道,我反对上帝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是以对上帝更高的理解的名义进行的。 这是一种安慰。 不过,我是完全经历了被上帝遗弃的状态、不幸状态,被上帝遗弃的体验并不意味着否定上帝的存在,它甚至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上帝交往的存在主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是痛苦的因素。不仅是个别的人,而且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人类和所有的生物
368
453自我认识
都体验到被上帝的遗弃。 这种神秘现象完全不能用构成人的生活一般事实的罪孽来解释。 体验到的被上帝遗弃完全可能并不比体验不到和认识不了上帝的遗弃更不好。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精神内部斗争的时期完全没有触动我的基本的宗教——哲学观点,有时它们只是更加尖锐化。 在这里我无能地说,存在着某种深深的神秘的东西,难以表述的东西。 在这个血腥的轰炸、杀人、集中营、拘捕、无数人的苦难的时代,我一直不断地思索恶的问题、苦难问题、地狱问题、永恒问题。 我的思索常常是矛盾的,在我所写的东西中已经对自己的内在斗争作出了结论,但是可能并没有指出最内在的斗争。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这些纳入我最后的著作《上帝的和人的辩证法》的实质性部分中。在1942年秋季,我作了一次大手术,在医院躺了四个星期,我没有想死着出去的可能性,我也没感到害怕,看护我的女护士、我的朋友T。C。 伦佩尔特都看到了。但我有一种很剧烈的感受。麻醉药是不充足的,只有下半身进行麻醉。 意识则是充足的,我完全能看清楚,没有感到任何的痛苦。 但是,我消失了任何运动的可能:身体陷入了完全被动状态。 我遇到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屏障,后来还有其他的束缚。我很难忍受完全被动状态。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权力更可怕的了。 它威胁着我的生命。 只是在某一时刻意识能敏锐起来,这表明我们是自由的实体。 悲剧也正在于必然性的权力凌驾于自由的实体之上。 巴黎刚刚解放时,在生活中出现了使我最为痛苦的事件,我们的朋友穆利在折磨人的疾病之后去世了。 我像忍受所有有生命者的苦难一样地忍受穆利在死亡面前的痛苦,通
369
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553
过它,我感到自己和所有等待挽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在逝世的前一天,穆利病得已经非常沉重,但仍挣扎着到莉季娅的房间工作,忽然他走到莉季娅床前,低声地述说着什么。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我很少也很难落泪。 但穆利去世时我大声地哭泣,作为一个上帝的神妙的造物,他的死使我体验了一次一般的死亡,谁都喜欢的死亡。 我请求给予穆利以永恒的生命,我需要与穆利一起永恒生活。 我很长时间不能谈论他,我所有时间都感到他在我眼前跳动。 现在已经没有朗读人莉季娅,没有穆利,只剩下我和若妮,只有她慰藉我的生活。与穆利的死相联系,我非常具体地体验了不死的问题。在我们花园的树下,有穆利的坟墓。 在他的墓前,我想到不死的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反对无个性的不死的思想,在那种思想里,所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人的内容都消失不见了。 这个问题是我体验最深刻和意义最重大的,它与我的生活中最不幸的和最重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点前面已经说过。
G G G外面的新生活开始于巴黎的解放,这还不是战争的结束,但是战争的顺利结束可能已经有把握了。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法国人进行的报复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很多俄国人被捕,根据是与德国人拘捕他们相反的理由。 逮捕有时有根据,有时则什么根据也没有。 气氛依然是很沉重的,在被占领的年代里,一部分俄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是令人厌恶的看风使舵,这种行为从性质上说属于背叛。 现在,又开始反方向地随波逐
370
653自我认识
流,对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和不好地理解的共产主义献媚,向苏联大使馆献媚。 一时这成了时尚。 只有很少的人是有尊严的和自由的。 我一直被认作具有“苏维埃的”倾向,尽管我一直大力批判并且不断批判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鼓吹自由。 我对苏俄的态度没有任何新的变化,我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俄罗斯民族的政权,任何其他的“政权”都不能而只有它能在国际关系中代表俄国。 实际上,任何政权我都不喜欢,都不可能喜欢。 任何时候我都不喜欢伟大的政权世界。 能激起我同情的只有无政府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定国家的功能在人民生活中的必然性。对于俄国侨民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引起了很大的矛盾。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对俄罗斯人民、对苏联人民的态度问题,对作为俄罗斯民族命运中的内在因素的革命的态度问题。 应当把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个人的命运来体验。在坚持任何抽象的自由——民主原则的高度时,我不能站在自己民族的命运之外。 这并不意味着要使我的思想和行为与苏联大使馆管理处相一致,经常环顾它来进行思考与写作。 当爱国者联盟——起初是爱俄国,后来是爱苏联——宣称无保留地接受苏维埃政权和苏俄制度时,使我很愤怒。人不应当对任何政权都无保留地接受,这是奴才状态。人不应当在任何力量面前垂首,这不配作一个自由的实体。 在1944年11月由作家联盟邀请,在俄国爱国者联盟的处所我作了题为“俄国的和德国的思想”的报告,报告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是我所有的报告中最好的。 这与爱国的高潮正相符合。 后来我在《俄罗斯爱国者》(青年作家团体加入其中)上
371
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753
发表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变换》的文章,它使某些俄国侨民感到难堪。 与我接近的朋友的圈子有了大的改变。 在我的住所里开始经常出现青年(相对年轻的)的作家,我对他们很有好感,这些人过去并没有来过,过去来的一些年轻的俄国人接受了苏维埃专制制度。 我和神学研究所团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宗教的和政治的分歧。 我和苏联大使馆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我感不到有什么这样的需要。但是,有些从苏联大使馆来的苏联人到我这里来,我以很大的兴趣向他们打听俄国的事情。 我与一些年轻的苏联外交官的会见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最令人愉快的是和一位苏联作家的会面,这位作家经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招人喜欢和很有才干的人。俄国给了他很强烈的印象,俄国对他来说就是宗教。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他格格不入。 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 当他告诉我所有的俄国人民不仅阅读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而且具有对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真正崇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还有痛苦的感觉。 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亚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论著被译成很多种语言,很多人写了论述我的文章,只有一个国家几乎不知道我——这就是我的祖国。这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断的标志之一。 在经历了革命之后又回归俄罗斯文学,这个事实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但是,也还不可能复兴俄罗斯文学,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阻碍着这一切。 哲学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没有自由思想。 可能准许我回到俄国,但是在那里我能干什么呢?回归祖国问题对我是十分痛苦的。 正是哲学家回到俄国没有意义。 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 而我是常常想念俄国的。 关于俄国
372
853自我认识
文化的悲剧,关于俄国的断裂,我想的很多,这些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存在某种痛苦的东西。 这种苦难只有到最后才能铲除。 在最后的时刻,俄罗斯的问题将把我折磨死,我处于诸多失望之中。
G在1945年行将结束的现在,我的知名度又有很大的增长,对我的评价比早先要高得多,我经常听见说,我有“世界的名声”。
经常有外国人来拜访我,我收到难以计数的信件。大规模的通信成了我的不幸,因为我不爱写信也不会写信。有时我陷入必须回答的大量书信的绝望之中。令我惊奇的是,我成了很受人敬重、受人景仰的人,这却意味着我几乎已经是生活的导师,智慧的指导者。这完全不适合我的自我感觉,我想使我的自传的读者相信,我完全不是受敬重和有威望的人,完全不是生活的导师,而只是真理和正义的追寻者,造反者,存在主义哲学家,应在这个意义下来了解我的哲学的集中的存在主义性,但我不是导师,不是教育家,不是指导者。 我的不断增长的知名度很少给我以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一般地我很少相信这个。我很少有虚荣心。我有很强的忧郁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