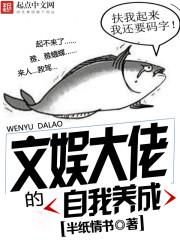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或者读历史的和惊险的小说。 我对小说的评价是与小说的作者迫使我越出自己的世界,达到周围现实以外的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我一直非常期待体验我所读的小说中英雄人物的生活。 我喜欢电影,因为它创造了幻想,引导我离开现实,但是我也伤心,因为那么快地忘记了很好的影片。我特别喜欢重读19世纪的俄国文学,我多次重新评价我对文学的关系,不过,我一直不变地喜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始终给它很高的评价。 但是,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在重读时也使我失望,因为它很少具有永恒性,而是过于和时间、年代联系在一起。 我也同样喜爱西方的作家,现在我比以前更加喜欢狄更斯;我对易卜生的爱也一直不变,我带
358
43自我认识
着喜悦与激动重读他的书,永远有新的教益。 我一直准备重读古希腊的悲剧、莎士比亚、歌德,虽然没能完全作到。 不过,我不特别喜爱但丁。 我对布鲁斯特评价很高,重读他的著作的同时还重读卡夫卡的著作和米勒作品的某些地方。 我读了许多的历史著作,特别是很多历史活动家的传记。 这对于我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它是我的末日论思维的营养物。 我已经说过音乐对于我的意义,它仿佛是作为我自身的抒情风格不足的补充。 但是,我想,我并不缺乏抒情风格,不过它是忧郁的,并且是替代性的,用以掩盖我的枯燥。如果问我,由于什么我不是在特殊的瞬间而是在生活的全部时间都感到痛苦,为什么一直强制自己进行斗争,那么我的回答是:由于我的洁癖,精神的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无所不包的洁癖。 有时,我痛苦地说到自己一般地具有对生活和世界的洁癖,这是很沉重的,我与之进行斗争。 我最多地用创造的思想与之斗争,用学说、写作与之斗争,用禁欲生活与之斗争,用远离自然的美的直观与之斗争,用怜悯心与之斗争。 当洁癖重又附体时,我因它而颤抖。 我经常将眼耳鼻闭住,因为世界对我充满了气味。 我那么激情地喜爱精神,因为它不会引起我的厌恶感,我喜欢的不仅是精神,而且还有香水。 我的洁癖,准确地说,原因之一是我是个形而上学家。对我很重要的是,我一直很喜欢笑和可笑的事情,在笑声中我看到了超越日常权力的解放的开端,喜欢俏皮,这可能是我身上的法国人特点。
359
关于自我认识及其界限。 自我鉴定543
G我还想解释周围的人们在我这里发现的矛盾和他们没有发觉的矛盾。这对了解有关人的一般本质的矛盾是有意义的。人的本质是矛盾的,现代的心理学,特别是心理病理学明白这个。 例如,在我这里,精神的革命性和“习惯”的巨大作用交织在一起,无政府主义(按感觉和观念来说)和喜好规定自己生活中的秩序交织在一起:我想,这些矛盾的属性有另外的根源。 习惯对我的意义有两方面的根据。 举凡与日常生活规章有关的,与物质世界有关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异常困难,我非常不善干在其中生活,害怕花很多的力量于生活的这些方面。 因此,我经常努力使外在生活的指导上自动化,力图在最大的不适应情况下使用最小的力。 这是通过习惯的道路实现的,习惯使我避免使用更多的力。 我要在思维与创造上耗费很多的力量,还要用很少的力量于其他的事情。我力图通过习惯的道路走出困境,这样就创造出幻想,仿佛从物质世界中得到了解放,而实际上解放只能来源于对物质世界力量的克服。 不过,习惯在我的生活中的作用还有形而上学的根据,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其现在状态中对我的痛苦的异己性。 习惯是同世界的异己性进行斗争的形式之一。 我指的是习惯,是我所建立的,而不是硬塞给我的。 我企图在我周围建立习惯的世界,以减弱世界的异己性。因此我很喜欢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书籍。所有的对立,不仅是和人的对立,而且是和地方和事物的对立,都在加剧面临的异己性苦闷。 异己性引起的不是害怕,而是
360
643自我认识
苦闷。 在死亡中,在杀人行为中,在仇恨中存在着异己性的极限。 恶可能是人所特别固有的,但是在恶中有异己性。 战胜了对恶的恐惧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战胜了与他异己的力量的人,这种异己力量就进入他的深处并成为他的本性。 恶是人的自我异化,全部宗教都努力克服异己性。 世界并不最终与人异己,这仅仅是因为上帝的存在,没有上帝,世界对我来说就成了完全异己的。 习惯可能是在日常外部生活的背景中和异己性的斗争,在黄昏中,我被异己性的苦闷所笼罩,但是如果在黄昏时刻我习惯地作某些确定的事情,使自己的生活有节奏,那么异己性的苦闷就减弱了。 我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想完全打翻这个异己的世界,客观性、客体性和异己性对我是同一件事。 但是,这种情绪是和对亲人的深切眷恋,对他们的担心和关心(有时常常是荒唐的)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种眷恋中,异己性占了上风。 当异己的世界将要瓦解时,这种联系应当保留着。当思考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时,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一直害怕生活。 在这里我与易卜生一脉相联。 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有根据认为自己是勇敢的人,我并不怯懦。 但是,我害怕顺从生活之流,这是因为看到了在生活之流和我的创造之间的冲突。 有时生活之流冲来了,但后来创造的思维战胜了。 我任何时候也没有掌握生活的艺术,我的生活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我任何时候也不表演自己的生活。
G我想给对我的生活十分重要的思想作出结论。 这正是我
361
关于自我认识及其界限。 自我鉴定743
的精神道路所实现的成就。 我最终克服了与历史的伟大、王国的光荣、强力意志有关的东西对我的诱惑。 在这种诱惑中我永远不能成为完全的自我。 我努力将自己对人的创造的崇尚从这种因素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导向其他方向。 我哲学地思考这种问题。只有思考了它,我才能完全表现自己的哲学。历史的伟大与威力之路是客体化道路,将人抛于外面的道路和自我奴役的道路。 这条道路将引导走向反基督的王国,同时也就是反人的王国。 人的真正的创造应当冲破客体化的奴役王国,结束宿命的道路,成为自由的、改造世界的道路,通向存在主义的主体性和精神性,也就是真实性的道路,通向人性王国的道路。 我认为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意义正在于这种预感,这种摆在人的面前的两条道路的意识。 这两条道路就是:客体化的、外倾化的、被虚幻的威力与强大所束缚的道路;趋向改造世界与解放世界的、趋向上帝的世界的道路。 我不想把谁打发到地狱里去,这对我十分重要。 不仅创造的思想,而且创造的激情,酷烈的意志和激动的感觉应当溶化僵硬了的意识,并且溶化呈现于这种意识面前的客观世界。 在生活中我坚持除了对上帝的真理的探索以外,不依赖别的。 我的主要成就在于,我把自己生命的事业奠基于自由之上。我不应当被当作信教的人的典范,我感到,我很少使用那种表述,如“他转向”
“他成了信徒”或者“他的信仰动摇了”
“他丧失了信仰”。对我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正统的“或者——或者”
,我不可能是正统的怀疑主义者。 怀疑主义在我这里完全是另一定规定,是更加深层次的规定,这种规
362
843自我认识
定不能改变——不知道在我的书里我能否提供这种感觉。 我用全部生命寻找真理,我从一开始就寻找它。 真理在我的精神道路之前就存在着(a
priori)。
存在着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不像世界,也不像存在于世界之中所有的东西。 它应当揭示出来,并呈现人形。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大约要回忆起我的许许多多的罪过、弱点和堕落,但是我将可能幸福地回忆起:我属于“渴望真理的人”。这是与我有关的无上幸福的诫律中唯一的一条。需要补充一点,我面向的不是明天的日子,而是未来的世纪,理解我的思想的前提是改变意识的结构。 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完全不是学者的年轻人中,但不存在于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之中。
363
第十三章沉重的年代(1940—1946年的补充)
我的自传中断了,它需要补充,这种补充有很大的意义。在这些沉重的年代里(1940—1946)发生了很多意义重大的外部和内部的事件。 由于经历了痛苦状态而使我的很多感受深化了,我最深的怀疑体验是宗教深处的产物。 这样的领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事件,从一开始,它的起源就是不清楚的和黑暗的。 这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是十分巨大的震动。 我一直等待着新而又新的灾难,不相信世界的未来。 我们进入残酷——灾祸时代的所有事情,我都不感到意外。 警笛和轰炸的时代开始了,对轰炸我是冷漠的,没有体验到任何的可怕。 夜里,当听到非常近的轰炸声时,我转到另一个方向并堵上耳朵。 我并不走下地窖。当天空很晴朗时,我观看空战的壮美景色。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人进入法国之前的事。 以后又面临着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德国包围法国和德国对俄罗斯的战争。 这不仅是外在的事件,而且是对精神生活有着影响的内在经验。
364
053自我认识
1940年6月我们离开巴黎,来到阿尔卡雄的皮瓦,和我们一起走的有穆利,我们不想在德国人的统治下生活,但这是幻想。 我们到达皮瓦后又过了一些日子,比在巴黎更多的德国军队出现在皮瓦。 皮瓦是个美妙的地方,那里把松树林与大海结合起来,空气令人陶醉,对人十分有益。 然而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被占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 我们丝毫没有受到强制,而是完全平静地在森林中不大的别墅过了3个月。 在阿尔卡雄生活着一些俄国的朋友。 当时美国更加紧地邀请我,我拒绝到美国去。 但是,我不能平静地看到德国军服,它使我发抖。 当时,反俄战争还没有进行。我用全部时间写我的哲学自传。当我于10月初回到家中的时候,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地位不是安全的,我写过反对希特勒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他们知道我是思想上的反对者。 开始了对俄国人的拘捕,在俄国人的圈子里有些难以相处的人是希特勒和德国人的拥护者。 当反俄战争开始时,情况更加紧张起来。 德国人侵入俄罗斯土地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的俄罗斯遭到死亡的威胁,她可能被肢解和被奴役。 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到达了高加索,在被占领的俄国部分,他们的举止如野兽一般,他们对待俄国人就如同对待劣等民族一样。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思考德国人战胜了什么。 我一直相信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对于俄罗斯受到危险的体验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感到自己与红军的成就溶在一起,我把人们区分为希望俄国胜利的和希望德国胜利的两种,我不同第二种范畴的人们交往,认为他们是变节者。 在巴黎的俄国人中有亲德分子,他们期待希特勒
365
沉重的年代(1949—1946年的补充153
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俄国。 这引起我深深的反感。 从192年被驱逐的时候起,我一直认为苏维埃的国际目标和武装干涉者的国际目标都是违法的。 我任何时候也不崇尚暴力。 但是,当暴力表现为红军保卫俄罗斯时,我认为是符合天意的。我相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 在巴黎是很艰难的,我的朋友开始受到拘捕,一些朋友由于政治的原因被驱往德国,在非常凄惨的环境中死去,盖世太保的代表一次也没有到我这里来,也没查问我的活动的性质。 某些直接反对我的指控者不能提供证据。 但在瑞士报纸上登出了我的被捕的消息。 过了一些日子出现了盖世太保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是两个人,他们要了解为什么出现关于我被捕的传闻。我用德语同他们交谈,这是为了简便。 他们告诉我,从柏林来了质问:报纸上关于拘捕如此著名的和珍贵的(在德国的)哲学家比如别尔嘉耶夫的消息,意味着什么?按盖世太保代表的话说,这引起了惊慌,当然这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说法。 但是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被捕,尤其是当拘捕是很草率、没有充分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