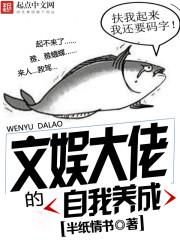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武备中学时有一次神学课考试(关于祈祷)
,我得了1分(20分制)。
神甫万万没有想到,我将是许多关于宗教哲学著作的作者。神学考试得1分,这在武备学校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丑事。对我来说,它却表现了我的特点:任何时候我也不能被动地学习某种东西,不能学习祈祷,无论怎样我也不能把祈祷和我早年对生活和永恒意义的追求联系起来。 我和东正教会的关系一直是痛苦的,一直没有严整性。 我永远保留着对真理
197
转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剧。 精神的交往381
和意义的自由探讨。 宗教的主题早就开始折磨我,我可能是比许多人更早地思索世界上一切东西的暂时性问题,思索永恒性问题。 但是我回忆不起来在童年时能够使我信赖的正统宗教观念。 实际上,我任何时候也没有产生被称作“向父的信仰的回归”那种东西。 极而言之,我一直嫌弃所有类型的宗教性。 只是在我的生活的莫斯科时期的开端,我才第一次感到古代教会和东正教祈祷的美丽,并且体验到与许多人在孩童时代的体验相类似的东西,只不过是在另一种意识状态之下。 我一直感到我与布尔加科夫之间在对待继承东正教传统问题上的巨大差别。布尔加科夫来自东正教传统的家庭,他的先人是神甫,我则来自俄国贵族家庭,这个家庭渗透着启蒙的——伏尔泰主义的、自由思维的思想。 这种情况创造了甚至是在相同的宗教思想下的信仰上帝的不同精神型式。在我这里,那个可以有条件地称作自然语言的基础,也是表现得比较差的。我过于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的恶和堕落,过于强烈地感受到个人的冲突和世界的整体性。 对我来说,没有比关于宇宙的和谐思想更格格不入的了。我不止一次地想,在我这里罪孽感、个人罪孽感、一般人的本质的罪孽感实际上是否强烈。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复杂的。 我想,我对于恶的感受比罪孽的感受更强,我永远不能接受作为罪行(由上帝的愤怒和惩罚所引起的)的恶的概念。 世界的堕落不仅意味着世界的罪孽,它的意义更为广阔。按自己的特点来说,我非常倾向于固有的不完善感和罪恶感,自我正确感对我完全格格不入。 我特别强烈地感受到苦难和不幸。 在世界的生活中存在着深深的不公正,存在着无辜的苦难。 这些使人难于
198
481自我认识
承认最传统的关于罪孽的学说。 我还将说到,关于天命的学说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这种学说在其传统的形式中将导致无神论。 将我从无神主义拯救出来的信念是这样的:上帝向世界自我显露,他在自然中显现自身,在圣子、圣灵中显现自身,在人类的精神高峰处显现自身。 然而上帝并不管理这个失落于外在的黑暗之中的世界。 上帝对世界和人的启示是世界末日论的启示,千年王国的启示,而非地上王国的启示。神是真理,而世界则是非真理,但是世界的非真理、非正义并不是对上帝的否定,因为我们的力量、权力甚至正义的范畴并不能应用于上帝。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世界的满足、比宣告世界无罪更不能接受的了。按我生命的第一感觉来说,我一直是个唯灵论者。 唯灵论这个词我不在广义上使用,而是将它与某种形而上学理论联系在一起。 唯灵论倾向和人类中心论倾向,和承认人的中心意义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用人类中心论与宇宙中心论相对立。 我一直责难地说,我不喜欢物质,并且逃避生活的物质方面。 这需要解释。 在肉体和物质中间划等号是错误的。人的肉体首先是形式,而不是物质。肉体的形式不是由物质的成分决定的。 可以反常地说,肉体是精神。我爱肉体的形式,但不爱具有重力和必然性的物质。肉体的形式与个性有关,并且继承着永恒性。 物质(“身体与血”)则不继承永恒性。 卡鲁斯①说得很有意思:精神不在脑
①卡鲁斯(Karl
Gustav
Carus,1789——1869)
,德国生物学家、医生、心理学家、自然哲学家。发现昆虫血液循环。无意识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发展了表情学说。 ——译注
199
转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剧。 精神的交往581
中,而在形式中。 按我的基本的生命与世界感觉来说,我无论何时也不可能为专横霸道的宗教传统的强大与沉重而感到沮丧。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尊重这种强大。 在它里面我看到堕落的世界的沉重,看到赋予历史以神圣意义的社会学解释。有时,解释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在我这里复活起来。 更有甚者,我在基督教内部和宗教唯物主义相对立。 因此,我与宗教的魔法因素有冲突。 道德的因素与自由相联系,魔法因素则与必然性及束缚性相联系。 我很不喜欢迷信和基督教中实质上的多神教因素。 实际上,这些因素是世纪初转向基督教的人们提出来的。 魔法很是大众化,很是时髦。 我不否定魔法的现实,但是对它的评价是另一回事。 基督教在历史上是很复杂的综合体。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上的基督教是教会——作为社会学现象的宗教团体——创造的。 宗教团体(共同体)的新构成可能有很多的改变。 在那里意识的结构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社会学的象征意义上对我最具永恒意义的和最杰出的是基督教的世界末日论。
G回想我的精神道路,我不情愿地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天主教徒和基督徒所称为Conversion(改宗)的事,也没有可以赋予中心地位的事。 我已经说过,我这里没有激烈的号召,也没有从纯粹的黑暗向纯粹的光明的转变。 我的生活的一定时期(我不能确切地规定它的时间)我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并且走上基督教的道路。 回想一个夏天在乡村的一个瞬间,当时我心情沉重地在花园里走着,已近黄昏,乌
200
681自我认识
云低垂,黑暗更加浓重,但是我的灵魂里却忽然一下子亮了起来。 这个瞬时的感受我不能说它是很突然的转向,因为在此之前我既不是怀疑论者,也不是唯物主义者,不是无神主义者,不是不可知论者,在这以后我也没有消除内心的矛盾,没有得到内心的充分的平静,也没有中止由于复杂的宗教问题而受的折磨。 为了描述自己的精神道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从自由到宗教生活使我精疲力竭,同时,还是要达到自由。 但是我体验这个自由不是轻易的,而是困难的。 我的这种把自由看作责任、重担,看作生活悲剧的根源的理解,是特别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正是对自由的脱离产生了浅薄性,并且可能把幸福给予顺从的幼稚者。 甚至,我不是把罪孽感觉为不顺从,而是感觉为自由的消失。 我感觉自由是上帝的,上帝是自由,并且给予自由。 他不是统治者,而是世界从奴隶制下的解放者。 上帝经过自由而起作用,而不是经过必然性或利用必然性起作用。 他不强制承认自身。 在这里隐藏着世界生活的秘密。 这个原初的宗教体验,被世界必然性的积层弄得混浊和歪曲了。说到我自己,已经说过,我宁愿不说激烈的Conversion(改宗)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不相信存在着可以由之转向的统一的、完整的正统思想。 我不是神学家,我的问题的提出,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不是神学式的。 我是自由的宗教哲学的代表。 但是,我读了许多神学的书,我想了解并确定“东正教”是怎样的。 我想用与东正教精神世界的交流,与东正教思想代表的交流来检验和补充我的学说和思想。 长期探索的结果我被迫意识到,东正教是难以确定的,它的确定的东西比天主教和新教要少得多。
201
转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剧。 精神的交往781
我认为这是它的优点,它较少唯理论的成分,这样就使人看到了更大的自由。凭良心说,我不能自认为是正统型式的人,但东正教对我比天主教和新教更亲近些,我也不能割断与东正教会的联系,尽管它的保守观念和片面性我是一直持异议和反对态度的。 当你考察一个自认为是超正统的,甚至唯一真正的东正教神学家时,我这样确定他的东正教意识:“东正教——这就是我”——这个正统的捍卫者和异端的揭发者这么说。 如果我面对这样的人,我就回答他说:“你的形式的标准是可以信赖的,但你的‘东正教是你的’观念是错误的。东正教,这不是你,而是我。”我很早就指出过,实际上我不承认任何正统与权威。 他们自封权威,揭露总主教和主教的异端,他们承认自己有大的自由,而否定其他人的自由。 为了更彻底地转向东正教,我开始特别迷恋于东方国家的教父。但是,我一直对古希腊的教父的评价比西方的和经院哲学的教父高。 圣谢拉菲穆。 萨洛夫斯基成了我最喜爱的圣者,希望在他那里看到他有的东西,也希望看到他没有的东西。 在这些年里常常是寻找狂喜比探索真理更多些。 这显然是对历史批判的完全漠不关心。
G我的宗教关注的中心一直是神正论问题。 在这点上,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 无神论的唯一郑重的论据是:全能全善的上帝与世界之恶和苦难的存在很难协调。对我来说,所有的神学学说都将奥秘理性化,而这是不能容许的。 我认为,神正论问题首先是以我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自由问题。我
202
81自我认识
得出了存在着非创造的自由之不可避免的结论,这实质上也就是承认不能理性化而只能描绘通向自由的精神道路的奥秘的存在。 我在很多著作中发展了自己的自由哲学,这种哲学是与恶的问题和创造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我说过,当我出版《自由的哲学》时,我的自由哲学还只是不完善的草图。后来,因为我的“非创造的自由”思想(这方面的术语,我是逐渐制定出来的)而受到许多的指责。 一般地说我的这个思想是与我所喜爱的伯麦关于Ungrund(深渊)
的思想相关的。不过,在伯麦那里Ungrund也就是(按我的解释)在上帝之中的原初的自由,而我则认为它是在上帝之外的自由。 原初的自由扎根于“无”之中,这完全不应当意味着本体论上的二元论,因为二元论已经是理性化了的。 传统的天意说激起我最激烈的批判,实质上,这种学说是隐蔽的泛神论,可以接受的形式极少,对此我已经讲过。 如果在上帝的潘多拉盒子中原来就装有全部的罪恶和苦难,装有战争和灾祸,装有瘟疫和霍乱的话,那么,信仰上帝是不可能的,反对上帝是无罪的。 上帝以自由方式进行活动,而不是以客观必然性的方式起作用。 他精神地活动着,而不是魔法式地活动着。 上帝是精神,对神的天意只能精神地理解,而不能自然主义地理解。 上帝不存在于神的名义中,不存在于魔法作用中,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力量中,而存在于全部正义之中,存在于真、美、爱、自由、英雄行为之中。 把上帝作为力量,作为全能之物和政权的这种感受,我是最难接受的。 上帝什么样的政权也没有,他所有的比政权小,比警察还小,对宗教来说,作为社会现象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威力等范畴,都仅仅是
203
转向基督教。 宗教的悲剧。 精神的交往981
社会的内在结构。 上帝没有政权,因为不可能把那些卑鄙的方式如政权搬到天上去;上帝不采用任何一种有着社会起源的概念。 国家是世界现实中最下贱的现象,任何类似国家的东西,也不可能搬移到神与人和世界的关系中来。 不能把统治关系移到上帝和神的生活中去。 在真正的精神体验中没有统治与奴役的关系。这样的真理在神学中整个地被否定了,神学处在社会内在的政权之中。 我认为,将基督教意识从社会形态学中净化和解放出来是基督教哲学的重要使命。 神学处于社会形态学的权力之中,它在社会的统治关系范畴中思考上帝,也这样来对待关于上帝——父亲、关于作为世界创造者的上帝的神学思想。我一直对上帝之子——基督、“神人”
、人的上帝的感受比对上帝——力量、上帝——创造者的感受要强烈得多。 这意味着,关于上帝——父亲、世界的创造者的思想,我认为是受了宇宙形态学和社会形态学强烈传染和歪曲。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信仰上帝,即存在着上帝之子救赎苦难。不是上帝与人的和解,而是人与上帝的和解。只是苦难的上帝才能与创造作品的上帝相协调。 纯粹的一神教是不能接受的,它是偶像崇拜的最高形式。 与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