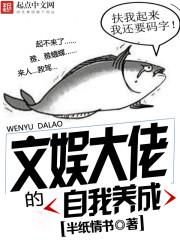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反动,我在这种革命中发现了对自由的厌恶,对个人价值的否定。 我一直有着两重性,我既有革命性又保有贵族的天性。 奇怪的是,这种两重性从没引起与我的性征相反的相应分裂。我从小就不能接受世界的秩序,不能服从世间任何东西,我总是由这样的特点中看到自己革命性的根源。由此已经可以看出这种革命性宁可说是个人的,也不是社会的,这是个人的起义,而不是人民群众的起义。 在我的禀性中永远具有造反和抗议的因素,这种因素反对革命中的奴隶制。 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紧张时刻,有一次,一个对苏维埃政权持机会主义的适应态度的以前的革命家对我说:“按本性来说,您是革命者,而我完全不是革命者。”很明显,他指的是我的不调和性,不适应性。 不依赖性和不适应性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没把它当作什么特殊的优点。 当人们对我说我的某些文章和某些观点是勇敢创新的时候,我甚至感到奇怪。 对于所谓的“社会舆论”我终身都是绝对蔑视的,不论它是怎样的,我从来没有重视过它。 对我来说,甚至不存在对待“社会舆论”的态度问题。 很难用政治来说明这种“社会舆论”方式的特点,革命的政治有自己专横的“社会舆论”
,由于这种“社会舆论”
,奴才们便依附于职业革命家。实际上,我厌恶那种把人的存在抛于它自身之外使之客体化的最可恶形式的政治,它永远是建立在恶的基础上的。不过,这种对政治的厌恶并没有使我逃避这个世界,而是渴望翻转这
127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31
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 在一定的阶段,政治是控制人们的虚构物,是吸吮人们鲜血的寄生疣物。 纯粹的政治革命使我嫌弃,不仅由于它的实践斗争手段、否定自由等等,更是由于它不是精神革命,精神被它完全否定掉或者成了废物。 这个世界的所有政治上层建筑都是适合于平凡的普通的、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人群的。 国家、客观化的道德,革命与反革命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 同时,还存在着真理,存在着全部解放的神圣之光。 我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当缺少能够改革和改造社会的创造性精神力量(或者这种力量很弱)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全部国家和全部革命,全部政权组织都落入世界公爵的权力控制之下了。
G很早我就有这种意识:世界、社会、文明都奠基于谎言和恶之上。 我读了许多历史书,这些读物对我来说是折磨人的,虽然我承认历史的意义并且把历史哲学看作自己的专长,但是,我认为历史是充满了罪行和谎言的,对神圣的历史事件的体验于我是格格不入的。 一个时期我曾努力去承认某种神圣的传统,但这对我来说总是不成功,而且引起了厌恶。我在精神上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在启蒙、批判和革命的世纪之后出生的人。 我克服了“启蒙”的理性主义,但这种克服是黑格尔所说的Aufhebung(扬弃)
,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停留于“启蒙”
或者装作停留在这个界限上。20世纪初的某些宗教学说装作处于朴实的、前批判的自发时期,摹仿人民的原始主义。 我的非理性主义或者超理性主义是通过“启蒙”而完成
128
41自我认识
的,但这种“启蒙”不是18世纪法国学说意义上的,而是康德意义上的,康德形成了“启蒙”的永恒真理,他的自律学说就是与此相联系的。我从一开始就是自主的反权威主义者,任何专横霸道都不能使我就范,在我开始起来对周围的社会造反时,托尔斯泰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任何时候也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在这个词的固有意义上)
,我甚至不喜欢托尔斯泰主义者,与他们格格不入。 只是在我身上有托尔斯泰的“疫苗”
,它一直存在于我的全部生活中。 它表现为我对于所有假圣人的和假伟大的历史的鄙视,对于历史上假圣人的蔑视,也表现为我深信全部文明的和社会化的生活及其规则、繁文缛节都不是真正的、真实的生活。 不过,我同时还具有历史感,这却是托尔斯泰所没有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中说:“从本性上说,人是预先被规定于社会中的政治动物,如果谁按自己的性质说不是国家的某一部分,他就是一个鄙夫或者是一个超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服从任何事物的。 我不认为自己是低于人的价值的存在,也不认为自己是高于人的价值的存在,但是我很接近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种情况。 其实,这表现了古代的意识和基督教历史时期的意识的巨大差别。 同样,这也是俄罗斯人和西方人的差别。 俄罗斯人不接受西方文明的人们所采纳的那种世界秩序。我很早就感觉到与贵族社会的断裂,我脱离了那个社会。对我来说,那个社会里的一切都是不可爱的和引起很多愤怒的,当我进入大学时,这种情绪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更加喜爱犹太人的社会。 至少,能够保证他们不是贵族,不是亲
129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51
戚。 当我的犹太同学来找我时,我的母亲就提出习惯性的问题:“Est-ce
unmonsieur
ou
ce
nest
pas
un
amonsieur?“
(“这是位先生呢,还是不是位先生?”)在那以前我曾因母亲永远不使用犹太语言甚至坚决不说“犹太人”而说“”吓唬过她。 与不喜欢贵族相联系,我也不喜欢b c M C S W E K军事,我决定离开武备中学去参加为了得到进入大学所必须的中学文凭的考试。 这是不轻松的,因为我在被动地掌握知识方面很无能。 我的主要的奋激——它比全部理性的理论和自觉的信仰都更为原始,更为有力——便是从少年起便固有的对国家和权力的厌恶。有时我觉得那表现了封建的根底。当我还小的时候,刚刚接触不管什么国家制度,虽然是最无恶意地但已处于厌恶和愤恨的状态,想毁坏这种制度。 按说我不能有任何的resentiment(怨恨)
,我属于享有特权的、统治的阶级,我的家庭和所有的总督和省长都有着友好的交往。但是对我来说,所有的统治制度都是宗教裁判所,所有的政权的代表都是残酷折磨人们的人,尽管在家庭关系中,在上流社会的会客室里,我遇到的这些政权代表经常是善良的和客气的人。 我不喜欢上流社会是有别的原因的。 上流社会还与宗法制度的习惯紧紧相联,对我来说,这是某种与国家不同的东西。所有的人在执行政权的职能时多是处于半兽状态。宪兵将军H。 拜访我的双亲时,遇见我也是很客气的,但是当你在监牢和审讯室里看见他时,他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无论何时,任何社会地位,任何等级的官衔,任何历史的大人物,都不会使我肃然起敬。 大概这种极端形式的特点是很少能碰到的。 我发觉,即使对于革命家,也常常是以其等级的
130
61自我认识
官衔使人敬仰,虽然是在否定的征兆之下。 在革命中获胜的革命者,自己也很容易地得到重要的等级官衔。 即使对于较高级结构的职务中的等级头衔,如院士、学位、广为知名的作家,我也从不敬仰。 概而言之,我与敬畏感、按社会地位区别人、人的固有本质之外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人们认为我具有令人敬仰的地位,对此我甚至感到不愉快。 我永远忍受不了人类社会的“印记”。约定的法律,封号,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充满对立的现实。 将经验的现实神圣化,将国家神圣化,生活方式神圣化,教会的外表的东西神圣化,特别使我感到愤怒,这些东西的神圣化就好像在纯经验的罪恶后面还存在着善的本质似的。通常人们这样想,人可能是坏的,但代表他们的官员是好的。 我过去和现在则这样想:对于不好的人们来说,官员更加不好,我这里指的是所有的官吏,其中包括着革命的官吏。 神圣的不是社会,不是国家,不是民族,而是人。 无政府主义,人格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我形而上学地固有的。 它是我现在所固有的,一如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固有的一样。不过,我并不赞同那种可称为温情的、乐观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如果有某种东西是我所固有的,那么,这是锡利亚式(“千年王国”说)的期望。我的青年时代的革命时期很促进了我的个性的道德外观的形成。革命的信念和革命的氛围使我产生了特殊的心理,产生了对未来可能的考验的特殊态度,一般地说产生了对未来期望的特殊态度。这种形态的心境我后来没有重复出现过,但是却产生了我的个性的坚毅性。 有意思的是,我的生活中的基督教时期却没有产生这种坚毅性。 我说,这种坚毅性是和
131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71
俄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禁欲生活相联系的,这种禁欲生活不是普通的禁欲生活,而是在被迫害中的坚忍的禁欲生活。当然,革命的禁欲生活在程度上比我所经历的要大得多,因为我没有过那种被迫害者栽上罪名而不得不忍受的禁欲生活。 我希望人们能正确地理解我,一般地说,我不认为我的革命的青年时代是禁欲主义的,甚至不认为那是革命意义的禁欲生活。但是,无可怀疑,我过着禁欲生活,在全部生活中一直保持着禁欲生活,正如一直保持着初恋一样。 当我设计了我的未来的时候,当我想象着未来的时候,那片密林给我提供的就是忍受苦难,为了信念而作出牺牲。我使自己习惯于这样想:监牢、流放、国外的艰难生活在等待我。 这些无论何时也没使我害怕。 我从来不向往外观上虚荣的升迁,从来不去谋求任何社会地位。 我一生都厌恶那种“占据社会地位”的事情,这种厌恶不仅由于我的革命感情,而且是由于我的基督教感情。我常常像受罪一样地去体验我在许多方面的特权地位,不过,我从来也没有准备去作职业革命家。比起职业革命家来,我更是一个理论家、思想家。 我的作用就在这里。 但是,我感到,我不仅和贵族社会有着深刻的断裂,而且和那称为自由的甚至激进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可以享有生活的福利,但却不遭受任何危险,即使反对党也是如此)也有着深刻的断裂。记得我对于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带有某种轻蔑态度的。当我还是大学生但已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时候,我参加了激进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小组的文学集会。 M。 图根—巴拉诺夫斯基把我领到那里,这次集会主要是与《神的世界》杂志联系起来的,这个杂志当时已经刊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了。
132
81自我认识
我自己也开始在《神的世界》上发表文章。 彼得堡的文学集会引起了我疏远、厌弃的感觉,我感到所有的人都是不真实的,其实,这种感觉是由于相对于我所接触到的所有社会集团的。 我称之为青年时代自己个性的革命坚毅精神是比革命性这个词的原有含意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正是由于这种根基,使我一直讨厌文学家、律师、教授们的社会,而在国外的时期则讨厌议会主义政治家的社会。 这种根基决定了对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的不调和的态度,后来我想,与以保留的形式和反对的形式享有现实财富的社会实行宗教上的断裂是可能的。 但是,我自己并不是这种僧侣禁欲主义的代表,清教徒的教义对我也完全格格不入。 我现在同意这种想法:是同一种动因引导我走向革命和走向宗教。 在另一种情况下,我讨厌满足于“象征的世界”
,希望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但是我的这种态度有比较激烈的时候,也有比较不那么激烈的时候。 不仅从社会的意义上而且从精神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性”
的厌恶永远是我的推动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督教和东正教,同样可能是资产阶级的。 我永远不喜欢这个世界的力量,不喜欢盛大隆重的东西。 我一直体验着在力量和价值之间令人痛苦的冲突。 力量大的价值低,力量小的价值高。 从“魔鬼阵营”中越出的革命贵族是很有魅力的,有时我为此而倾倒,这是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
G还是在进入大学之前,在看到马克思主义小组之前,我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同情已经明显起来。 我是从伦理学论证
133
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91
社会主义的,我还把这种伦理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