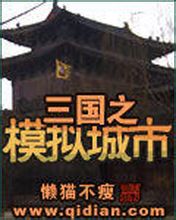城市蜿蜒-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同居吧。娃娃脸把外衣脱了,挂在衣架上,先坐着跟江一聊了几句,他说:分你到机场啊,下午叫你去拿调令。江一说:是吗?那多谢你啊,借问一下,机场是什么概念?娃娃脸说:机场?就是客运嘛。江一当然知道机场是客运,可自己到那儿去干什么呀,总不能是卖票吧?江一对这个鸟单位的事一点也不得要领,心想娃娃脸初来乍到,大概也不甚了了,问他也是白搭,还是睡一觉,下午去拿调令吧。
一觉醒来,娃娃脸已经不在了,看看时间,已经三点多。江一想起拿调令的事,赶紧爬起来洗刷,换了套干净衣服,拖鞋也在水龙头下冲洗了一遍。他知道穿这玩意儿不像话,可还没钱去买鞋,只好凑合了。到了人事处,娃娃脸和女领导都在。娃娃脸看见江一就对他使眼色,还对着他向女领导努嘴。江一不知道他是啥意思,走过去叫了声方科长。方科长说:来了?我给你开调令。
女领导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空白调令,认真地填了起来。领导填调令的时候,江一不好站在旁边看,就四处东张西望。人事处很多人,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的,大家都显得很忙碌。娃娃脸也在那儿忙着整理文件。
江一终于拿到调令,上面写着分配到洲头咀当干部。他不知道洲头咀是干什么的,他就知道洲头咀肯定不是机场。娃娃脸不是说分到机场吗?江一就多了句嘴:不是分我去机场吗?女领导听了这句话就拿眼睛去找娃娃脸,娃娃脸早就溜出去了。领导只好解释说:本来是这样安排的,今天上午机场有人过来开会,说没地方安排住宿,所以改派到洲头咀。江一说:洲头咀是干什么的?领导说:旅检。看到江一仍是一脸迷茫,就解释说:就是检查旅客的行李物品。江一老是有种心有不甘的味道,就因为一天之内把他调了两个单位。后面那个单位一定没有前面那个单位好,因为好地方总是人满为患。江一说:想问一下,我住在哪儿?不会老让我住招待所吧?领导说:住在三元里,火车站后面。江一突然想起下火车时看到单位在那里也有派出机构,心想那地方不错,以后回家坐火车方便,离宿舍又近。他试探着问:可不可以分到火车站?领导说:你不想去洲头咀?江一说:去哪儿没所谓,我只想离住的地方近一点,因为我——晕车。领导说:不会骑单车吗?江一说:单车是什么?领导就笑了,她笑着说:就是自行车。自行车自然会骑,可干吗要告诉你会骑呢?会骑你还不让我天天骑自行车上班?女领导说:自行车也不会骑?她装出为难的样子,冥思苦想了半天,才说:车站肯定不行,没编制了,不如去邮局吧,就在火车站旁边。这就叫想要的偏不给你,不要的偏塞给你。这可是国家机关,哪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江一拿到调令后,心里有点沾沾自喜,这可是他到单位争取到的第一个胜利。这下好了,上下班不用在车上颠簸了。事后他才知道,邮局是单位里最差的单位,大家都叫西伯利亚。也就是说,他给女领导狠狠地涮了一回,他还自以为很得意呢。
第二天,房间里住进了个新同事,这人瘦高瘦高的,拎着两个大皮箱。江一那时正躺在床上看书,突然听到锁孔有响动,他就盯着房门看,门推开了,先进来两只大皮箱,接着探进一只黑黑的脑袋,跟着才是整个身体。江一一看到两只皮箱人就呆了,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用皮箱装行李,就算不富裕,至少也是小康了。这人是广东某高校毕业的,分到肇庆。两人聊了些闲天。江一一看还能跟他聊两句,看他样子也算大方的,不如找他借点钱。一个单位,年头不见年尾见,他不会担心自己不还钱吧?可初次见面就找人借钱,到底不好开口。
二
江一的行李还在火车南站,就一些书籍和床上用品,还有两件御冬的衣服,尽管不值什么钱,但要重新置办,却要花不少钱。娃娃脸一早就帮江一联系好了车,约他九点半在火车站门口等。这小子昨天差点给女上司训了一顿,就因为江一出卖了他。他回去后,女上司盯着他看了好几眼,总算没训他。他也不记仇,一早就安排江一去拿行李,就因为这个,江一后来跟他做了朋友。
早点江一吃了一只两毛钱的粽子。他本来很讨厌吃糯米,可这玩意儿吃了不容易消化,可以管好一阵子,比馒头包子顶饿。南站离单位不远,江一边吃边往前走,省下几分钱的路费。走到南站门口,才九点十分,江一一看时间还早,就在南站里面溜达,转了一圈,再回到门口,已经九点半了。江一那块手表是在北京买的,三十九块钱,相当于大四时候一个月的饭钱。这块国产表如今不怎么听使唤了,一天慢一分钟,半个月就得调一次,否则就会误导主人。江一站在门口等,双眼盯着进出的车辆,没有发现一辆车挂着单位的牌子。他看了一个多小时,看得眼酸目肿,从南站进出的车真是多,就是没有一辆是冲着自己来的。
这样等下去不是个事,江一四处瞅瞅,发现传达室有部电话,传达老头守在一边,那老头目光如电,已经盯着江一看了好久。在他眼里,江一大概是个盲流,甚至就是一个不怀好意的歹徒。老头一直在监视着江一,看他想干什么。
江一站在玻璃窗外,敲了敲玻璃,叫一声大爷。大爷把玻璃窗拉开一条缝,那条缝刚好够塞进一只拳头。大爷说:干什么?江一说:大爷,借个电话用用行不?大爷说:打电话?去街边打。江一心想,去街边打我还用得着求你吗?这不是没钱吗?有钱我来看你的脸色我是吃饱了撑的呀。江一清了清喉咙,尽可能把声音放柔和一些:大爷,怎么跟你说呢,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这也是没办法,我刚毕业,才分来单位,今天来拿行李,单位说好派车来,可等到现在也没见个人影。这么说吧,大爷你也有儿女吧?假如站在你面前的是你儿子,我知道我不配做你儿子,那么就当是你侄子、外甥什么的,身无分文,还没吃早餐,站在这儿等一两个小时,吃灰尘、吃废气,又冻又饿,差点给人当成歹徒。您明明知道他口袋里没钱,却非要他去街边打公用电话老头说:得得得,给你打,给你打。江一打电话时老头说:我不是可怜你,我是怕你唠叨。
接电话的正好是方科长。江一说:领导,帮我拉行李的车怎么还没到呀?领导说:车没到?那你再等等,现在广州到处塞车。江一说:等多久都没所谓,别的东西我没有,时间我有的是。问题是有没有派车,车来不来?领导一听江一有些情绪,语气就软了八分,她说:派了车,你再等等,我帮你催催。
江一把话筒还给老大爷。说:问一声心里就踏实了,多谢。
江一继续站在门口等车,看着民工装卸货物。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有两个穿蓝背心的民工在往上面装纸箱。他们干得很卖力,满头大汗,身服全湿透了。装完了货,一个穿西装的人走过来,每人给了十块钱,大概是小费,民工也不说声谢,把钱装在口袋里,站在树下擦汗。歇了不到五分钟,又有一辆卡车开了过来。这回是往上面装布料。江一看那布料不太重,估计拿得起放得下,突然心里一动,走过去想搭把手。他刚把一捆布料拿起来,从仓库里走出一个男人,问他干什么。江一说:不干什么,闲着也是闲着,帮他们打个下手。男人说:去去,一边去,这钱也是你挣的吗?给他一口说破了江一的企图,江一还真有点脸红,原来凭力气吃饭也未必都光彩呀。想把这几天的零用钱挣到手的愿望破灭了,江一只好继续站在大门口等待那辆等也等不来的车。
转眼到了十二点半,两个民工装完了货,坐在树下休息。一会儿有人送了三个盒饭来。民工赶紧洗手吃饭,其中那个高一点的民工突然对江一说:兄弟,我们叫多了一份,要是不嫌弃,拿去吃吧。一看到盒饭,江一的胃神经就开始痉挛,像有几万只小虫子在咬。这会儿也顾不得脸面了,反正初来乍到,也不怕碰见熟人,他说:那就多谢了。走过去,坐在树下,边吃边跟他们聊起来。这是两个湖南民工,在南站干了半年,每月工资八十元,不包吃不包住。他们的工资刚好够吃住,如果客人不给小费,他们就等于白干了。江一问一个月能挣多少小费,高个儿说:难讲,有时多一点,有七八十块,有时少一点,才十来块钱,要看客人大不大方。江一说:今天收获不小啊。高个儿说:这个客人每次都比较大方,他有钱。他们谈话的时候,矮个儿民工一句话也不说。江一问他话时他就笑一笑,使人疑心他是不是个哑巴。高个儿也问了江一一些问题,江一如实相告。他说:一看就知道你是读书人,不过是穷苦人家出身,我佩服你,要是有困难,就说一声。江一说:你们也不容易,挣的是血汗钱,今天请我吃饭,我已经非常感谢了。
门卫老头突然打开窗子,对江一喊:喂,你还要不要打电话?江一一愣,马上说:打。他一边拔号一边对大爷千恩万谢。大爷却不买帐,他说:你别谢我,我是怕睡了午觉,你又来吵我。这回接电话的是娃娃脸,他一听出是江一就问他在哪里。江一说:在南站。娃娃脸说错了,在北站,司机去了北站。江一说:他妈的,我的行李在南站,他去北站干什么?
娃娃脸一见到江一就嬉皮笑脸地说:不好意思,让你白等了,责任在我,我没讲清楚。江一说:不关你事,那司机是傻逼。娃娃脸说:还没吃饭吧,我请你吃饭。江一说:多谢,一个民工赏了我一个盒饭,要请你晚上请我,我没钱吃饭。娃娃脸以为江一开玩笑,嘿嘿直乐。
江一回到招待所倒头就睡。睡中午觉已经成了习惯,不睡不舒服。江一总是考虑上班的地方要近,也是没有办法,那是给身体逼的。这一觉睡得够长的,醒来已经六点多,估计是在南站站的时间太长,身心疲惫。江一用手在脸上干洗了一把,觉得饿的感觉又强烈起来。中午吃了个盒饭,好像才填了半个肚皮,他比民工还能吃呀。娃娃脸似乎没有来找他的意思,不能指望他请吃晚饭了,晚餐只好继续素面加白开水。提起素面白开水,江一就想起在学校里精打细算的事。学校里一个菜要五毛钱,加上二毛钱的馒头,要七毛钱一餐。如果买方便面,二毛五一包,差不多可以买三包,省一点可以顶两餐。干脆买方便面吃算了,招待所有的是开水。一块钱可以买四包,又不用看面馆老板的脸色。那婆娘看他尽买一块钱的素面,吃得又慢,等于占了几个人的位子,早就对他没有好脸色,卖票的时候爱理不理。江一对这种人情世故早就见多不怪了,但心里还是不大舒服,心想以后有钱了就不来帮衬你。这家小店似乎也不指望江一来帮衬。
单位旁边就有一家杂货店,不过广州的方便面跟北京不是一个行情,同样一个牌子的,要三毛五一包,一块钱买三包还差五分钱呢。江一一算帐就犹豫起来,这方便面毕竟没那么好吃呀,如今饭量大了,三包未必够吃一顿,可想想面馆那婆娘的脸色,还是决定买方便面。
肇庆佬九点多才回招待所。江一跟他聊了几句闲天,终于决定向他借钱。江一说:兄弟,你手头还宽裕吧?兄弟说:一般啦。江一说:借个十块八块的,行不?兄弟没有出声,继续收拾他的东西,然后就从房间里消失了,直到深夜才回来。一回来就收拾东西,似乎准备明天一早就走人,然后就进卫生间洗刷,然后倒头就睡。江一一早就躺在床上,但他睡不着,同室的一举一动他都听在耳里,内心十分愧疚。因为他要借钱,害得同室跑到外面躲了四个小时,还逼得他一早就走人。钱真是个好东西呀,以后要是有了钱,不知会变得吝啬还是大方。江一相信肇庆佬不愿意借钱一定有他的苦衷,他大概担心到了肇庆也陷入江一的这种困境吧。谁知道呢,去肇庆还要路费,到了肇庆也许还要住招待所,还有其他开销。江一宁愿相信是这样的原因,这样他就不会觉得自己的同事还不如陌路相逢的民工。
也不知是想得太多,还是下午睡得太多,没法入睡。江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数羊都数到一万八了,后来终于迷糊着进入梦乡。江一是给电话铃声吵醒的,娃娃脸在电话里说:司机在门口等你呀,叫你去搬行李。江一没好气地说:让他等着吧。他心里说:老子是没钱,有钱早叫出租搬回来了,用得着求你?江一起来清洁自己,发现肇庆佬连屁都捡走了。呵呵,又是自己一个人住,舒心噻。中午娃娃脸可能要来午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