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区柯克悬疑小说-第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马斯特回到原来位置,呼吸越来越困难,他极力不去想它。
如果他敲铁门,会不会引起外面的人的注意呢?马斯特躺在地上,听不到任何风声,推开书架,也感觉不到墙壁传来任何凉意。外面的声音真是很难传进来。他居然指望有人能听到他微弱的声音。根本不会有人进来——除了玛格丽特回来拿她忘记的东西。马斯特又将耳朵贴在铁门上,不知道外面雨停了没有。
马斯特往旁边一倒,他忘了铁柜在那里,撞得头晕眼花。
对了,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查理却说他要到马路边画向日葵,这根本不可能。另外,他还说过,如果画不成的话,他会再打电话来的。不过马斯特承认,他弟弟可能刚刚睡醒,所以可能忘了说过的话。
洛克在圣路易市,丽达在纽约,那就应该是查理了。
马斯特心情平静了一点,对自己也很满意。现在他快死了这种心境下,他甚至觉得可以原谅查理,谋财害命,真不值得。
跟查理在一起,马斯特从小就处处占上风。
马斯特从衬衫口袋里拿出圆珠笔,为了看清楚,他打着了打火机——虽然他知道打火机会加速他的死亡。呼吸更加困难了,马斯特从文件上撕下一张纸,左手举着打火机,右手打开圆珠笔。
只花了三十秒钟,马斯特在纸的反面写上查理的名字,以及“我看见他靠近这扇门”,“这是预谋”。后面这四个字,会让查理也死在一间黑暗的房子里的。
马斯特吃力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打火机的火焰渐渐灭了,屋里又是一片黑暗。
“你看到这书架推开了,所以打电话报警?”警长耐心地问玛格丽特说。
玛格丽特点点头。
地下室的铁门已经打开,警察局的照相人员已经拍完照,验尸的医生宣称马斯特已经去世。玛格丽特一直不停地哭泣,她望着人们把马斯特的尸体抬上了救护车。大家都出去了,包括“上校”,它今天早上还没有活动呢!
“上校”在草地上打滚,虽然没有以前灵活了,但仍然很快活,它想叫主人去关那刺耳的茶壶声,跳起来撞击铁门,因为用力过猛,碰伤了右脚,显得有点跛。
屋里,警长问玛格丽特:“谁是查理?”
琳达
琳达
琳达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琳达一头金发,衣着时髦,开着一辆赛车。她买下了我们前面的木屋。我们这个村子,住的大部分是退休老人和周末度假者,突然出现了琳达这样的美女,大家都被震住了。
琳达一来,就缠上了我妻子妮娜。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村里,妮娜是唯一年龄和她差不多的女人。当然,我认为,如果琳达有选择机会的话,她绝不会选妮娜做朋友的。在一般人眼中,妮娜是个羞怯、文静的家庭主妇。她怎么会引起琳达这样外向的女人的注意呢?妮娜自己向我做了解释。
“亲爱的,你注意到没有,人们开始回避她?上星期,金斯基家的宴会没有邀请她,阿尔玛拒绝她参加节日委员会。”
“我并不觉得奇怪,”我说,“瞧她谈话的方式和内容,谁也受不了。”
“你是说她的浪漫史?但是,亲爱的,她生活在那种社会中,她那么说话是很自然的,这说明她很坦白。”
“她现在已经不生活在那种社会中了,”我说,“如果她想要人们接受她,她应该适应现在的环境。你注意到没有,当她大谈和酒吧认识的男人如何度周末时,金斯基太太脸上的表情?我想劝她别那样大谈男人,可是又不好说。她总是说,‘我和某人同居的时候,’或者‘我和某人风流的时候。’你知道,年纪大的人是不喜欢听我们年纪不大,”妮娜说,“我希望我们脑子开通些。你是喜欢她的,对吗?”
我对妻子一向很温和。妮娜的父母很专制,从小轻视她,长大后,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所以我对她从不粗暴。现在,我也只能顺着妮娜的话,说我挺喜欢琳达的。
如果琳达只是白天和妮娜在一起,我不会有什么意见的,我相信妮娜不会受她的影响。
但是,每天我劳累一天后回到家中,总会遇到琳达。她有时很悠闲地坐在沙发上,穿着丝绸长裙子和高筒靴子,不停地抽着烟。有时我们正要吃晚饭,她就带着一瓶酒来了,和我们聊一些她感兴趣的话题,像“结婚是个等死的疗养院吗?”或“男女应该生孩子吗?”她经常会说些让我们那些年纪大的朋友不高兴的话。
当然,我并不是非得和她们呆在一起,我们的房子很宽敞,我可以到厨房或书房。但是,我想过以前那种安静的日子。有时,她会要我们去她那里喝咖啡或喝酒,那就更没意思。她的那个木屋装饰得很华丽,但很俗气,她会向我们展示她以前男朋友送的那些礼物。
每当我拒绝前往时,妮娜就会很不高兴。为了让她高兴起来,我就会建议去看琳达,一听这话,她马上就会兴奋起来。
不过,有一个念头在支持着我,那就是,像琳达这样吸引异性的女人,很快就会找到男朋友的,那样的话,她就没有时间缠着妮娜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还没有找到男朋友。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妮娜。
“她去伦敦,就是为了看那些男朋友,”妮娜说。
“可她在这儿从来没有男朋友。”我说。
那天晚上,琳达请我们过去欣赏一幅画,她说是一个叫拉尚的人画的,那个人非常迷人,也非常喜欢她,我说我想认识他,为什么不请他来度周末呢?
琳达晃了晃涂成绿色的指甲,诡秘地看了妮娜一眼说:“那样其他老朋友会怎么说呢?再说他们也不喜欢乡下。”
显然,琳达的其他男朋友也不喜欢乡下,所以只能琳达去伦敦看他们。我注意到,自从我向她打听拉尚这个人之后,琳达去伦敦的次数更多了,回来之后讲的那些故事,越来越耸人听闻。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对她产生了怀疑,我决定试探她一下。
我一反常态,不但听她说,而且还问她一些问题。我记下她提过的人名、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我会问她,“我记得你说过,你是在美国认识马克的?”或者问她,“你那次度假是和赫伯一起去的吧?”在不知不觉中,我慢慢地套住了她。圣诞节那天,我做了一次试验。
我注意到,琳达和我独处时态度很奇怪。比如,有时琳达过来,妮娜不在,她和我在一起时,总显得冷冰冰的,有点羞怯,她那些挑逗人的谈吐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显得很生硬。她只会聊聊村上的事情,一本正经的样子。
那时候,我才想起她参加村里宴会的情形,她从来没有引诱男人的举动。是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太老了,不值得引诱呢?一个身材细高、英俊的五十岁男人,难道不能和一个三十岁的少妇玩玩吗?当然,他们都有家有口,可是,她提到的那些男朋友也都是结了婚的人啊。从她的话中可以听出,她对抢别人的丈夫,并没有什么顾忌。
圣诞节那天早晨,妮娜在厨房里忙碌,琳达来了,我去开的门。
“圣诞快乐,”我说,“琳达,亲吻一下吧。”在圣涎树边,我抱住她,亲吻她的嘴巴。她全身硬梆梆的,然后发起抖来。她举止笨拙,表情尴尬,就像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我一下子明白了,她为什么离婚。她是个性冷淡者!一位美丽、活泼、健康的女孩,居然缺乏那方面的能力。她过去所说的一切都是她的幻想,她在幻想中把自己说成一个荡妇。
开始,我觉得这很好笑,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一发现告诉妮娜。可是,那天直到凌晨我们才有时间独处,当我上床时,妮娜已经呼呼大睡了。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我不像最初那么兴奋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如果我告诉妮娜实话,她一定会很伤心,会憎恨我的。
我怎么能告诉她,我吻了她最好的朋友?在她不在场时,我挑逗、引诱她的好朋友,结果被拒绝了?
接着,我意识到,我真正发现了什么:琳达憎恨男人,没有男人会娶她。她会永远一个人住在这里,每天到我们家来,一直到死。
当然,我可以搬家,可以把妮娜带走。远离她的朋友们?远离她心爱的房子和乡村?我怎么能保证,琳达不会跟着搬呢?琳达非常喜欢妮娜这样一位天真的听众,她不会放过妮娜的,我们永远不会再有宁静的生活了。
天亮时,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自己唯一能做的是什么。
我决定杀掉琳达。
决定容易,实施很难。对我有利的一点是,在外人看来,我没有杀人的动机。邻居们认为我们夫妇心地善良,非常宽容,居然能与琳达这样的人相处。做出杀她的决定后,我对她非常好。从邮局下班或购物途中,我会到她家去看望她;如果下班回家,只有妮娜一个人在,我就会问,琳达到哪儿去了?然后提议立刻打电话给她,请她过来一起吃饭或喝酒。妮娜对此感到很高兴。
“亲爱的,过去我觉得你不是真心喜欢琳达,”她说,“对此我很内疚。现在你意识到她的好处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一月,村里出了一件事,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村子边缘的一栋木屋里,一位老小姐被杀。警方认为是精神病人干的,因为家中没有任何东西被偷或被毁。
这案子似乎破不了,我开始考虑,怎么用同样的手法杀掉琳达,使凶杀案看上去像是同一个凶手干的。正当我这么计划时,妮娜染上了流行性感冒。
于是,琳达过来照顾妮娜,为我做晚饭,打扫屋子。因为大家都相信,杀害老小姐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所以,晚上我总是送琳达回家。虽然她的小屋就在我们花园边的巷子里,距我们家只有几英尺。那儿很黑,因为没有街灯。每次送她回家,我都要求她挽着我的手臂,看到她畏畏缩缩的样子,我都觉得好笑。
我总是坚持送她进屋,替她打开所有的灯。后来,妮娜的身体渐渐好起来,需要好好睡一个晚上,我就到琳达那里,和她一起喝杯酒。有一次,在离开她那里时,我在门口与她吻别,让任何一个注意观察我们的邻居知道,我们的关系是多么地融洽,我是多么感激她照顾妮娜。
后来,我自己也染上了感冒。开始我觉得,这病扰乱了我的计划,因为我不能耽搁得太久,人们对凶手的担心逐渐淡漠了。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生病给我提供了方便。
星期一,我已经在床上躺了三天。琳达对我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那天,妮娜说她本来答应去金斯基太太家的,但是她不想去了,撇下我似乎不好,她说,如果我病好一点的话,她准备星期三去金斯基太太家,帮她剪裁衣眼。
星期三那天,我觉得身体好多了,下午,医生来给我作检查,说我胸部仍然有痰。当他到浴室洗手时,我把他插在我口中的体温表取出来,放到床后的暖气机旁边。体温一下上去了。我装出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说觉得头晕,而且忽冷忽热。
“让他在床上好好休息,”医生说,“多喝点热饮料,他可能起不了床。”
我说,我两腿发软,起不了床。妮娜马上说,她晚上不出去了。医生帮了我的忙,他说,别那么大惊小怪,我只是需要休息,多睡睡觉就行了。
七点钟,妮娜终于到金斯基太太家去了。
她的汽车一发动,我就坐了起来。从我的卧室,可以看见琳达的房子,我看到她家的灯全亮着,只有门廊的灯关着。天色很黑,没有月亮和星星。我穿上长裤,在睡衣上套上一件毛衣,向楼下走去。
下了一半楼梯,我就知道自己真的病得很厉害,我全身发抖,走路摇摇晃晃,头一阵阵地犯晕,不得不抓住楼梯的扶手,以免摔倒。
还有一件事不顺利。我本来打算大功告成后,回到屋里,把我的外套和手套剪开,扔进客厅的壁炉里烧掉。但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妮娜的剪刀,后来我才想起,一定是妮娜带到金斯基太太那里去了。
更糟的是,壁炉里没有生火。我们家的中央暖气很好,我们生火只是为了添加一些情调,可是我在楼上生病时,妮娜没有去生火。那时,我真想放弃那计划了,可是,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我现在不动手,那么以后将永远不可能过两人生活了。
平常,我们把花园用的雨衣和手套放在后门边,妮娜只开了走廊上的一盏灯,我不敢开灯,就在黑暗中摸索穿上雨衣。雨衣似乎紧了点,我的身体湿漉漉的,很不灵活,但我还是勉强把扣子扣上,然后,戴上手套,取下一把厨房用的刀,从后门溜出去。那天晚上没有雾,不过天气仍然很潮湿。
我走过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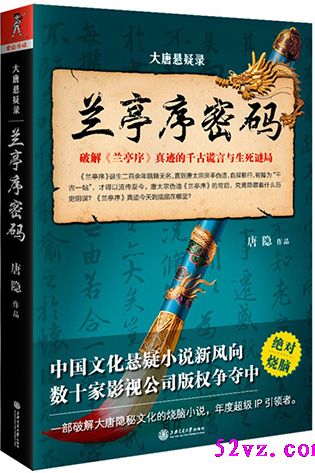
![囚鸟[gl悬疑推理]封面](http://www.cijige2.com/cover/57/5736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