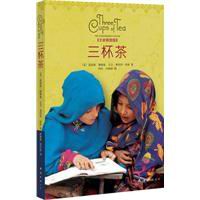三杯茶葛瑞格·摩顿森-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摩顿森感觉到有人站在他身边,抬起头,看见
一位高大男子的眼睛。男子的银色胡须修剪成学者样式,他带着微笑用帕施图语和摩顿森打招呼。接着他用英文说:“你一定是那个美国人。 ”
摩顿森激动地站起身跟他握手,却觉得天旋地转。过去四天里,越来越沮丧的他,除了茶和米饭,一直没吃其他食物。男子扶着他的肩膀把他稳住,然后叫人把早餐送来。
摩顿森一边吃着温暖的“恰巴帝”,一边弥补六天没说话的痛苦。他问起男子的姓名,男子停顿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就叫我卡恩吧。”卡恩是瓦济里斯坦地区菜市场的名儿,载他到瓦济里的司机也叫“卡恩”。
卡恩虽然是瓦济里人,却在白沙瓦的英国学校受过教育,满口当年学过的漂亮英文发音。他没解释为什么到这里来,但可以想见,他是被找来评估这个美国人的情况的。摩顿森把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工作描述给他,连喝了好几壶绿茶才把故事说完。他解释,自己想为巴基斯坦最穷困地区的孩子盖几所学校,因此到瓦济里斯坦来看看这里是不是需要
他的帮助。
摩顿森焦虑地等着卡恩的回应,希望听到这一切不过是场误会,自己很快就能回家,但他却无法从眼前身形壮硕的男子身上得到放心的答案。卡恩拿起《时代》杂志随手翻着,停在一页有关美军的广告上,摩顿森立即产生了一种危机感。卡恩指着一位在操作战地收音机、身穿迷彩装的女兵,对摩顿森说:“现在你们美国军队都送女人来打仗,是不是?”
“一般来说并不会。 ”摩顿森回答,努力搜索着更好的词汇和说法。
“但我们国家的女性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他发现即使是这样的回答,都含有冒犯的意思。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想找些可能让他们产生共鸣的话题。
“我的妻子很快要生下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卓一’,儿子。 ”摩顿森说,“我得回家迎接他的到来。 ”
几个月前塔拉曾经做过透视,摩顿森见过模糊的照片,知道即将出生的是个女儿。“但我知道对穆
斯林来说,第一个儿子出生是件大事。 ”摩顿森事后说,“说这个谎让我很难过,但我觉得如果告诉他们我儿子要出生了,他们有可能因此放我走。 ”
卡恩继续对着美军的广告皱眉,仿佛压根儿没听到摩顿森说话。“我已经告诉妻子我会回家。”摩顿森恳求着,“我想她一定非常担心,我能不能打电话告诉她我没事?”
“这里没有电话。”自称卡恩的人回答。
“你能带我到巴基斯坦军队的岗哨吗 ?我可以从那里打电话回家。 ”
卡恩叹了口气。“恐怕那不太可能。”他直视着摩顿森的眼睛,一抹逗留的眼神暗示了他不能自由表达的同情。“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收拾茶具准备离开,“你不会有事的。 ”
到了第八天下午,卡恩再次来看摩顿森。“你喜欢足球吗?”他问。
摩顿森飞快地思考这个问题潜藏的危险性,最后判断危险应该是零。“当然。 ”他说,“我在大学时也打球。 ”当他从美式英文转换成英式英文时,才想
到卡恩指的应该是英式足球,而不是美式足球即橄榄球。
“那么我们可以请你观赏一场球赛。 ”卡恩招手示意摩顿森走到门边。“来吧。 ”
他跟着卡恩走出没上锁的前门。走进宽阔的空地时,他感到有些晕眩——这是一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观察监牢周围的环境。
在一条往下走的碎石路尽头,从一栋清真寺尖塔旁边,可以望见公路把河谷分成了两半。比较远的那一边,大约一公里多一点开外,就是巴基斯坦军队的岗哨。摩顿森心里闪过逃跑的念头,但立刻想起了枪楼上的狙击手。他顺从地跟着卡恩爬上山,到达一处宽阔的岩石平地。在那里,他惊讶地看见二十多个大胡子年轻人熟练地踢着足球,奋力想把球踢进空军火箱做成的球门。
卡恩客气地将他带到球场边一张白色塑料椅坐下。摩顿森认真观看比赛,球员们踢起的阵阵尘土,沾到两人湿透的夏瓦儿卡米兹上。突然间枪楼传来一阵叫声,哨兵看见巴基斯坦军队的岗哨上有动静。
“真是对不起。 ”卡恩说着迅速把摩顿森带回高墙里。
那天晚上,摩顿森辗转反侧,始终睡不着。从卡恩的举止和别人对他的尊敬程度来看,卡恩很可能是个新上任的塔利班指挥官。但这对自己有什么意义?观看足球赛是不是他很快会被释放的迹象 ?或者是处决他之前的最后一根烟 ?
凌晨四点钟,他们再度到小囚房带摩顿森出去的时候,他得到了答案。卡恩亲手给他系上眼罩,在他肩上披了件毯子,客气地领着他的手走出去,坐进载满了人的卡车。
“那个时候,在‘ 9·11’之前,把外国人斩首并不普遍。”摩顿森说,“虽然我觉得被射杀不算是太糟的死法,但想到塔拉将要独自把我们的孩子带大,而且可能永远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就难过得发疯。我可以预见她永无止境的痛苦和怀疑,那是生命中最可怕的情形。 ”
卡车上的风很大,有人给了他一根烟,但是他回绝了。他不想再保持客气的形象,烟味儿也不是他想留在口中的最后味道。卡车开了半个多小时,
摩顿森拉紧毯子,还是忍不住浑身发抖。卡车转下一条泥巴路,驶向密集的开火声响时,他整个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司机踩下刹车,卡车滑进了震耳欲聋的巨大枪声中,那是几十支 AK—47步枪自动连发的结果。卡恩解开摩顿森的眼罩,推推他的胸膛。“你看,”他说,“我告诉过你船到桥头自然直,万事会有最好的结果。 ”越过卡恩的肩膀看去,几百名高大蓄胡的瓦济里人正围着营火跳舞,一边朝天空开枪。从他们被火光照亮的脸上,摩顿森惊奇地看到了欢喜,而非嗜血。
和他一起坐卡车来的人们欢呼着跳下车,朝天空一阵乱开枪,就加入热闹的人群。天应该快亮了,摩顿森看到营火上煮着热腾腾食物的大锅和烤着的羊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边喊,一边跟着卡恩走进狂欢的人群,不太相信八天来经历的危险已经奇迹般地结束了。“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
“我最好不要告诉你太多。 ”卡恩也大喊着回答,
企图盖过枪声。
“就是说我们曾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有些争执,可能让我们有大麻烦。但‘支尔格’(长老会议)把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现在举办庆祝会,庆祝送你回白沙瓦的宴会。 ”
摩顿森仍然不太相信他,但一把卢比钞票被塞进了他的口袋,他终于相信苦难已经结束——那位额头上有子弹擦伤的守卫踉踉跄跄走向他,笑脸泛着营火和大麻的红光,他挥着一叠脏兮兮皱巴巴的粉红色卢比钞票,一股脑儿塞进摩顿森夏瓦儿的胸前口袋里。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摩顿森,转向卡恩寻求解释。“给你的学校 !”他对着摩顿森的耳朵喊,
“所以,如果安拉愿意,你可以盖很多很多所 !”
另外几十位瓦济里人也暂时停下来,上前拥抱摩顿森,有的给他带来冒着烟的烤羊肉,有的同样捐了一堆钱。天放亮时,摩顿森的肚子和夏瓦儿口袋都胀得鼓鼓的,八天来紧紧压在胸口的恐惧终于弭平了。
满目晕眩之际,他也加入了庆祝的行列。羊肉
的油脂从他长了八天的胡子上滴下来,摩顿森跳着原以为早已遗忘的坦桑尼亚舞步,周围的瓦济里人大声喊着给他助兴。他在狂喜中舞着,放纵地舞着——为那失而复得的自由。
十四平衡
看似生与死间的对立,已被砍断。不要攻击或刺戮或逃逸,不再有限制或被限制。一切都融入灿烂无垠的自由中。
——《格萨尔王传》
一辆样子奇怪的小型车停在摩顿森家的车道上,溅满泥巴的车体几乎看不出底漆的颜色。特制车牌上写着“婴儿捕手”。
摩顿森走进舒服的家里,惊喜地发现这间宁静的老房子竟然属于自己,每当回家时这种感觉都要出现一次。他把从市场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里头有一堆塔拉想吃的东西,新鲜水果,还有三四种不同口味的哈根达斯冰激凌。然后转身上楼
————————————————————————————————————
找妻子。
她在楼上的小卧房里,一位身材高大的妇女在身旁陪着。“亲爱的,萝贝塔在这里。”塔拉卧在床上对摩顿森说。
摩顿森印象中娇小的妻子,现在像颗过熟的水果一样大了好几号。他在巴基斯坦待了三个月,才回到波兹曼一个星期,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他对坐在床边的助产士点点头:“嗨。 ”
“你好。 ”萝贝塔有点儿蒙大拿口音。她对塔拉说:“我会向他解释的。 ”接着又转向摩顿森:“我们刚才在讨论要在哪里生产,塔拉说她希望就在这里,这张床上,迎接你们的宝贝女儿,我也同意。这个房间有种平静的力量。 ”
“我没意见。 ”摩顿森握住塔拉的手。他说的是实话,做过护士的摩顿森很高兴让妻子尽可能远离医院。萝贝塔给了他们电话号码,要他们在阵痛开始时立即打电话给她——无论几点钟。
接下来的几天里,摩顿森一直小心翼翼地陪在塔拉身边,弄得塔拉有点儿烦了,最后只好叫他到
外头散步去,她才能好好睡午觉。经历过瓦济里斯坦的事,波兹曼的秋色美得让摩顿森觉得如同置身幻境。他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步,两旁是迷人的树林,公园里还有大学生在跟狗儿玩飞盘,这是他八天囚禁生活的最好解毒剂。
摩顿森被安全送回白沙瓦旅馆,口袋里塞满了瓦济里人捐的卢比钞票,总数接近四百美元。他带着塔拉的照片去了电信局,一边看照片,一边拨电话给妻子。因为时差的关系,美国这时正是午夜时分。
塔拉还醒着。“嗨,亲爱的,我没事儿。”电话里都是杂音。“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 ?”“我被关了几天。 ”“什么意思,你被谁关起来了,被政府吗 ?”塔
拉紧绷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很难解释。”他不想让妻子更担心,“不过我就要回家了,再过几天就能看到你了。 ”在转了三班飞机的漫长航程中,他不停地把塔
拉的照片从皮夹中拿出来,久久凝视着她,让她的面容抚平他受创的心灵。
在蒙大拿的塔拉也从担忧中恢复过来。“头几天没有葛瑞格的消息时,我想,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但是他足足消失了一个多星期,把我急得不行。我不断跟母亲说,想打电话到国务院去,葛瑞格身处封闭的地区,要是他出了什么事,很可能演化成国际事件。我觉得自己非常脆弱孤单,人又怀孕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惊慌和恐惧,我当时大概都经历过了。他终于打来电话时,我已经开始强迫自己为他不幸遇难的消息做心理准备了。 ”
1996年 9月 13日早上 7点,距他们在费尔蒙饭店邂逅刚好一年,塔拉的第一次阵痛开始了。
7点 12分,阿蜜拉·伊莲娜·摩顿森降生了。“阿蜜拉”在波斯语里是“女性领袖”的意思;而“伊莲娜”则是乞力马扎罗山区的部落语,意思是“神的礼物”,这也是为了纪念摩顿森钟爱的小妹克莉丝塔·伊莲娜·摩顿森。
助产士离开后,摩顿森侧卧在床上,紧紧拥抱着妻子和女儿。他把哈吉·阿里给他的七彩“托马尔”挂在女儿的脖子上,然后笨拙地试着打开这辈子的第一瓶香槟。
“我开吧。 ”塔拉在一旁看得直笑,把女儿递给摩顿森,接过香槟。橡木塞“砰”地一声跳开,摩顿森的大手轻轻盖在女儿柔软的小头上,心中满溢着幸福,满到让他热泪盈眶。那间充满煤油味儿的囚室,和这一刻幸福舒适的卧房,还有门外林木扶疏的街道,这一切,竟然都属于同一个世界。
“怎么了?”塔拉问。
“嘘。。”摩顿森伸手抚平妻子皱起的眉头,然后接过一杯香槟。“嘘。。”
从西雅图打来的一个电话,仿佛验证了那句话 ——“有生必有灭”。吉恩·霍尔尼想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科尔飞学校完工的照片。摩顿森告诉他自己被绑架的经历,说打算再多待几个星期,好好认识一下自己的女儿,然后再回巴基斯坦。
霍尔尼对学校建设进度十分不满,显得毫无耐
心,摩顿森忍不住问他究竟为什么如此心烦。霍尔尼一开始还怒气冲冲,最后终于透露他患了骨髓纤维化症——一种致命的白血病,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
“我必须在死前看到学校的照片。”霍尔尼说,“答应我,尽快把照片带给我看。 ”
“我答应你。 ”摩顿森的喉头哽住了,他为这位坏脾气的老人悲伤。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把如此之多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身上,他必须全力以赴。
为了信守对霍尔尼的承诺,摩顿森只和家人相处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