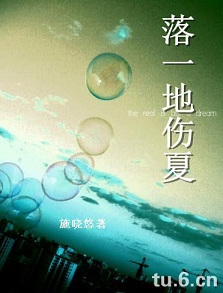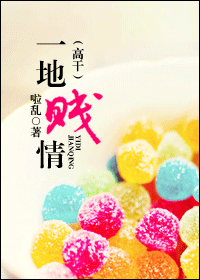一地烟灰-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边角落里的那位女同学问我采访过几次向她这样的美女,我的答案是:一次但没有成功。”话刚落音,讲堂里“哄”地一下子笑了起来。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她,把她脸看得一阵红一阵白的。
我看着她生气地起身离去,出门时还白了我一眼。心里“咯噔”一下,连话也说不连贯了于是匆匆结束了这堂讲座。等我出门的时候,女孩子已经不知所踪,一种莫名的失落爬上了我的心头。
第1卷 第六根 朝拜延安
四月底,P大组织全体大一学员赴延安考察参观。去之前我们只是以为窝在学校太郁闷了,出去玩玩,透透气是件美事,等到了那里,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一趟“旅游”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震撼。
我曾以为那里既然是他老人家带领革命先烈们跋涉了二万五千里最终落脚的地方,必定是个物产丰饶的风水宝地。当我真正踏上那寸草不生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坡,看到那穿着光板羊皮袄,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老羊倌,听到那破锣嗓子吼出的信天游,尝到那甜甜的酸枣和结实的小米馒头,心里竟然升腾起一种久违的感动。在这片浑浊的天地里,名和利都好似不再分明,每个人都优哉游哉的活着,所谓的幸福不过是酸汤饺子和砖垒窑洞。他们那慵懒的眼神,闲散的步伐,怡然自得的笑容让我们这群“城里来的学生娃”羡慕和惭愧。
四月底的延安依然是灰不溜秋,好像外面的春意盎然、繁华富足与它全然无关一般。宝塔山、延河、枣园、杨家岭、南泥湾三天的行程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一路上“骊山”大巴掀起的尘土像极了七十年前战场上弥漫的硝烟。我的耳朵里灌满了短促的冲锋号和凌厉的喊杀声;缺口的大刀,吃剩的皮带、身上取出的弹片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些躺在阵列馆的东西依然让我血脉喷张。
看着墙上的一张张的黑白照片,里面的每个人都衣衫褴褛却笑容灿烂,好像吃不饱穿不暖成天面对死亡的不是他们,二万五千里爬山涉水穿冰卧雪的不是他们;十年抗战趟过的枪林弹雨的也不是他们。是什么能让一个人变得执着勇敢和快乐?是什么支撑着一只队伍前赴后继概而赴死?是什么拯救一个民族于水火之中?我不禁想起“80后”的我们嗤之以鼻的两个词:“理想”、“信仰”。
“别跟我谈理想,戒了”如今这句话就跟当年“实现共产主义”的口号一样广为流传。这是一个让前辈们匪夷所思的年代,理想就跟泡泡糖一样,没事嚼它是幼稚的表现,而所谓的“信仰”早已连同大刀长矛被扔进了展览馆,每个人都现实的活着,更多的钱和更高的地位取代了“共产主义”成为我们一生不懈的追求,但我们再奢华富足的生活也无法填补精神的空虚,人们就像狗咬尾巴一样打着转儿狂躁地寻找着自己的幸福,即使筋疲力竭却也是徒擂功。
离开延安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待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人,不管他功成名就富甲一方还是处境卑微不名一文,都应该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看看破烂的窑洞,听听沧桑的信天游,让毛乌素沙漠的狂风涤荡自己沾染功利的灵魂。
回到学校,总编让我排一个延安之行的专版。投过来的稿子中,有一篇题为《朝拜》的文章写的特别流畅丰满,寥寥几百字就把高原的厚重和历史的深沉细腻的表现出来。读完这篇稿子,我特别想找这个名叫舒展的作者来交流一下。虽然我一贯以为上帝是公平的,但凡漂亮的女人,是写不出漂亮的文字来,就像漂亮的孔雀不会飞一样,但我还是决定会会这个文字优美的作者。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地方之后,我忐忑不安地在编辑部等着她的到来。
“报告”,“请进。”我故作镇静地慢慢抬起头,随即下颌半天没有顺利合上去。我曾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她的模样:酒瓶底眼镜、茁壮的眉毛、带雀斑的塌鼻子还有一笑就露出的闪闪发光的银色牙套可我从来没有想到是她。
“怎么是你?!”
“你抢了我的白呀,”她不屑地扬起头,“还以为是哪位编辑呢,早知道是你我就不跑这一趟了。”说完兀自笑了起来。我脸上马上红得发烫,很奇怪以前有小B他们撑着就一副情场老手的样子,现在单枪匹马还真是
“上次那事,实在是不好意思。”“哪次啊?”她狡黠地看着我,明知故问道。
“就是就是上次和几个战友看你玩笑的事啊。”我支支吾吾地辩解道,“你长得这么漂亮,男生找你搭讪是很平常的事啊。”
“男人搭讪的倒见过,但拿记者证搭讪的就你一个了。”格格地笑了起来,声音像风吹过精致的铃铛。我感觉我的脖子都要红了,“呃,不好意思,我就这件事向你郑重道歉,对不起。”“呵呵,这次算了,不过还有一次呢。”我想坏了,敢情这丫头是来报仇雪恨的。真后悔自己没事找事把她招出来,害得自己现在又是道歉又是泡茶,忙得晕头转向。
“唉,你找我来不会就是为了说抱歉的吧。”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让我猛然记起这一次会面的主题来。“对对对!”我拍拍头,从桌上拿起她那篇《朝拜》晃了晃,“这——是你写的?”“怎么?你怀疑我抄袭?”她有些得意地站起来。“不是不是不是!”我赶紧辩解道,“不好意思,我表达失误了,你知道——我一跟美女说话就紧张,一紧张就口不择言。”女孩扑哧一下笑了起来,看来恭维对每一个女生都是所用的。“你骗人,那次在图书馆前面,你都把人家忽悠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一听,刚要说话得嘴又张到那里合不拢了。气氛又一次陷入尴尬。
“呵,说说你怎么会怀疑不是我写的。”她善意打破这尴尬。我忙不迭接过话来阐述了“孔雀不会飞”的观点,并且顺带把她的稿子褒奖了一番,看得出她对我的戒备在一步一步转变为好感。“其实上学期我就认识你呢,你的那篇《情殇》在我们宿舍广为传阅,我还把它特地剪了下来呢。”我一听,那个兴奋劲盖都盖不住,看来,不仅仅是女人对恭维缺乏免疫力啊。接下来,我们索性放下报纸谈起了文学(这是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这个)她刚我说起了米兰•;昆德拉,说起了马尔克斯,说起了卡夫卡,听得我一头雾水。完了她问我看过拿些小说喜欢那些作家,我诚实地告诉她我看过的小说只有《鹿鼎记》和《》还有几本小黄书而认识的作家还没有手上的指头的多。她扑哧一下笑了起来,嗔责道:“你这个人就没两句真话!”我嘿嘿干笑着,心想哥们我多少年才讲一句真话,却没人相信,也够悲哀的。
我知道这文学是谈不下去了,就赶紧转换话题,我们从伊拉克战争谈到一中群殴事件,从中东油价谈到芬芳苑小炒,从普京总统谈到高中班主任卢SIR,为了不露馅我天马行空绝不在一个话题上多讲几句。看得出舒展兴致很高,整整一个小时她都毫无倦意。倒是我因为“三急”不得不想办法结束这场愉快的谈话。事实上在她来之前我就憋得难受了,苦苦支撑一个小时后我再也扛不住了。我抬起手腕作了个看表的动作。她敏感地反应过来,“哟,耽误你不少时间了,我得走了,再见!”〃嗯,有机会再聊。〃我故作轻松地站起来微笑着目送她离开。
在她出门的一刹那,我抓起茶几上的纸巾就往厕所冲。刚出门口就撞上了折回来的她。“怎么了?是不是落下什么东西?”我的表情已经僵硬扭曲。她吃惊地看着我,又看看我手里抓的纸巾,似乎明白了。“忘留•;•;•;你电话了•;•;•;”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我顾不上那么多,扬起纸巾就张牙舞爪朝WC冲去,边走边背着:“135•;•;•;•;•;•;”酣畅淋漓之后,我意识到在她面前我又丢大了一回。果然,过了一会儿,就收到她的短信:“嘿嘿,不好意思啊!不知道你有这么急的事。”后面跟了一个没心没肺的笑脸。我回道:“幸亏你问的是电话号码,要是身份证号,那就惨了。”
周一的时候报纸出来了,那篇《朝拜》四平八稳地放在专版头条的位置。接下来的反响很不错,连离退休的老干部都打电话过来夸了几句,说是看到这些就让他们回忆起那金戈铁马的岁月。这把总编兴奋得像嗑了药一般。他抓着我的手说有内涵有特色有水准,还要给我请功评先进,我也像生了个乖巧听话考试拿第一的孩子一般充满了成就感。老实说,报纸好看不好看关键在稿子,我只是个做包装的,万万不敢邀功。我给舒展打电话表示感谢,她却高兴地说要请我吃饭,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发表文章,用行话说就叫处女作。我坏笑着说:“好啊,你的处女作由我编辑。太荣幸了。”她说:“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乐不可支地赶紧放下电话。
在P大请客吃饭无外乎就是“芬芳苑”,我和舒展刚找个地坐下,就看见猪头和薇薇在对面桌上扬手示意。我带着舒展过去打了个招呼。“我介绍一下。这是猪头,这是猪头夫人,薇薇。”猪头笑着说:“冯子。现在不再是单身了,要积点口德啊。”说完坏笑着地看了舒展一眼,看得她脸刷地一下绽开出两朵艳丽的桃花。我介绍道:“这位是舒展,才女啊。”舒展腼腆一笑说:“怪不得人家叫你疯子呢。尽说不着边的话,我叫舒展,五系的。”“你好”,薇薇礼貌地打着招呼,却用挑剔的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着她,完了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觉到了气氛不大友好,就招呼道:“你们慢用,我们就不打搅了。”猪头嘿嘿笑道:“冯子,第一次吃饭你可千万得慢用啊,要不就你那吃相会把人家才女吓跑的。”我拍了他头一下低声喝道:“看老子回去削你!”
我背对着他们坐下,舒展和薇薇刚好相对。菜上来后,我委屈着自己的辘辘饥肠尽量往斯文里整。半小时过去了,我的胃还像个球胆一样除了空气啥都没有。舒展笑着说:“看你垂涎欲滴两眼放光还扮个绅士的样子太难受了,放开吃吧,我不介意。”我自我解嘲道:“你看人怎么就这么准呢,真是一针见血啊。”“呵呵那是,我还看准了对面那女孩喜欢你。”“谁?”我惊愕地回头,刚好撞上薇薇的目光。我笑着说:“你就是经不得夸,没见人家有主吗。告诉你他们俩还是我撮合的呢。”
“相信我的直觉。绝对没错,她都往你这瞟了几十次了,”舒展凑过来压低了声音,“你不知道,她看我的眼神都透着股杀气呢,人家肯定把我当你什么人了。”我冲她阴阴地笑了笑,“要不,咱就依了她的想法?”“想什么呢你!”她举起筷子向我的头敲来,我闭上眼睛却把头伸过去,等了半天却没见它落下来。我缓缓地睁开眼睛端详着她,一片绯红从她的脸上洇开,散到了脖子和耳根。
我想,我是喜欢上这个姑娘了。
编辑部的工作日渐繁重起来,总编动不动就给我压担子,还美其名曰栽培我。本来学习对于我来说比吃药还难受,这下倒好,我算是找了个彻彻底底不学的借口。于是上课成了偶尔有空才干的活儿,即使上课,书包里也一般没有书本,只有厚厚一沓稿子。有一次上高数课,老师除了一道题然后点名道:“冯牧云起来回答。”我正忙着审稿,一看老师并不认识人就喊道:“冯牧云请了病假。”没想到老师来了一句:“那你起来回答。”课堂里哄地笑出来,我站起来低头说不会。“你叫什么?”我看着在旁边笑得最欢腾的猪头回答:“朱波(猪头大名)”猪头的笑容一下子冻住了,张开嘴留下一个惨绝人寰的表情。这位兢兢业业的老师说:“放学后冯牧云同志和朱波同志去我办公室一趟。”猪头当时的眼睛瞪到了前所未有的宽度,估计当时要谁在他后面使劲一拍,没准眼珠子就会骨碌一下子掉出来。
放学后,猪头追着我死缠烂打直到后来我允诺请他吃饭才作罢。进了办公室后我叫朱波,他叫冯牧云,俩人被高数老师批评教育了差不多一小时才告辞。“朱波、冯牧云。我记住你们了。”临走时老师留下一句让我们后患无穷的话。果然,以后上高数,老师特别喜欢叫我和猪头回答问题。每次叫到“冯牧云”,我都要连掐带拽才能把他弄起来,而叫到“朱波”,我总是威风凛凛站起来很干脆地回答“不会!”那感觉,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宁死不招的地下党员一样。课后猪头几乎是哀求道:“大哥,求求你行行好看点,这样下去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