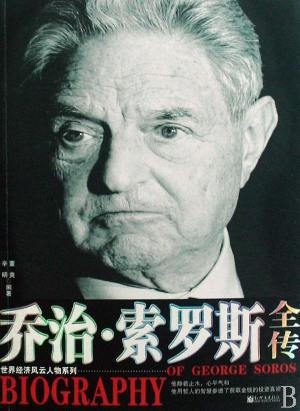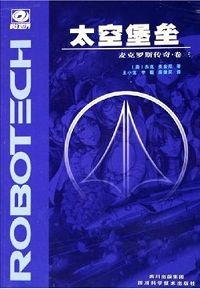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纳蒂在这个时期真正的政治忠诚似乎只是对哈亭顿。布雷特告诉哈亭顿,纳蒂、丘吉尔和张伯伦达成一致的,是“维护好(自由)统一党,而且您的愿望和意见似乎是他们全部考虑中最优先的因素因而根本的问题是,借用伦道尔夫的说法,‘不让格莱德斯通那帮人掌权。’”塔迪在3月份使用了一个真正的地主才会采用的隐喻,建议丘吉尔说,如果由统一党人发起或者支持的措施通过的话,他们应该知足:
哈亭顿不是乳臭未干的小孩,而且也没有失去他的羊群(意思是指他的支持者),他和乔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支持政府,都是跟稍后的《刑事法案》和《大额采购法案》有关。草场上还放养着几匹血统存疑的马,他们的老子有两匹或者三匹的种马都有可能(也就是在下院与相当数量的目的各异的赞助人有关的立法措施)。如果有人问我的话,我应该说,这些措施最早提出的人很难确定,但是其中之一肯定是乔。
当爱德华·汉密尔顿在8月份与纳蒂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哈廷顿马上就要当首相了,而且是真正的‘自由党’首相,尽管现在是所谓的保守党在做代表。哈廷顿不会再次被安排去做那些激进党人的脏活累活。他的忍辱负重已经超出了对党的忠诚感情”。而纳蒂披露了自己对张伯伦也越来越不信任,而在张伯伦自己的说法中,似乎那些自由党过去的宗派可以重新团结起来。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2)
对于张伯伦来说,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人物。他是披着托利党人羊皮的激进主义的狼。他是典型的民主主义者——一个大肆挥霍的沙文主义者——与丘吉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为后者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是一名很典型的皮尔派人士。而对于格莱德斯通先生来说,他没有任何机会——对最近两年甚至是两个月中自己心里想什么事情他从来都弄不清楚,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因此,一个像汉密尔顿那样对格莱德斯通派如此忠诚的人也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蔑视,对此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无法否认纳蒂“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所具有全面的知识”)。但是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汉密尔顿接下来的活动安排居然是与罗斯伯里在门特摩尔一起吃饭,而此时的罗斯伯里已经被看成是(最起码将会是)自由党人将来某一天在上院里的代表。
换句话说,他们所争论的话题事关自由党的命运,由哈亭顿牵着走向东,张伯伦拉着走向西,而罗斯伯里则处于两者之间,想着从格莱德斯通的沉沦中抢救点什么东西出来。当然,纳蒂想尽量把丘吉尔和哈亭顿调和到一个“真正的”自由党的标签下面的愿望,由于前者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而夭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统一党似乎还是有可能避免被保守党人一锅端的机会。还有就是为什么纳蒂要建议在1890年的大选中为哈亭顿提供自由统一党的竞选经费,而且鼓励德比爵士也这样做?不应该不切实际地像纳蒂在1888年所做的那样去推测,格莱德斯通已经被“适时地逐出了权力的舞台”,而且“随着格莱德斯通先生的离去,《地方自治法案》就会自生自灭”。甚至格莱德斯通在自由党获得1892年胜利后的政治反击,最后也都证明是短命的;而罗斯伯里的继任者也只能很谨慎地乐观,他必须时刻提醒他自己,对《地方自治法案》和上院的改革只可能是表面上的。
与政治家的关系
或许,纳蒂在19世纪8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党政治中的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远离作为一个银行家所应该关注的那些东西。或许我们可以说,一名罗斯柴尔德人首次以职业政治家的身份为了自身的利益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时,在他们对爱尔兰或者是社会政策的辩论与他们自己作为富裕的地主的利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联系。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时刻牢记在心,当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的时候,纳蒂仍然还是把他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花在纽科特,而且作为一个银行家,他最优先的政治考虑是对外的政策,而不是国内的政策。甚至就在我们探寻并且重建他在关于地方自治的辩论中的作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记住其实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角度。罗斯柴尔德家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们的政治关系来影响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解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是考虑他们在后迪斯雷利时代与两位政治家的关系。他们与这两位的关系最为密切——伦道尔夫·丘吉尔和罗斯伯里。而且有必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帝国属地中最为重要的地方:印度。
在1880年之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印度没有太多的兴趣,尽管他们与在那里的公司有些业务。当他们的亲戚加布里埃尔和莫里斯·沃尔姆斯在丧失音信25年之后,于1865年从塞伦回来的时候,夏洛特不仅被他们的外貌——“苍老、猥琐的英国高加索印度人”所震撼,同时也被他们描述的茶叶种植生活所迷住。那些赤身裸体的苦力,闷热、蛇、大象、豪猪、吃珍珠的昆虫,仿佛就像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球的事情;沃尔姆斯把他所拥有的一个种植园叫做“罗斯柴尔德”,只是一种赞誉,并不是说明这个家族在拉吉有经济方面的参与。然而,在1880年之后,这一切都变了。1881~1887年间,夏洛特的儿子们负责为印度铁路发行股票,价值总计640万英镑。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3)
自由党的下台以及丘吉尔被萨利斯伯利爵士在1885年夏天任命为印度国务卿,似乎预告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印度的兴趣开始萌发。与他整个短暂而辉煌的政治生涯相矛盾的是,丘吉尔正刻不容缓地在印度事务上与纳蒂和他的兄弟们建立起一种跟他早先谴责过的格莱德斯通政府与巴林家族为埃及事务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在计划为印度中部铁路发行筹款债券的时候,丘吉尔特别告诉总督都费尔林爵士:“如果明年我还在位当这笔贷款提出来的时候,我将会打一场针对贝特拉姆·居里的大战,把这笔贷款交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手里,因为他们的金融知识在英格兰银行都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渊博,而且他们的委托人简直难以计数。”
丘吉尔的传记作者罗伊·弗斯特认为,发行新铁路股票确实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了帮助。当时的人们也认为,丘吉尔决定吞并缅甸——在1886年元旦宣布——也与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日渐亲密有关。正如爱德华·汉密尔顿所讥讽地评论的:“沙文主义越来越流行,因为它能产生利润。”理所当然地,在宣布吞并后的一周时间里,他们要求取得“缅甸的所有铁路,并把线路延伸到边境”,丘吉尔向萨利斯伯利保证,那些说法都是“一派胡言”。事实对此作了证明:在1889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负责成功发行了巨额的缅甸宝石矿的股票——当时的认购者人数是如此之多,甚至纳蒂都被盛传只能通过梯子才能爬到他的银行办公室,而且股票的升水高达300%。难道布雷特没有在1886告诉哈亭顿说“丘吉尔和纳蒂、罗斯柴尔德在张伯伦的协助下联手领导着帝国的业务”?难道汉密尔顿后来没有对罗斯伯里评论说让张伯伦“深陷困境”的是他与“某一家金融企业”的“过从甚密”?难道萨利斯伯利夫人没有在与赫尔伯特·冯·俾斯麦和罗斯伯里的谈话中大肆谴责“伦道尔夫,说他把所有的事情都通报给了纳蒂·罗斯柴尔德”,而且“暗示说没有人会无缘无故为那些金融大鳄提供政治消息而不为所图”?过度亲密的关系的证据似乎是很令人瞩目的,特别是考虑到丘吉尔个人金融状况不是十分稳固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了解的——尽管丘吉尔早期的传记中掩盖了这个事实——他去世的时候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的债款“高达惊人的66902英镑”,虽然他曾经听从罗斯柴尔德的建议,投资矿业股票也赚了些钱。
然而,经过更加仔细的观察发现,丘吉尔在印度办公室和财政部中有限的能力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银行业务中所能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是有限的,而且同样的,他们作为丘吉尔的银行顾问对丘吉尔的重要性也是在他离职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缅甸宝石矿所发行的股票只是区区30万英镑,而且是在丘吉尔结束他短暂的印度办公室任期后4年才正式发行。一直到1896年,罗斯柴尔德家族才发行了200万英镑的缅甸铁路债券,他们在10年前首次接触印度金融委员会的时候则吃了闭门羹。在萨利斯伯利第二届政府的财政部,丘吉尔征询过他们对金融政策的意见(任命纳蒂进入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去质询公共开支)。但是,很难说清楚丘吉尔的那种自我毁灭和极端格莱德斯通式的对军费开支的反对,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有利于罗斯柴尔德的利益,事实上,丘吉尔对埃及和货币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与纳蒂产生了分歧。罗斯柴尔德家族跟他在1886年12月份那次非常关键的辞职决定也没有关系。当勒景诺德·布雷特询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纳蒂的时候,丘吉尔说“不要,因为他正在生艾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的气,后者显然发表了反对他的言辞激烈的谈话。‘他抱怨说我没有征询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意见。无论如何我都很高兴把他们当朋友,但我不是雷伍尔斯·威尔逊,而且也没有领他们的工资’”。对纳蒂来说,丘吉尔的辞职只是“闹情绪”,尽管丘吉尔自己坚持说是“一次单纯的误判他不知道萨利斯伯利已经‘早就备好了王牌’,换句话说,他早已准备好任命高森来补这个缺”。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4)
相关的资料表明,只是在他离开了这个职位之后,他才开始向罗斯柴尔德家族大量地借钱:截至1888年,他的债务只是900英镑;但是到了1891年,就膨胀到了11000英镑。尽管纳蒂继续鼓励丘吉尔相信自己还很可能会在某一天回到政府里,但是考虑到这位前财政部长越来越古怪的表现,他不大像是相信这样的说法。按照爱德华·汉密尔顿在1888年8月说的:“R·丘吉尔所有的东西都向罗斯柴尔德要但是作为他的主要财务顾问,罗斯柴尔德已经把他看成是毫无希望的政治家,而把他抛弃了。”事实上,把纳蒂在1886年之后对丘吉尔的资金支持当成是一项本质上的友谊之举,就像梅毒冷酷地拿走它应得的部分一样;因为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丘吉尔现在更多的是负债而不是资产。这门锈蚀的大炮在1891年的时候再次开火,当时丘吉尔从一次由罗斯柴尔德资助的到马希侯诺尔兰德的探险中归来,但只是报告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前景——这让纳蒂大为光火,就像我们将在下文中看的一样。更多的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出于对可悲的丘吉尔的同情,促使罗斯柴尔德更多地关注他雄心勃勃的儿子,他们对年轻的温斯顿1904年时以一名代表曼彻斯特的自由党议员的身份反对《外侨法案》时无疑觉得相当满意。
罗斯伯里的情况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尽管关于罗斯柴尔德影响程度的类似问题再次冒头。这个在格莱德斯通的第三和第四个任期中出任外交部长并且在1894年接替他出任首相的人娶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政治上是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正如像对待丘吉尔一样,当时有些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结合不好,”自由党的机关报《正义》在格莱德斯通于1893年9月访问了特灵之后发表评论说,“当外交部长通过婚姻与同样阴险的金融企业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与罗斯柴尔德爵士推杯换盏。”
毫无疑问,几乎从他娶了汉娜的那一刻起,家族中更加政治化的成员就开始对罗斯伯里的政治生涯更加关注。在1878年9月——也就是婚礼后的第6个月——费迪南德向罗斯伯里披露了这种关切的程度:
纳蒂与往常一样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而且竭力向我灌输你的追求和政治抱负。他希望知道,当自由党再次执政,如果给你比较低级的职务,你是否会考虑接受。我只能向他表示我对此一无所知。艾尔弗雷德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来了,而且似乎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他知道我们昨晚一起去看戏——废除宗教裁判所真的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的这些亲戚怎么都是一些喜欢刺探别人隐私的人啊!
在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