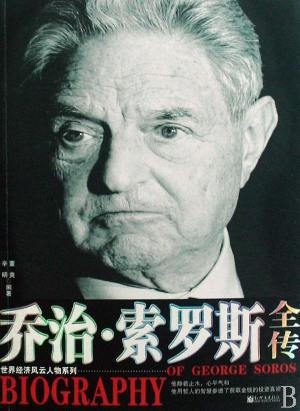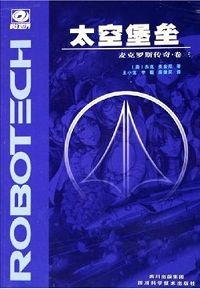罗斯柴尔德家族·四部曲-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号声一直响彻西奈半岛的时候别无二致”。他“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对自己族人的未来充满信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希东尼亚与迪斯雷利的相像程度远甚于列昂内尔,因为他说他出生于西班牙的马拉诺——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他们表面上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的宗教——而且迪斯雷利喜欢幻想自己的家族是西班牙系的犹太人。但余下的绝大部分很显然来自罗斯柴尔德的启发。因此,年轻时候的希东尼亚被“关在了大学和学校的大门之外,这些大学和学校对于学习以及先人的事业来说缺乏古代哲学的最初知识”。另外,“他的信仰使他不可能追求成为一个公民的理想”。然而,“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想法可以诱使他伤害自己种族的纯洁,因为他一直为此而备感自豪”而去与外族通婚。只有当希东尼亚阐述对自己种族的看法时,迪斯雷利才接替了列昂内尔:
希伯来人是一个没有被混杂的种族组织没有被混杂的种族是大自然的贵族在广泛的旅行中,希东尼亚拜访而且检视了整个世界上的希伯来人社区。他发现,总体上看,较下等的阶层情况比较差,而上层人士沉浸在对肮脏事物的追求中;但他发现知识的发展没有受到破坏,这给了他希望。他被说服相信组织能经受住迫害的考验。当他反省他们所经受的那些磨难的时候,发现种族居然能够幸存下来,这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管过了多少个世纪,遭受了多少个世纪的谪贬,犹太人的思想对欧洲事务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不用提他们的法律,这些法律你们还在遵守;不说他们的文学,这些文学滋润着你们的思想;我只说说活生生的希伯来人的才智。
然而,就算在这里,罗斯柴尔德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当迪斯雷利想办法说明他关于犹太人影响力程度的观点时,他非同一般地直接取材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最近的历史,他通过希东尼亚的口说:
我刚才告诉你说我明天准备去金融城里,因为我一直遵守这样的规矩,当国家事务还在考虑的过程当中时,我会积极介入。否则的话,我从不干预。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很多战争与和平,但是我从来不会惊慌失措,除非有人通知我,统治者想要更多的财富
返回到几年以前,俄国向我们提出过要求。现在圣彼得堡朝廷和我们家族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他们有荷兰的关系,这些关系基本上可以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我们对波兰希伯来人这个人口众多,但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也是所有部族中最多的民族的支持举动,对于沙皇来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是与罗曼诺夫家族的关系出现了好的转机。我因此决定亲自去一趟圣彼得堡。抵达后,我与俄罗斯财政部长康可林伯爵举行了一次会谈;我见到的是一位立陶宛犹太人的儿子。我们所讨论的贷款与西班牙的事务有关,我决定从俄罗斯到西班牙去着手解决。我与西班牙部长塞诺尔·门迪萨伯尔(SenorMendizable)原文如此。一到就马上有了一名听众,我见到的是一位像我一样属于新教教徒的阿拉贡犹太人的儿子。在马德里做完这一切之后,我直奔巴黎,拜会法国国会的议长,我见到的是一位法国犹太人的儿子(据推测是苏尔特)。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7)
因此,您看,我亲爱的科宁斯比,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那些人士与那些不了解实际幕后真相的人所想象的完全不是一伙人。
撇开迪斯雷利认为所有这些显赫人物都是像他们一样的犹太人的臆想不谈,一个确凿无误的事实是这段描写的灵感来自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迹。
他还明确提及犹太人在政治上被“当成平等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而列入了同样的阶层,随时准备支持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和财产的政策,而不是驯服地在一个试图降低他的人格的制度下苟延残喘。托利党人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一场重要的选举,出来投票反对他们的正是犹太人然而犹太人科宁斯比从本质上说是托利党人。托利主义事实上只是抄袭了那些把欧洲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强大的势力”。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汉娜喜欢这本书。正像她在写给夏洛特的信中说的:“经过对希东尼亚身上所具有的民族高尚品质的认真研究,经过使用很多支持他们解放的论述,他很聪明地描写了众多我们似曾相识的事件,人物的刻画也很到位我已经给他写了张便条,表达我们对他的精神产品的赞赏。”
如果《科宁斯比》暗藏着对列昂内尔的歌颂,那么《唐克雷德》(Tancred)就是在歌颂他的妻子。对伦敦景物的描写再一次充满着对罗斯柴尔德的隐喻。我们参观了一次“西昆大院”,还去了希东尼亚豪华装修的房子。另外,还有一个明确的影射是希东尼亚为获得一条被称为“伟大北方”的法国铁路所做的努力。再一次,希东尼亚成了迪斯雷利理论的代言人——这个理论现在被用来重新定义基督教本质上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是犹太教的发展:
我相信(希东尼亚宣称)上帝在何烈山对摩西说过,而且你们相信他以耶稣的身躯在卡瓦利山上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至少在世俗的观念上看,两者都是以色列的子孙,他们用希伯来话对希伯来人讲。先知只有希伯来人,使徒也只有希伯来人。亚洲现在已经消失的众多教堂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罗马的据说要与世长存,而且现在改为信奉摩西和基督的教义的教堂也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起来的。
然而,是埃娃这个人物按照这些线索发表了最勇敢的宣言。作为一位叙利亚犹太人的公主,表面上看她的身上很难找到夏洛特的影子;然而,对她的外貌的描述显示她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某些模型。同样,尽管夏洛特的观点似乎不大可能带有埃娃的影子,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一点。比如,她具有罗斯柴尔德式的对异族通婚和变更信仰的深深的厌恶。“希伯来人从来没有与他的征服者融合,”她大声地说道,“不,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基督徒!”相似的,迪斯雷利所喜爱的主题——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本原——也在她的书信中有所表达。“你是那些崇拜犹太女人的法兰克人中的一员吗?”埃娃第一次(在圣地的一片绿洲中)碰到唐克雷德时问道,“或者是那些辱骂她的人中的一员?”她提醒他,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但他是一名犹太人,而你崇拜他。”因此“基督教界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犹太女人,另一半崇拜一位犹太人”。埃娃用另一个罗斯柴尔德式的句子询问唐克雷德: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8)
“欧洲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一座?”
“毫无疑问,我的祖国的首都伦敦。”
“那里最有名望的人是多么富有,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吗?”
“我相信他是一位跟您有着共同种族和信仰的人。”
“那么,巴黎呢?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
“我想是伦敦最富有的人的兄弟。”
“我对维也纳非常熟悉,”这位女士说,脸上带着微笑,“恺撒给我们的同胞封了帝国的爵位,因为,公正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分崩离析。”
迪斯雷利没有考虑夏洛特的地方是他设计好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很过分)辩论,说在“基督受难时提供牺牲和祭礼”方面,犹太人“完成了上帝仁慈的意愿”,而且“拯救了全人类”。她也没有接受他的说法(通过女巫的口):“基督教是完善后的犹太教,或者什么也不是要是没有基督教,犹太教也就不完整。”
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提出的这些争论,表明了迪斯雷利对罗素的限制权利法案的态度。他在第一次辩论前两周,告诉列昂内尔、安东尼以及他们的妻子,他准备好了要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对托利派的条款,“我们必须主张我们的权利,不是为了什么特权,而是为了良心的解放”。这使得围坐桌前的自由派人士不知所措:路易莎描写迪斯雷利用“他那奇特的唐克雷德似的条理”侃侃而谈,而且“怀疑他是否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对议会这样说”。他确实说了。夏洛特起初对此相当热心。“没有谁可以,”她在1848年3月告诉德莱恩,“在用伟大的机智权利、智慧或创造性来表达自己的方面超过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
批判“风暴”
迪斯雷利面临的问题是小说的销售情况相当糟糕,几乎是个灾难,而现实的政治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就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他和保守党领导人本庭克分道扬镳,并取代皮尔成为了托利党的领导人;然而在支持罗素法案的过程中,他们又面临前后排议席分裂的危险英国议会中的惯例:前排议席为反对党领导人的专座,而后排议席为普通议员席。——译者注。开始时他们似乎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陷入的麻烦程度会有多大。本庭克特别漫不经心,他在1847年9月告诉克罗克尔:
我相信我在投票时一直都站在犹太人一边。我说我相信,是因为我自己从来都不会费心去关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没有价值的事,而且很少关心我是怎样投的。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与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有多大不同,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当成是国家应该关心的大事我把犹太人事务看成是个人的事务,就像是巨额的个人财产或者是离婚法案像影响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对于保守党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可能会投弃权票,保持我自己一贯的支持犹太人的立场,但又不得罪党内的大多数人,我猜想这些人将会站在对立面。迪斯雷利当然将会热诚地支持犹太人,首先是由于以前先入为主的支持他们的印象,其次是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伟大的盟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人在个人特点方面都很高调,而且伦敦市已经选举列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作为它的代表之一,在公众声音方面是这样一种情况,因此我认为党作为一个党派继续与犹太人作对,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9)
至于说迪斯雷利,他在11月16日信心满满地向本庭克和约翰·曼奈斯保证:“风险不是很大,而且在明年之前也不会交锋。”
两人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事实上,只有另外两名保守党人在提案投票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米尔尼斯·加斯克尔和——很可能是一名转变了信仰的人——托马斯·巴林)。以那些顽固的守旧分子为首,比如罗伯特·英格里斯爵士,投反对票的不少于138人,使该党又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当迪斯雷利宣称那些用十字架钉死耶稣的人和在耶稣被钉死前跪在他面前的人之间没有差异的时候,我是否应该为他欢呼?”奥加斯塔·斯戴福特要求进行澄清。本庭克辞职,把他现在称之为“没有罗马天主教、没有犹太人党”的领导职位留给了史丹利爵士。这就很好地理解了为什么迪斯雷利随后在下院辩论时调整了自己的态度的原因:最重要的事情是,当时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一位人物从此以后好像“良心被狗吃了”,并没有悄悄地放弃他对恢复犹太人人权的全部支持。对于他的行为最常见的那些批评——特别是来自于夏洛特和路易莎的那些批评——是不公平的,因为迪斯雷利继续投票并偶尔还会站在他1847年时候的立场上发表讲话。一个无法宽恕的情况当然是他那段时间对列昂内尔的经济依赖避免了出现180度转变的情况,这是夏洛特一直都心存疑虑的。1848年5月还出现了另外一次她与玛丽·安娜之间的尴尬情况,因为玛丽·安娜谴责列昂内尔不回复迪斯雷利的信函。这些情况暴露了“她的丈夫还深陷在债务之中,正被放债人拼命追讨,哀求我的丈夫给予帮助和支持”。在两位女人再一次交锋之后,列昂内尔决定另外再借给迪斯雷利1000英镑。
皮尔派保守党阵营也出现了分裂。当罗素在1847年12月提出他的提案时,另一位表示支持的是皮尔派的一位刻板的高教会派被保护人格莱德斯通,他以前曾经是恢复犹太人人生权利的反对者。尽管他发现这个决定“很痛苦”(并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个事件可能迫使他离开国会的想法),格莱德斯通的逻辑还是相当严谨:下院已经接受了天主教、贵格教会、摩拉维亚人、独立派、一神教,地方政府已经接受了犹太人,因此,继续对犹太教国会议员进行限制就显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