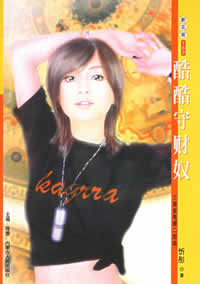霸主的男奴-第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浮白嘴角一勾,优雅叩杯,“缇绝,你需知,做任何事都需要代价的。当年我救你是,如今我救他也是。”
萧戎歌颓然放下剑,浮白想藏人没有人能找到,“我以问鼎阁为易如何?”
浮白摇首,“于陶浮沉而言,千万人不如一个萧缇绝。”
“你莫忘了剑凌和他的儿子还在我手中,你便算藏着他,终有一天他还是会回来!”
“他伤早已康复,若想回我能拦得住?”
萧戎歌如遭雷击,剧烈的咳嗽起来,嘴角很快便浸出血迹来。
浮白宽慰的拍拍他的肩,“戎歌,逢场作戏最后一次,只要你能杀了他,剑潇就是你的人。”
“你的人”三字深深触动萧戎歌的心,浮白怜伤的抚过他斑白的鬓发、唇边的血,“戎歌,你耗不起。”
患上咳血之症,命不久矣!
在死之前能再见他一面,受辱又何妨?他这一生受到的侮辱还少吗?“——好!”
陶浮沉这日在仕子楼宴请宾客,萧戎歌锦衣华服,镶珠带玉而至。极其俗气的打扮由他穿来却贵气无比,满堂宾客一时被眩住,半天回不过神来。
萧戎歌看向主位上年过不惑的男子,两鬓斑白、眼角含皱、体态微臃。近二十年不见了,那时他只有现在的剑潇这么大,自己只有当年的剑潇那么大。时光倥偬,一转眼少年竟白头。
陶浮沉举至唇边的酒盏“啪”得一声掉下,不可置信得看着迎日而立的男子,白日的阳光照在他满身珠玉上,使他整个人虚实难辩。
萧戎歌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站着,手里的折扇摇啊摇,眼里神色难辩。
陶浮沉如梦游般的起身步伐恍惚的走来,伸着手却不敢触摸他,似怕一触他的影响就消散了,“缇绝?……缇绝……”
萧戎歌桃花眼一眯,嘴唇微勾,如桃花笑春风。
无数个午夜梦回思念不已的笑,柔三分,媚三分,邪三分,纯真一分,“……缇绝,真的是你吗?”
“是我。”他声音极轻极缥缈,像朝歌夜弦的余音。
陶浮沉手颤抖的抚上他微白的鬓,瘦削的脸,“缇绝,连你也老了……”记忆中的那个少年像初春刚抽出的柳条,那么年轻。
“我以为你认不出我了。”
“怎么会?”然后像二十年前一样将他抱入怀中,竟不顾身边全是朝中大臣,不顾二十年前他差点因这个少年被废。
朝中大臣这才从惊怔中醒过来,年轻的脸羞得通红,年老的气得胡子直抖,接受男风的羡慕的眼红,不接受男风的觉得男人相恋竟也如此美好。
陶浮沉的管家识时务的提醒主子回府。萧戎歌与他同乘而回,浮沉才从迷糊中醒来,“缇绝,你竟活着为何不来找我?”
萧戎歌只是一笑,陶浮沉才想起他一向是厌恶男风的,在自己身边虽然恭顺却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自己,果真离开了又怎么会回来?那么,现在回来却是为何呢?
“当年你是如何逃生的?”
“陶浮白救了我。”萧戎歌毫不隐瞒的道,“也是我让他送得画像。”
陶浮沉眼里痛楚一闪,“那么,你这次……是为了他而来?”
“不。”忽然不忍说下面的话。陶浮沉虽辱他也救了他,一向对他甚好,以前他有恨,可自从有了剑潇以后他觉对陶浮沉升起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来。
都是爱而不得,爱恨不堪,同是天涯沦落人。
“缇绝,你从不会骗我。”
萧戎歌目光一瞬不瞬的盯着他,“他挟持了剑潇,我只有用你的人头才能换回剑潇。”
陶浮沉悲苦一笑,“原来你爱上了别人?原来你爱的是剑潇?你怎么能爱上男人?——缇绝啊缇绝,若是为了一个女人我可以将头送给你,可是你爱的为什么要是男人?你冒死离开我,就是为了爱另外一个男人?”
萧戎歌悲凉一笑,怜他又自怜,“如果能选择,你也不会爱上我。”
陶浮沉目光灼灼地看着他,“我只问你,这么些年,你可想过我一回?可爱过我一分?”
萧戎歌崭钉截铁的道:“不曾。”
陶浮沉悲伤而笑,手掌一下一下拍着自己的腿,脆响不绝,“缇绝啊缇绝,你从来都是说着最无情的话,做着最动情的事。你从不说骗我的话,却欺骗着我的感情!”
萧戎歌沉默不语。
浮沉忽然提住他的衣襟,眼神阴戾,声音粗重,“如果……如果……我让你陪我睡呢?”
萧戎歌身子一紧。
“陪我睡一夜,我便换他一命,如何?”陶浮沉步步逼近,眼与眼不过尺寸间的距离,因而萧戎歌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眼里的伤痛疯狂。
到底是跟了他两年,说话的语气,做事的方式都如此一般无二。萧戎歌禁不住苦笑,他身上的味道一如二十年前,有点清、有点苦,像是新剥的莲子。
“他剑潇可以用命换你的身子,我就不能用命换你的身子?”这些年他无关自己的活着,天下也有了,爱人也有了,可自己却什么也没有了!
“好!”萧戎歌干净利索的答应。
浮沉的脸顿时青紫了下去,“你真要为他这般?”
“我也曾这样侮辱过他,报应不爽。”垂目低讷,泪意隐隐,“老天连死都不让我们死在一起。”
浮沉松开他的衣襟,拊掌大笑,“缇绝啊,你跟了我两年,什么没学会,惟独将痴情与绝情学得一般无二。”
一杯酒饮尽抽出萧戎歌袖里的留白剑,以酒洗剑,长袖拂拭,“痴情送给了他,绝情留给了我。”
萧戎歌竟为他心里一痛,惭颜低语,“沉哥……”
沉哥?他又叫自己沉哥了?这么些年,他心里原来还记着自己是他的沉哥?足矣!足矣!
他俯身轻轻吻了吻萧戎歌的额头,一如当年般温柔怜惜,留白雪刃一闪,萧戎歌下意识的要抬手相阻,却终将没有动。于是留白雪刃便划破了陶浮沉的颈。
“缇绝,我强迫了你两年,相思了二十年,现在我不强迫你了。——我要你欠着我!记着我!”
眉眼一合,敛住这男子最后的样子:明眸皓齿,掩住珠玉之色;桃花修眉,成就绝世之姿。这些都不足以心动,心动的是那眼角的泪珠儿,如晨露盈盈欲坠。
——为君一滴泪,长笑竭此生。
缇绝!缇绝!
血流出脖颈,流过萧戎歌的五指,他神情呆愣地看着浮沉含笑闭眼,却有长泪一滴,从眼睑流下,沾湿的留白剑。
妾有容华无功过,空将涕笑两留白。影里风霜露里埋。
萧戎歌想起了二十三年前,武家。
那时他受不了武峻的折磨抱着流苏逃走,被武家家丁追上,准备跳水寻死的时候,陶浮沉出现了。不过弱冠之龄,衣着素雅却自有一股皇室矜贵。
浮沉斥住了家丁,然后蹲下身子,修长的手指拭去他脸上的泪和灰尘,“你叫什么名字?”
温润如玉的眼自有一分安定人心的力量,他惊恐在这目光下渐渐平息了,“……鶗鴂。”
浮沉彻眉沉吟了一下,“鶗鴂?数声鶗鴂,又报芳菲歇。……莫把弦拨,怨极弦能说。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可是取自这首诗?”
他摇摇头,还不懂诗,嚅嚅的道:“是杜鹃鸟的意思。”外婆说他出生的时候窗外有一只杜鹃儿在啼叫,因此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浮沉摸摸他的头,“便是这个意思了。”指着与他相依的流苏,“这是你妹妹么?”
“嗯。她叫流苏。”他见那些家丁看到浮沉就不敢行粗了,料想浮沉可以救自己,因为表现的十分乖觉,眨着泪意盈盈的眼睛,纯真无邪的问,“哥哥,你能救我们吗?”
浮沉的眼睛在那时闪过一抹怜惜与痛爱。多年来经历□□以后戎歌才明白,浮沉那时的眼神与当日自己看到剑潇一剑削去肩上腐肉时的眼神,定然是一样的。
浮沉蹲坐着将满身污垢的流苏抱在膝上,目光平视着他,“我会保护你们。”然后对武家家丁道,“让武炎来见我。”神情不怒自威。
他不知道浮沉是如何和武炎谈的,当武炎暧昧的看他一眼,兴高采烈的离开后,浮沉蹲下身怜惜的揉揉他的脸,“以后这里便是你们的家了,喜欢这里吗?”
他看着浮沉温和善良的眼睛,认真的点点头,“喜欢。”
浮沉也笑了起来,如春风拂面,“我叫陶浮沉,你以后就叫我沉哥可好?”
他软软的声音糯糯的叫,“沉哥……”
浮沉的眼一瞬迷离,然后抱起流苏,牵着他,“来,沉哥带你们去吃东西。”
此后他和流苏便住在这里,那时的他刚从武炎的魔掌里逃出来,时常会在梦里惊叫出来,很多个夜晚叫醒自己的不是侍伺自己的下人,而是浮沉。
推醒自己,声音如温和而有磁性的轻唤着,“鶗鴂,醒醒,鶗鴂……”
醒来时头上的汗已被浮沉用丝卷擦干净,小心翼翼地将他揽在怀里,“不怕。沉哥在不怕……”
浮沉身上的味道是清苦的,却极是安人心神,很多时候他便在浮沉怀里睡着,迷迷糊糊间似有什么温热的东西在自己额头滑过。
现在想来那不是浮沉替自己擦汗的手指,而是他的唇。——他也曾偷吻着自己,一如自己曾那么绝望痛苦的偷吻着剑潇。
爱情有时候真的会轮回的,你怎么对别人,别人就怎么对你!
怕他孤单浮沉特意送他去私塾读书,小孩子的记忆长久也短暂,他渐渐的从自闭中走了出来,和孩子们融入一起。跳房子、打陀螺、玩溜溜、捉迷藏……
很多次他课间玩耍时,感觉有人在看着自己,一回首便对上他幽深地有些异样的眼眸。对上他的眼睛后渐渐收起幽深,温和一笑。
偶然有暇的时候浮沉也会陪他们一起玩,微笑着看他耍赖、不讲道理,纵容着他打架欺负人。
浮沉从未不允许他打架,只是每次他被大些的孩子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浮沉总是不顾脏乱将他揽在怀里,修长的手指弹落他身上的灰尘,拿出药膏小心至极的为他擦药。
那一次他和小伙伴们玩着堆沙城,他将“旌旗”占在别人的城墙上时,浮沉过来了,蹲在雄赳赳、气昂昂的他身边认真的问,“鶗鴂喜欢打仗?”
他年少轻狂的道:“我要让他们的地盘都成为我的!”
“鶗鴂想要天下么?”
“想!”
那时他看到浮沉一惯温和的眼里忽然便有雄心万丈,然后握住他的手,一字一顿的道:“鶗鴂,我会将这江山送到你面前!”
那时候戎歌笑了,他不知道自己笑什么。只是那天后他在浮沉的书房里看到这么一副字画。
——江山拱手,为君一笑。
此后浮沉没有再让他去私塾,亲自教他读书习字,很多时候他从书坐上抬起头的时候,就见浮沉拿着笔眼神迷离的看着他,墨浸染了书卷也不知晓。
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问,“沉哥,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浮沉摇了摇头,然后似喜似悲、似怅似苦的叹息,“鶗鴂,你长大了呢。”
这半年来浮沉着意让人替他调理身子,他长高了些,也不似以前那般削瘦,渐渐有少年人的青春英姿。
“我长大了要为沉哥打江山!”他已知道浮沉是太子,在皇子众多的皇室要真正登上皇位还需拼打,这是他唯一能报达沉哥的。
浮沉眼神又是一阵迷离,招招手让他过去,怜惜的抚摸着他的头,“打江山是需要流血的,鶗鴂,沉哥不想让你再看到血。”每每听到他梦里凄惨恐惧的呼叫他都心痛不已。
他那时的眼光异常坚定,“鶗鴂也不想看到沉哥手上染血,所以要替沉哥打江山!”
时至今日,他依然不想看到被自己浑身泥垢染脏的白衣上染上血,可是他终究还是染上血了,不是别人的血,是他自己的!
浮沉没有说话,沉吟半晌后终于一伸臂将他抱在腿上。他那时觉得这抱与平日有所不同,可究竟哪里不同他也不知道。
浮沉将手中笔递于他,“来写写你的名字给沉哥看。”
他便在纸上写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字,——鶗鴂。
浮沉看了半晌,然后长叹,“我的小鸟儿翅膀长硬了,何时飞走了如何是好?”在纸卷上写下“缇绝”二字,“以后叫就这两个字可好?”
“为什么?”改这两个有何意呢?
浮沉当时沉吟未语,现在想来其实是怕他飞走了吧!那一抱的不同他也明白了,因为除了爱以外,还带着欲。
那天晚上浮沉第一次允许他喝酒,并陪着他喝酒。
绿酒初尝容易醉。他喝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浮沉抱着他,缠绵悱恻的问,“缇绝喜欢沉哥么?”
“喜欢。”他单纯的回答,全未将浮沉与武炎联系起来。可是浮沉却做了和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