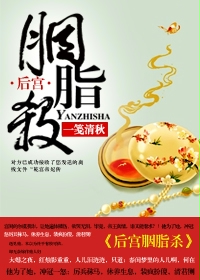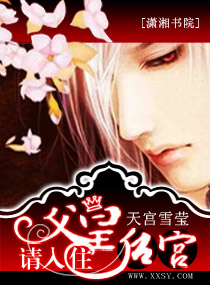后宫如懿传4-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惢心答得行云流水,想是细细查问过了。如懿微眯着眼,有一种细碎的光凝成疑虑的波彀,在她的眼眸里流过:“你告诉了玫嫔为她孩子超度善后之事,她要见本宫言谢,那也算情理之中。可去启祥宫这便奇怪了,没头没尾的,去做什么呢?”
惢心揣度着道:“奴婢想着,玫嫔小主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娘娘替她了结了她孩子的事,她自然要谢娘娘。且说来玫嫔小主也够委屈的,一辈子的苦楚说不得言不得,不能说出口一句,怕许多事许多话,一辈子也要烂在自个儿肚子里,带到地下去了。”
惢心说者无心,如懿的太阳穴突突地跳着,像是被一根银针挑动了最痛楚的神经,她哑声道:“是金玉妍!一定是金玉妍!孝贤皇后的七阿哥莫名染上痘疫离世,玫嫔说是她自己做下的,可是她只是一个嫔位,哪里有能力做到这样左右逢源,天衣无缝!只怕,是因为她想着临死前谢了所有该谢的人,就像她一定要见本宫一般。所以所以”
惢心一步上前,紧紧扶住被怒火与恨意烧得灼痛的如懿,隐忍着道:“皇后娘娘,如果孝贤皇后临死前的话是真的,许多事她没做过,那么如今的事,真的很可能是嘉贵妃指使,若是连孝贤皇后的七阿哥都能死得无声无息,那这个女人的阴毒,实在是在咱们意料之外。”她越说越痛,情不自禁俯下身抚摸着自己伤残的腿脚,切齿道:“皇后娘娘,她能害了奴婢和您一次,就能害咱们许多次。”
如懿紧紧地攥着手指,骨节发出咯咯的脆硬声,似重重叩在心上,她的声音并不如内心沸腾的火,显得格外平静而森:“惢心,无处防范是最可怕的事,只要知道了是谁,有了防范,便不必再怕。”
惢心垂着头,懊丧道:“只可惜,嘉贵妃有李朝的身份,轻易动她不得,只是,不能除去这样的人,日日在身边,真是芒刺在背。”
如懿摇了摇头,将无奈躁郁之情深深摁入情绪的最底处,轻吁道:“即便我贵为皇后,许多事也不能如愿以偿,眼下能做的,也唯有如此而已。”
她在踏出殿门的一刻,最后望向玫嫔沉浸在死亡中显得平和的脸容,有一瞬间的恍然与迷茫;若有来日,自己的下场,会不会比玫嫔好一点点?还是一样,终身限于利用和被利用的旋涡之中,沉沦到底?
第十九章初老
玫嫔的丧礼办得极为草草,没有追封,没有丧仪,没有哀乐,更没有葬入妃陵的嘉遇,白布一裹便送还了母家。皇帝不过问,太后亦当没有这个人,仿佛宫里从来就没有过玫嫔,连嫔妃的言谈之间,也自觉地掩过了这个人存在的痕迹。
倒是数十日后,与如懿一起时,皇帝才淡淡问起:“那日送鸩酒,听说皇后亲自去了,玫嫔对你说了什么?”
如懿坐在曝光晴明底下,拈着一枚白玉棋子,专心于棋盘之上,不以为意道:“姐妹一场,终究得去送一送,玫嫔倒是说了几句,但都是疯话,不值得臣妾入耳,更不值得皇上入耳。”
皇帝含了若有若无的笑意:“疯话也是人话,说给朕听听。”
如懿支着腮,思忖片刻,郑重其事地下了一枚子,方才松了口气道:“玫嫔想知道,当年她死去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
静室内幽幽泛着微凉,角落里放着一尊鎏金龙鼎炉,毓瑚捻着尺余长的细金箸,熟练拨弄中炉内浅银色的细灰,又撒落一把龙涎香,香料燃烧,不时发出轻微的“噼啪”之声,越发衬得四周的空气安静若一潭碧水,皇帝道:“只是这样?”
如懿扬起眼眸,平视着皇帝:“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没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一面,是最大的缺撼,足以抱憾终身。”
墨玉的棋子落下时有袅袅余音,皇帝嘘一口气:“你告诉她了?”
如懿的目光微有悲悯:“这是她最后的心愿。”
皇帝微凉的手指像带着微湿的水汽,抚过她的手背:“皇后慈悲。”
如懿有难以言说的心绪,细细辩来,居然是一种畏惧:“是皇上慈悲,玫嫔自裁,皇上并未牵连她家人。”
皇帝的口气淡得如一抹云烟:“她也是一时糊涂。”
隐忍已久的哀凉如涌动于薄冰之下的冷水,无法静止。如懿只觉得齿冷,那种凉薄的心境,如山巅经年不散的浓雾,阴翳成无法穿破的困境,她终于忍不住道:“是。与其一世再这么糊涂下去,还不如自己了断了自己,由得自己一个痛快。”
如此寥寥几语,两人亦是相对默然了。殿中紫檀架上的青瓷阔口瓶中供着一丛丛茶蘼,雪白的一大蓬一大蓬,团团如轻绵的云,散着如蜜般清甜的雅香,垂落翠色的阴凉。置身花叶之侧,相顾无言久了,人也成了花气芬氲里薄薄的一片,疑被芳影静静埋没。幸好,意欢诞育的消息及时地拯救了彼此略显难堪的静默。李玉喜滋滋地叩门而入:“皇上大喜,皇后娘娘大喜,舒妃小主生了,是个阿哥!”
皇帝喜悦表情后有一瞬的失望:“是个阿哥?”
如懿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微妙的变化,笑道:“皇上跟前如今只有一个四公主,一定盼着舒妃生一个和她一般玲珑剔透的公主吧?其实阿哥也好公主也好,不都是皇上的骨血么?”
皇帝笑笑道:“甚好,按着规矩赏赐下去吧,叮嘱舒妃好好儿养着。朕和皇后晚上再去瞧她。”
李玉答应着,满面堆笑地下去了。
如懿轻声道:“皇上不高兴?”
棋盘上密密麻麻落满黑子白子,皇帝懒懒地伸手抚过:“没有。皇后多思了,只是有了那么多阿哥,又添上一个,没有从前那般欢喜罢了。”
彼时如懿与皇帝尚未踏足储秀宫,太后已经由福珈陪着去看了新生的十阿哥,欢喜之余更赏下了无数补品。其中更有一支千年紫参,用香色的宫缎精致地裹在外头,上面刺绣着童子送春来的烦琐花样,足有小儿手臂粗细,就连参须也是纤长饱满的——自然是紫参中的极品了。恰好嫔妃们都在,连见惯了人参的玉妍亦连连啧叹:“太后娘娘的东西,随便拿一件出来便是咱们没见过的稀罕物儿。”
福珈笑道:“可不是!这也算咱们太后压箱底的宝贝之一了,还是旧年间马齐大人在世的时候孝敬的。太后一直也舍不得,如今留着给舒妃小主了。”
意欢自然是感谢不已:“太后,臣妾年轻,哪里吃得了这样的好东西。”
太后笑叹着慈爱道:“自孝贤皇后去世后,皇帝一直郁郁不乐。你诞下皇子,这样让皇帝高兴的事,哀家自然疼你,且你生这个孩子受了多少的辛苦,临了生了,肚子里孩子的胞衣又下不来,硬生生让接生嬷嬷剥下来的,又受了一番苦楚,哀家疼你,更是疼皇帝和皇孙。”
意欢抱着怀中粉色的婴儿,仿佛看不够似的:“只要孩子安好,臣妾怎么样都是值当的。”
嫔妃们见太后如此看重,愈加奉承得紧,储秀宫中一片笑语连绵。
待回到自己宫中,嬿婉才沉下脸来,拿着玉轮慢慢地摩挲着脸颊,一手举着一面铜鎏花小圆镜仔细端详着,不耐烦道:“陪着在那儿笑啊笑的,笑得脸都酸了,也不知道有没有长出细纹来。”
澜翠正蹲在地上替嬿婉垂着腿,忙笑着道:“怎么会呢?小主年轻貌美,哪像舒妃在坐蓐,眼浮面肿,口歪鼻斜的。”
嬿婉丢下手里的小镜子,懒懒道:“舒妃哪里有你说的那么丑,本宫看她除了头发少些,也没什么大碍啊!”
澜翠不敢接嘴,却是春婵进来道:“小主,田嬷嬷来了。”
嬿婉神情一变,忙敛容正色道:“请她进来。”
田嬷嬷是个半老的婆子,穿了一身下人的服色,打扮得倒也干净,一看就是在宫里伺候久了的嬷嬷。十分世故老练,只是一笑起来,那笑容便能腻死个人。
嬿婉见她进来,倒也不急着说话,由着澜翠给田嬷嬷搬了张小杌子坐下,自已慢慢喝下了一碗冰豆香薷饮,才闲闲道:“如今天热了,不喝点子解暑消闷的东西,心里总是闷得慌。”
田嬷嬷忙同赔着笑脸道:“令妃娘娘说得是,这过日子谁没点儿闷着憋屈着的时候呀,奴婢这不就给您送痛快来了么?”
嬿婉的表情有些不大舒服:“舒妃不知道?”
田嬷嬷信心满怀:“这个自然,女人生下孩子之后,总得一刻钟到半个时辰的工夫,这胞衣才会娩出来。奴婢便假称舒妃小主的胞衣脱不下来,时辰未到就硬生生探手到宫体里给她硬扯了下来。”她得意地摆弄着右手道,“这一扯呀,手法可轻可重,奴婢的手一重,便是伤着宫体了,舒妃小主生下了十阿哥是她的福气,可再要生育,那便是再也不能了。”她说罢,眼巴巴地瞧着嬿婉,谄媚地笑,“这一切神不知鬼不觉的。小主的吩咐,奴婢做得还好么?”
嬿婉强忍着恶心与害怕,点点头:“做得是不错。可接生的嬷嬷不只你一个,还有太医在,你是怎么做到神不知鬼不觉的?”
田嬷嬷得意道:“人虽多,但奴婢是积年的老嬷嬷了,论起接生来,谁的资格也比不过奴婢。奴婢说的话,他们都得听着,都信。且太医到底是男人,虽然伺候在旁,却不敢乱看的,小主放心就是。”
嬿婉这才笑了笑,示意澜翠取出了银票给她:“三百两银票,你收好了。”
田嬷嬷笑得合不拢嘴,忙不迭将银票仔细叠好收进怀里。
嬿婉惋惜地摇摇头,撩拨着冻青釉双耳壶扁瓶中一束盛开的雪白茶蘼,那香花的甜气幽幽缠绕在她纤纤素手之间,如她的神情一般,“只是舒妃到底有神气,十阿哥平平安安,全须全尾地生下来了。”
“不能不生下来,那么多太医和嬷嬷在,又有太后万全的嘱咐,小主便容她一回吧。”田嬷嬷笑得有十足的把握,“只是生下来了,养不养得大还是一说呢。舒妃小主有孕的时候肾气太弱,生的若是个公主还好,可是个阿哥,那就难了。”
嬿婉眼中微微一亮,不动声色道:“真的难?”
“真的难!”田嬷嬷会心一笑,“那奴婢不扰小主歇息,先告退了。”
嬿婉凝视着田嬷嬷离去的背影,冷冷地笑了笑,任由微红的烛光照耀着她恬美容颜。
日子平静地过去,仿佛是随手牵同的大片锦缎,华美绚烂又乏善可陈。
玫嫔蕊姬与庆嫔缨络的事仿佛也一页黄纸,揭过去也便揭过去了。太后依旧是慈宁宫中颐养天年的太后,皇帝依旧是人前的孝子皇帝,连庆嫔身体见好后都依旧得宠,一切仿佛都未曾改变。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意欢这一生生育到底伤了元气,头发也没长回来多少。皇帝虽然常常去看望意欢和新生的十阿哥,并且嘱咐了太医仔细治疗脱发之首,但甚少再传她侍寝。意欢将何首乌汤一碗碗地喝下去,效果也是若有若无的,幸好她一门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得闲便整理皇帝的御诗打发时日,倒也不甚在意。
而十阿哥仿佛一只病弱的小猫,一点点风凉雨寒都能惹起他的不适,扯去意欢所有的心血精力,但,这也不过是漫长年岁里小小的波澜而已。日子就这样平静祥和地过着,仿佛也能过到天荒地老去
然而,打破这平静的,是平常而又不平常的一夜。
作为一个陪着同一个男人从少年同眠到中年的女人,如懿是难以忘却这特殊的一次的。
养心殿中小小一双红烛的火光跳跃着,照得双眼发涩。风凉雨软,吹得帐幕微微掀起,那灯光便又忽忽闪闪,这是一个寻常不过的秋天的夜晚,窗外天色阴沉,半点月光也没有,连星星都被银线般的雨丝淹没了,细雨绵延不绝地落在殿前的花树上,从树叶黄灿的枝条上溅起碎玉般凌冽的声音。
皇帝在她身上吃力地起伏着,分明已经汗流浃背了,却还是徒劳。如懿敏锐地发现了皇帝眼睛里深深的恐惧和迷乱,像一张布满毒丝的蛛网,先蒙住了他,然后蒙住了自己。
如懿的手指像春水一样在皇帝身上淙淙流淌,抚摸过他的面颊,他的耳垂,他的胸膛,她极力镇静着自已的心神,以此来面对皇帝从未有过的突如其来的失败。
皇帝的声音像漏着风,失去了一贯的沉稳笃定,变得软弱而胆怯:“如懿,如懿。”好似这样,便能唤回一点儿自信与精神似的。
如懿用明黄色赤线腾龙滑丝锦被遮住自己的身体,凝视着窗上一小块被雨淋湿的旋罗绢的窗纱,那种半干半湿的痕迹像某种开到糜烂的植物,散发着香气熏人而行将枯萎的气味,她的心绪烦躁而恐惧,有个念头秘不可示地转过,年过四十的皇帝,开始出现衰老的迹象。
皇帝绷紧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松弛下去,成了一摊软绵绵的滑腻的肉,养尊处优多年,皮肉是光滑滑而富有弹性的,夹杂着力不从心后汗水黏腻的气味。她情不自禁地哀伤起来,对着这个比自己大了七岁的男子,可是,这样的情绪她又怎敢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