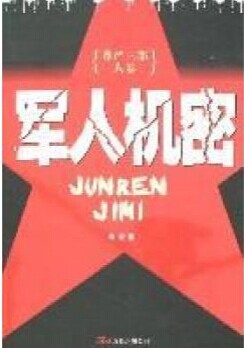军人机密-第3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碾子:“真走?”
事儿:“真走!”
小碾子咬咬牙:“走就走!”
姜家,卧室。
司马童与姜佑生像在进行一场政治谈判。
司马童:“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毛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七一公社’是一个保皇派组织,是右派,海军‘支左’,只能支‘狂飙兵团’。”
姜佑生:“毛主席相信军队,才用我们,‘支左’、‘支左’,当然是叫我们支持左派。谁左谁右,基地党委会有统一看法。”
司马童:“你们的党委也不会铁板一块,也会有左中右。你是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应该先有倾向性意见。”
姜佑生:“我们的党委是团结的。我提醒你,你的‘狂飙’不准试图分裂我的党委,不准分裂海军部队,这是前提。”
司马童淡淡一笑:“可以。我也不要求海军在所有的问题上支持我们。但有些事,请睁只眼闭只眼。”
姜佑生警惕:“你们要干什么?!”
司马童:“你……你虽然是司令员,但也不要什么事都管。”
姜佑生:“我当然不会什么事都管。但我告诉你,我是在‘支左’,不是在支儿子。为了避嫌,你得退出‘狂飙’的第一、第二把交椅。”
司马童一愣:“这个组织是我一手创立的,离开我就会闹内讧……”
“那样的话,你们算不得什么左派。”
“……我非得退?”
“必须退。”
司马童想想:“好!我连第三、第四把手也不干。换个形式而已。”
姜佑生:“不准搞什么花样!”
“形式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司马童笑笑,指着双人床上仅放着一套的枕头、被子,“妈妈是不是搬到隔壁去了?幸亏你们公开还是夫妻的形式,只是内外有别。”姜佑生语塞。
司马童站起来,临走,恢复了一张儿子的脸,他真诚恳求地说了一句:“爸爸,让着妈妈一点儿。”
司马童走出门后,姜佑生愤愤自语:“小野心家!小阴谋家!”
贺家,谢屋。
贺子达在谢石榴面前摩拳擦掌:“我的司令职务又恢复了,这回该看我们的了!谁拥护共产党我就支持谁,谁反对共产党我就镇压谁!老号长,你说,现在市里已分成两大派,我支哪一个?”
谢石榴抽着旱烟,苦着脸:“都是共产党的老百姓。”
“哎——”贺子达不满意地,“这时可来不得菩萨心肠!毛主席要军队出动,还不是为了迅速把局面稳定下来。我贺子达不是自吹,在领会上级的战略意图方面,我从来没出过岔!”
谢石榴:“我怕你越支越乱。”
贺子达:“不会。对付那种可能打乱套的仗,我最有办法。这就是一开始就要猛,就要果断,就要快刀斩乱麻。我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无论大小,都给它放进一个兵去,看谁还敢再乱折腾!”
谢石榴:“我倒要问问你,你准备支哪一个?”
贺子达:“那还用说,‘七一公社’的骨干都是过去的劳模、标兵,还有复转军人,我不支它支谁?!”
小火车站,夜。
一列货车停靠在站台,一个检修工用小锤“叮叮当当”地敲着车轮。
票房侧。枣儿:“这是货车,不是票车。”
小碾子:“货车不朝北开?”
枣儿:“那倒不是。碾子哥你等着,我去打听一下,这车是去哪的。”
枣儿刚要走,小碾子拉住她:“黑灯瞎火的,你一个姑娘家……问道,我会。”
“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
“哎。”小碾子走了,半道上还回了一次头。枣儿挥挥手。
站台,检修工敲着。小碾子走过去问:“这位大哥,这车是朝哪开的?”检修工未抬头地:“朝北。”小碾子喜上眉梢,又问:“要钱吗?”检修工回头瞥了一眼,继续往前敲轮子:“废话,不要钱!”小碾子更加欢喜:“哎,知道了。”他撒腿往回跑。检修工直起腰,看着小碾子跑的方向:“什么毛病!”
票房边。小碾子奔过来:“枣儿,没错,快上车,不要钱!”
“打听清楚了?”
“打听清楚了。”
“问仔细了?”
汽笛吼了一下,火车开始启动。小碾子拉住枣儿:“快!火车要跑……”枣儿和小碾子在站台上拼命奔跑,稀里糊涂爬上车头后面的煤车。
广播车窗外,烟火腾腾,一片武斗噪音。
戴着柳条帽的乔乔播音:“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两方的高音喇叭,在不断打语录仗和为自己的武斗队打气。
陆军作战室。军官报告:“贺司令,‘狂飙’围住了市府大楼,‘七一’的大本营吃紧。他们来电话求援。”
贺子达踱了两步:“命令一团一营立即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跑步到现场,先隔开双方。然后一边做工作,一边把‘狂飙’的武斗队分割开来!”
军官:“是!”
沙袋工事旁,“狂飙”的几个头头围住唯一不戴袖章的司马童:“司马童,‘地老鼠’如果压到红旗街口,‘七一公社’的死党马上就会突出包围圈。”
司马童:“要海军!话由你们说,大体意思这样……”
海军作战室。军官报告:“今天下午两点四十分,‘狂飙兵团’声称警备区的一个营已经在市府大楼的争夺中介入武斗,他们要我们采取相应对策。”
姜佑生:“贺子达真敢动武?再了解一下。”
另一军官:“门卫值班室报告,两分钟前警备区又有十五辆大卡车满载士兵开出大门,向市府方向驶去。”
军官们议论:“参加老百姓武斗,用得着那么多兵吗?”“贺子达想干什么?”
姜佑生猛地心中了然,微笑自语:“老一套,重兵突击,以势压人。”姜佑生看了一下手表,“命令:一、二、三支队各抽调二百人,登车待命!”
军官:“现在陆军有两个营,近八百人,我们的兵力是不是太少了……”
“足够了!”军官欲离。姜佑生又道:“听着,等贺子达的兵压过红旗街口时再出动,在‘狂飙’的前面再隔开一道。”
军官:“为什么要等到过了街口?”
姜佑生:“对‘七一’的人要网开一面,不能赶尽杀绝。执行!”
“是!”
陆军作战室。军官:“部队快压到红旗街口时,‘七一公社’向我们的战士手里塞棍棒和柳条帽,两个营长来电话问,拿还是不拿?”
贺子达狡猾地笑了一笑:“人家给你,你就拿着。”
海军作战室。军官:“陆军已压过红旗街口有十五米的距离。”
姜佑生看看手表:“该我们了。出动!”
“陆军大多装备了棍棒,我们,是不是……”
姜佑生不满地看了军官一眼:“我们只带语录本!”
“是!”军官跑步离开。
陆军作战室。军官:“海军六百人左右在我军前面组成‘人墙’,双方几乎鼻子顶着鼻子了,气氛十分紧张。”
“瞎紧张!”贺子达也似心中明了,他也看了一下手表,道:“命令一营、二营,撤!”
军官不解:“撤?”
贺子达:“快四个小时了,人家来换岗,你不回家吃饭吗?棍棒统统带走,柳条帽还给人家。”
“噢——”军官恍然大悟,拿起步话机话筒,“命令警备区部队全部撤回营房,立即开饭,饭后待命。”
现场。司马童狠狠捶了一下沙袋:“嘿!白打了一天!他们原来是担心武斗扩大,故意用兵隔开我们。这两个老家伙,现在在穿一条裤子,一个比一个滑!”
晚冬的北方夜晚,货车在“轰轰隆隆”地开着。
煤厢内,枣儿和小碾子脏兮兮的,冻得瑟瑟发抖。枣儿不由自主地使劲朝小碾子身上挤着,小碾子开始还犹豫,不一会儿渐渐伸出胳膊,渐渐搂住枣儿的肩头,渐渐两条胳膊上去,紧紧地搂着。寒冷,使枣儿和小碾子的搂抱十分单纯,十分纯洁。即使这样,他们俩仍在一起发抖。
南方则大雨如注。
贺子达披雨衣登上吉普。司机问:“贺司令,上哪?”
“市里随便走走。”
“这么乱……”
“正因为乱,才要看看。要不,要我这个警备司令干什么?!”
“要不再叫几个人?”
“你要害怕,我自己开车。”
“真是的……”司机嘟囔着,把车开出大门。吉普在雨中的街上转着……行至“华夏理丁大学”时,校园里的喇叭战与样板戏“打虎上山”的音乐震耳欲聋。
贺子达道:“进去看看。”
车驶进校门。两派学生的燃烧瓶炸得火光冲天。不知学生们用的是什么化学药品,五彩缤纷的。贺子达看得上瘾,笑骂:“这些大学生就是不一样,把仗打得像他妈过节似的!”说着,他钻出车。
司机:“你哪去?”
“我看看,对那些坏头头有个数。”
“我跟你一起去。”
“你看着车,别让人抢走了。”贺子达裹紧雨衣,猫着腰,钻进硝烟之中。
烟火中,贺子达反穿着雨衣,像个黑色的幽灵。他看见一处库房写着“文攻武卫”四个白字,推门走了进去。房子中央有两个写着“火药”的汽油桶,贺子达从桌上提起暖水瓶,倒在两个桶里,并出了个鬼脸。贺子达出门跑了几步,顺手把挂在小树上的广播线给拽断一根……“打虎上山”一下哑了。
谢石榴站在贺家门口看着雨夜,抽着烟。他似乎是在等贺子达,也在为他担心。
大学,两派的武斗并没因为贺子达的小破坏而有丝毫减弱,相反双方的高音喇叭都在喊:“正告A派的坏头头们,你们胆敢派出小股亡命徒偷袭我弹药库,我将以牙还牙!”“B派的保皇狗们听着,五分钟之前我广播线遭到破坏,这是你们猖狂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又一铁证!”
贺子达听着,苦笑着。一阵很猛的烟火把他逼进一座楼里。
楼上有人喊:“冲出去!”接着是一片杂乱的脚步声。贺子达又被逼到底楼,他推开一间地下室的门,赶紧闪进去。厮杀的人声渐渐远去。
贺子达滑稽地嘘口气,回身观察这间地下室。原来这是间半地下的实验室,到处都是试管、烧瓶……贺看见一个酒精炉上正烧着一口砂锅,走过去揭开盖,鼻子马上很有反应。锅里黑乎乎的,有一种膏质。接着贺子达发现地下室幽暗的光除了来自半截窗外的战火,还有一盏灯被电线长长地牵到一个壁柜里,壁柜的门没怎么关严。贺子达好奇地走到那壁柜前,猛地拉门:贺子达那个真正的儿子——鹿儿,正用两块棉花塞着耳朵眼儿,蜷在里面,埋头一边看书,一边演算习题!
鹿儿一惊,站起来,撞到了壁柜上面的隔板,发出“咚”的一响,又捂着脑袋坐下去。
中篇
15
贺子达拿起书看看:《高等数学》。他马上有一种天生的好感,笑笑,脱下雨衣的帽子,露出红五星。
鹿儿:“是军宣队的?”
贺子达:“就算是吧。”
“什么?”鹿儿没听清,忙掏出耳朵里的棉花。
贺子达故意地说道:“不关心国家大事,不参加革命运动,躲在这儿走白专道路可不好。”
鹿儿口吃:“是、是,我,偶尔……”
“别害怕,我说反话呢。”贺子达笑笑,叹了口气,“哎——这年头,像你这样的学生真是难得啊!放着书不好好读,玩打仗,打死一个,国家少一宝哟!”
鹿儿:“……您不是军宣队的?”
贺子达:“我是管军宣队的。”
“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
“……管军宣队的,好像比军宣队右……”
贺子达大笑:“说得好!”他重重拍了鹿儿一掌。鹿儿一歪斜,坐在地上。
“手重了,手重了。”贺子达马上疼爱地把鹿儿扶起来。他把壁柜里的书搬出一摞,坐在上面,解释,“累了,没有侮辱斯文的意思啊。”
鹿儿:“坐吧坐吧。”
贺子达慈爱地端详着鹿儿。鹿儿也打量着贺。贺子达把灯挪得离鹿儿的脸近一些,认真看着。鹿儿也揉揉眼睛,盯着贺。
贺子达:“我们见过面?”
鹿儿:“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你去过警备区?”
“去过,请人做报告。”
“什么时候?”
“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