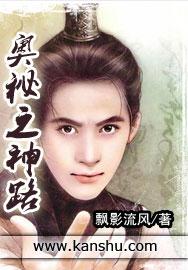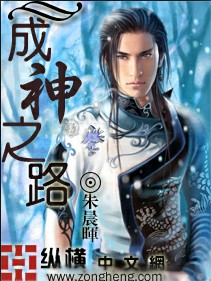桐花万里路-第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苏凌景暗叹了口气,自知辩驳不过他,只得道:“你还记得当年的大皇子穆容焱吗?”
穆容焱,正德帝第一个儿子,生母婉氏,是正德帝还是皇子时的通房丫头,因是庶出,虽为长子却无继任大统的权力,饶是如此,这位皇子却一直恪守本分,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加上性情本就温和无争,子恪与他虽然并不亲近,却也一直很敬重这位兄长。
只是……
子恪想起当年的崇华殿之乱,暗暗垂了眼眸,却听苏凌景接着道:“当年祁门关一别,我原本想去盛京寻你,却不料京中风云际变,我被穆容焱抓进监牢里,这伤,便是那时候留下的。”
子恪闻言抬头,眸中似乎有一瞬的震惊,但很快便明白了,他握拳的手在案几中一砸,冷哼道:“原来如此!”
正德三十六年四月,临洮之战的险胜鼓舞了平叛大军的士气,自叛军作乱以来的颓败之局幡然逆转,乾坤朗朗,平叛大军士气高涨,势如破竹一路北上,接连收复临州、洮州,五月,叛军见幽州久攻不下,转取景州,冯巳得此间隙又趁机收复了叠州,随即整顿大军,向东与唐万年的三十万大军汇合,成合围之势,于百里坡大败叛军。
狄肃且战且退,据守祁门关与平叛大军对峙,同年六月,两军又一次交锋,冯巳以奇兵诱狄肃深入祁门关的贝叶峰,斩杀了狄肃三员大将,又趁胜追击,在三青峡射杀狄肃,降敌军三万五千余人,至此,连绵半年之久的北疆三郡叛乱告一段落。
祁门关之战大获全胜,子恪原本打算待唐万年安顿三郡之后便随其一道班师回朝,却不料此时京中传来噩耗:太子的生母昭和皇后薨。
太子快马赶回盛京,却被正德帝软禁在东宫,第二日章德殿中颁下一道谕旨,大意是因其生母昭和皇后失德,废储君穆容祀太子之位。
太子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诬告他的母后曾与侍卫私通,怀疑她诞下的皇子非皇族血脉,正德帝盛怒之下质问昭和皇后,昭和皇后深觉受辱,又心寒同床共眠的丈夫竟如此不信任自己,心灰意冷之下自缢身亡,正德帝见死无对证,又见密告之中言之凿凿,人证物证俱在,更是深信不疑,盛怒之下撤了太子的储君之位。
正德三十六年七月的章德殿一片愁云惨淡,六十一岁的正德帝似乎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第二日早朝,正德帝招众臣公卿推议储君,有近半数的大臣推举大皇子,正德帝见大皇子之势盛极一时,反倒按下不表。
午后正德帝单独召见了大皇子,随侍左右的宫人听得书房之内一片争执声,紧接着瓷盏碎裂的声音响起,众人皆是诚惶诚恐,没有一个敢入内服侍的,待到大皇子出来,已是日薄西山,伺候在皇帝身旁的内侍省监秦寺战战兢兢地进了书房,见正德帝靠坐在龙椅之上,疲惫的按着眉心叹道:“这个位置坐的久了还真是硌人啊,他们要就给他们好了。”
秦寺立在一侧不知该接什么话好,却听正德帝又道:“朕真的是老了啊。”语调之中一片萧索。
秦寺暗暗抬头看了看龙椅上的皇帝,确实是有些风烛残年的老态,黄昏的光线照射进来,映得他发上的银丝比往日更加明显,他跪下一面收拾着杯盏的碎瓷,一面说道:“皇上福寿康健,哪里老了啊,老奴还要再伺候您个几十年呢!”
龙椅上的人隔了半晌方才说道:“朕哪里还有几十年了,罢了,你起来替朕拟旨吧。”
作者有话要说:
☆、心事只合说与君
光影西斜,穿过层层流苏纱帐透射进来,室内的安神香袅袅,隐约有些不真实的感觉,子恪从回忆中回过神来,略一垂眸平静道:“他死了。”
“死了么?”苏凌景重复道,语气中略带着一丝惊讶。
子恪心底却无端的一沉,他想起第二日去安和殿给父皇请安时的情形,那个时候,他跪在冰冷的水磨青砖地板上,光洁的地面倒映出自己的影子,看不清此刻自己是怎样的表情,他只听到重重帷幔里自己的父亲用苍老的声音问:“你大哥呢?”
“他死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说,不带一丝情绪。
“死了么。”帷幔中的声音沉寂了半晌,那片刻的沉寂于他而言却格外长,他听见殿中的九莲灯漏滴答、滴答的落水声,声声如同敲击在自己心上。
隔了半晌,帐中的人苍凉地笑道:“哈哈,好啊,好!朕养的好儿子!”
那笑声响彻在空旷的大殿中,极尽嘲讽,子恪将头埋得更深,不是没有后悔过,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哥哥。
只是,那一瞬间的失去理智让他意识到,那深藏于心中的感情是如此深刻而沉重,沉重到让他害怕,害怕借由任何一人宣之于口,无论这个人是谁。
他低头审视自己的影子,模糊的光线中忽然看到自己勾唇一笑,他俯身在地,平静地说道:“儿臣罪该万死,请父皇责罚!”
“责罚?这天下都是你的了,我怎敢责罚你!”又是一记嘲讽,那苍老的声音似是回忆起什么来:“子恪,你可知朕为何废了你的储君之位却仍把天下给你?”
“儿臣,不知。”
“十九年的尽心培育,朕在你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朕虽废你储君之位,却仍盼你能做个明君,纵使你不是朕的儿子又怎样?可你倒好,登基第一天就弑兄瞒父,你……太叫朕失望了!”
太叫朕失望了!!
那声训斥横亘在脑海之中,这些年来,这件事情便如芒刺在背,纵使他做的再好,也无法掩盖他弑兄的这一件事实。
自那以后父亲便长病不起,拒绝再见他一面,第二年春天便离开人世了。
“是,被我杀死的。”子恪又道,语气之中的萧索意味,却是苏凌景从未见过的。
苏凌景抬眸,有瞬间的震惊:“子恪……”
子恪平静地将那日崇华殿的事情讲给苏凌景听,略去穆容焱提到他的那一截,顿了顿又道:“逸之,你是不是也认为我是一个酷厉严苛,残暴薄凉的人?”
苏凌景自他的叙述中回过神来,摇了摇头,温和道:“虽然那个时候有很多种可以制住他的方式,但当时情形就算是我也没办法做到更好,杀死自己的亲哥哥确然不是什么值得提倡的事,纵使他已经失去理智,但是,子恪,我只是想告诉你,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就算是我也会失去理智,逝者已矣,不必用一时的错误评判一生的对错,你从来不是酷厉严苛、残暴薄凉的人,相反,我认识的子恪虽然偶尔任性,却一直是个温柔的孩子。”
子恪倏然抬眸,直视苏凌景的眼睛,那眸中的锐光点点,熠熠生辉,半晌忽然意识到他方才说的话,别过脸不自然道:“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恩。”苏凌景抬手拍了拍子恪的肩,四年未见,他再也没有当年孩子的模样,可似乎是一种习惯,总会不自然地将他和当年联系在一起。
子恪将苏凌景的手拉下,看着掌心的纹路道:“逸之,他……是怎么为难你的?”
似乎想起不愿意回忆的事情,苏凌景的眉间轻蹙,子恪没有放过那一丝的表情,握住他的手一紧,轻道:“不愿意说便算了,反正他也已经死了。”
苏凌景展颜一笑:“没什么不愿意说的,只是不明白当时穆容焱心中所想。初时我在盛京遇到他,他似乎知道我在寻你,便告诉我皇城之中大变,让我在他府中稍安勿躁,他会替我给你带信,我想彼时我已无官职在身,加上皇城之中又是非常时期,确实不宜轻举妄动,便在他府中住下了。后来无意间听他与近卫军密谋,半数皇城的军队控制在他手中,我心知不妙,想要通知你,却不知他从何处听得我曾化名为林毅助晋王谋反一事,劝说我留下……”
苏凌景想起那个时候的穆容焱,眸中阴蜇得全然没有初见时的温润,他说:“谋权篡位不是你一直以来帮晋王做的事情么?如今我们不谋而合,你该高兴才对啊,苏凌景,站在我身边吧,我要你看看,这天下是如何被我纳入囊中的!”
子恪握住他的手又紧了紧:“后来呢?”
苏凌景不甚在意地说道:“后来我几番出逃都被他抓住了,他嫌我轻功碍事,便把我手脚筋挑断了……”
那轻描淡写的语气仿佛不是在说自己的事,子恪却知道他所受的苦决不止这简单的一句,蓦然心口揪心似地一痛,他略带后怕的轻吐出一口气,将他的手按在心口,喃喃道:“幸好,幸好……”
幸好你还活着,幸好还能见到你。
苏凌景见子恪一阵难过,抬起另一只手揉了揉他的头发,叹气道:“早知你如此便不说了,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熟悉的动作勾起许多年少时的回忆,子恪觉得心口酸涩地疼,忍不住便要将心头深藏的话脱口而出,却听苏凌景道:“好了,不说了,翟前辈说他已经找到恢复的法子了,虽然武功不能和从前一样,但要想恢复成一个正常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子恪见苏凌景朝他宽慰一笑,原本憋在心里好多的话却没了机会出口,他点点头道:“好,这几日得闲,我便陪着你罢。”
话音刚落便听见屏风后面有人轻轻地咳了一声,接着一个须发花白的脑袋探进来,翟风嘿嘿笑了两声,道:“二位谈完了?”
子恪蓦地被人打断,脸色黑了黑:“你来做什么?”
翟风白胡子一蹬:“小子,这是我的病人啊,我叫你看会你倒看成自己的了,别过河拆桥哈,当心我一个不高兴不治了!”
子恪没料到翟风这么不卖他面子,想了想没反驳,只哼了一声。
苏凌景失笑,总觉得这两日来这两个人不对盘,他摇摇头,又对翟风道:“这几日辛苦前辈了。”
翟风笑眯眯地坐下,点头赞许:“还是苏小友懂事,”顿了顿转头对子恪道:“先说好,我可不是卖你的面子治的。”
子恪转头不再理会翟风,倒是苏凌景接口道:“好了,前辈,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子恪起身便要走,刚动作便听见咕噜一声,他顿了顿,才尴尬地发觉那是从自己肚子里发出来的。
苏凌景疑惑地看了看子恪,问道:“子恪没用午膳吗?”
见子恪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苏凌景笑笑说:“躺了这么久我也饿了,正好一起用饭吧,前辈要不要一起?”
翟风两眼发亮,对苏凌景道:“你下厨?”
子恪的脸更黑了黑,他起身边往外走,边道:“他现在能下什么厨?躺好,我去吩咐他们备饭。”
翟风见子恪出去,看了他的背影一眼,对苏凌景道:“他现在怎么这么别扭?”
苏凌景笑笑:“我也觉得子恪今日怪怪的,前辈莫不是说了什么话刺激到他了罢?”
翟风抓抓头发,努力回想:“啊,不会是我说你快死了吧?”
苏凌景无奈地叹气:“前辈,那种话是能随便说的么?”
作者有话要说:
☆、此时无声胜有声
日暮西沉,熔金的流光照洒在宸朝宫的翠瓦金檐之上,金色的光线衬得琉璃砖瓦愈加流光溢彩,淡月初升,悬在大殿之后的那方暮色渐沉的天幕中,似一抹浅淡的影子,同这绛紫深彤的晚霞极不相称,子恪将视线收回,划过窗下凝思对弈的苏凌景,他手执棋谱正对着其中一页解一个古局,黑子衬得他指尖莹白如玉,落日的余晖给他渡上一层淡金色的流光,静谧美好的有些不真实。
像极了那抹淡月,这金碧辉煌的宫殿都压不过他的清淡,似乎只要他在,便觉格外安心。
似乎注意到他的视线,苏凌景从棋盘中抬起头来,正对上子恪若有所思的表情,他放下棋谱问道:“忙完了?”
这几日子恪真如那日所说,得闲了便往宸朝宫里来,后来索性将奏章搬到这里来批阅,忙得晚了便在这里睡下,几乎将宸朝宫当做自己的寝殿了,起初苏凌景还说他,后来索性便不管了,于是便这样,一人批阅奏折,一人或研棋对弈,或读书弄墨,倒也悠闲,只一点,无论子恪多晚,苏凌景都陪着他。
子恪应了一声,将笔放下,绕过桌案走到苏凌景面前,低头审视着那盘残局,问道:“还是昨日那个?”
“恩。”苏凌景将手边的参茶递给他,见他坐下才道:“这古局解了两日了,大约是个残谱。”
子恪端了参茶押了一口,信手捻了一子落下,笑道:“你跟那老头儿还真是一样。”
苏凌景见棋路渐开,子恪落下的那子是之前从未想过的地方,霍然有些柳岸花明之感,也跟着落下,边道:“怎么?”
“都是棋痴。”子恪见苏凌景专注的模样,索性陪他下下去,这一子下得倒不似方才漫不经心,思索了半晌才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