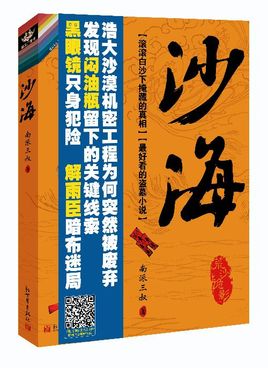迷途笔记-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欧阳乾
¤╭⌒╮ ╭⌒╮欢迎光临
╱◥██◣ ╭╭ ⌒
︱田︱田田| ╰……
╬╬╬╬╬╬╬╬╬╬╬╬╬╬╬版 权 归 原 作 者
。。
引子
世界有没有漏洞?
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可笑,它看上去是如此地真实,每天忙碌的工作带来的压力、夜店里性感妩媚的女郎、可口美味的食物、被女友抛弃时的痛苦……这一切都让我们完美地体验着它的存在。但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萦绕在我意识深处,让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起码不是看上去的那么回事。
很显然,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所以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继续深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取了社科院的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科学”。这是一个笼统而扯淡的专业,每个研究它的人最后不是变得歇斯底里,就是呆板刻薄,上过“毛概马哲”的兄弟应该都知道。为了完成毕业论文,掌握第一手资料,我跟我的导师天南海北地跑了很多地方,包括秦岭绝壁、黄河古道,还有川中疫区。在这些地方,我接触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见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我的固有意识里,它们本应该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就活生生地存在着,即使像个Bug,也“存在即合理”一般不容置疑地存在着,并且还呈某种规律性的联系……这已经明显超越了我毕业论文的研究范畴,也违背了我大学之后继续深造的初衷——我对这个世界的怀疑死灰复燃,怀疑它的构成、怀疑它的目的,甚至怀疑整个人类本身。
我们为何在此?
我们从何而来?
我们意义何在?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踏进这个世界的漏洞,我终于知晓了一些答案。但对于一个具有既定法则的世界来说,你怀疑了它,同时也就等于被它宣判了死刑。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当我了解了这一切后还是忍不住暗骂一声。
第一篇笔记 迟到的流浪者
康锦跟我认识的所有的社科老师都不一样,他不歇斯底里,也不呆板刻薄,也不心理变态……这是我的一个阴影,在我以前大学考试的时候,因为一时笔误把“马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写成了“马精”,结果老师连着让我三次补考都没过,所以我对社科老师有着一种天生的恐惧。不过幸好康锦是个正常人,也幸好他就是我的导师。
我是跨专业考进来的研究生,所以康锦对我非常照顾,为了让我能够在毕业的时候顺利完成论文,他从一开始就带着我跑了很多地方,奔波于各个省份之间,让我能够积累第一手的宝贵素材。这些地方有的该去,而有的去了就是个错误。
比如鲁西南那一次,就是不该去的。那一次旅程就像是一把钥匙,慢慢开启了一扇通向深渊的大门,它吓到了我不说,还吓到了许多人,差不多有七十亿。
“老师,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在大巴车上,我一边啃着面包一边说。
“菏泽。”康锦头靠在椅背上,双眼望着窗外,“传说在上古时代,那里曾经发生过天人交战,战后就成了一片大泽之地,所以叫菏泽。你这样记就能记住了。”
“哦,联想记忆法。”我点点头。
“长青,这次是个极好的案例,你一定要做好记录。关于‘人长期在重压下生活会导致人格的裂变’,这样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我疑问道:“老师,人还没见呢,你就能下定这样的结论?”
“大体情况我已经在电话里了解了一些,差不多就是这样。很多事情看起来光怪陆离、千奇百怪,但究其背后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对事情要善于分析和归纳,长青,这也是你以后学习的方向。”康锦说完,把身体全部放松在了座椅上,闭目养神。
当我们下大巴车的时候,已是下午。通向村庄的乡间小路被雨水冲毁了,泥泞不堪,根本没法通车。村长赶着驴车已经在路口等候多时了,见了我们急忙招呼着。于是我们又换乘了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只是这条路实在太泥泞了,驴子走起来都深一脚浅一脚的。等我们赶到村里的时候,天色已然是黄昏了。
村长擦着头上的汗,带着歉意地笑笑说:“康教授,这就是咱们村,挺破的,多少年了也没发展起来,您别见笑啊……要不,咱们先去村委会安排好住宿吧?”
他话里夹杂着浓郁的地方口音,勉强能让人听个明白。康锦摆摆手说:“没事,住宿倒是不急,先去一趟曹金花家里吧。”
曹金花,这个女人是我们此行的唯一目的。在来之前,已经有三位心理医生对她束手无策,而曹金花家里也付不起长期在精神病院治疗的费用。对于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村妇来说,乡财政收入再多也没有闲钱送你看病,只要你不掂着刀乱砍人,那么就算相安无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康锦得知了这个情况,他觉得颇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就跟乡政府联系了一下,说自己或许能解决这个事情。乡里当然乐意,就安排村里接待一下,于是康锦就带着我来了。
村长挥鞭呵斥驴子,车子朝村内走去。我已经被颠得七荤八素了,扶着脑袋问:“老师,我怎么听着这里的人说话口音跟王宝强差不多啊?”
“这是河南口音。”康锦往南边指了指,“瞧,那边就是黄河,很近,过了黄河就是河南省了。1963年前后,这里整个县还属于河南省,后来因为黄河发水,经常改道,河两边的人为了争地发生过很多次械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就把这一片全划归菏泽管辖了。地是划过来了,可这口音还是以前的。”
村长惊讶地瞅了康锦一眼,继续赶着驴子说:“教授就是教授,真跟平头老百姓不一样,啥都知道!乡里领导说你是个大学者,让俺好好配合你工作,跟你学习学习……”
康锦笑着摆了摆手:“老哥,太夸张了,我算不上什么大学者,顶多就是个知识分子。对了,你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下曹金花的情况?”
“她啊?”村长皱眉想了半天,最后摇了摇脑袋,“不知道该咋说,本来好好的,也不知道咋的忽然就变成现在这个样了。也没别的,就是她说的话别人一句也听不明白。乡里不是也派人来看过好几次吗,一点法子都没有。”
曹金花家住村西头,三间破旧的红砖瓦房。曹金花的丈夫跟一群汉子正蹲在路边吃着晚饭。鲁西南地区的风俗,晚饭的时候大老爷们儿都会捧着碗蹲在路边吃,一边吃一边唠嗑。她丈夫看到我们来了急忙放下饭碗,站起来在衣服上蹭了蹭手,局促地笑了起来:“来,来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庄稼汉子的形象,四五十岁,背稍有佝偻,眼角的皱纹随着笑容绽放开来,像一道道冲开的沟壑。我们跟着他朝院门走去,后面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老人小孩都有,还有几个端着饭碗的,一边走一边哧溜。
到了院门口,村长回身摆着手驱赶道:“去!去!有什么好看的,该干吗干吗去!”
几个小孩嬉笑着跳开。没有人远去,都聚在曹金花家门口,像一群等待电影放映的观众。几个妇女还伸长了脖子,显出急不可耐的神情。进门之前,她丈夫嗫嚅着嘱咐道:“你们别问得太急,别逼她,要不她就哭,光摔东西……”
康锦点点头,示意他不用担心,就领着我走了进去。村长则站在门口,不让任何看热闹的进来。
屋里没有开灯,光线有些昏暗。黄昏的阳光像掺了水一样稀薄,编织在一起淡淡地洒开。桌子边只坐着一个女人,我想那就是曹金花。她体形有些臃肿,跟一般农村妇女的打扮也别无二致,乱糟糟的头发昭示着这个村子的美发水平。曹金花就坐在那里,端着搪瓷碗,就着咸菜有一下没一下地喝着稀饭,对我们的到来视而不见。
“长青,你先跟她沟通一下,注意引导。”康锦小声对我说。
我点点头,这是培养我与人沟通能力的最好方法。康锦也习惯这样,他喜欢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研究人,研究交谈对象,这样便于更冷静地观察研究对象的肢体动作和细微神态。
我在曹金花对面坐了下来,隔着一张油腻的方桌。她抬了一下头,眼神稍有呆滞。
我说:“你好。”
她低下头喝稀饭,并不理我。
我继续:“我们是专程从外地赶过来的,希望能跟你交流一下。”
她仍旧不理我。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都会这样,对于别人的问话不理不睬。这是因为他们始终沉浸在一种自己创造的主观世界里,无法有效地对外界做出反应。我并不气馁,从各个角度旁敲侧击,希望能找到引起她注意的话题。就在我喋喋不休的时候,她忽然抬起了头看着我。
“乡里告诉你我是个精神病对不对?”
我愣了一下。她的普通话竟然说得很标准,但还夹杂着一点淡淡的地方口音。
我说:“没有,乡里没有出具任何诊断,你别多想。我就是跟你随便聊聊。有时候精神上的压力会有一些隐性的表现,自己也很难发觉。不过我们可以谈谈,试着找到发现问题的途径。”
她用粗糙的手抹了抹额头上的刘海,说:“这么说,你还是觉得我有精神病。”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跟你沟通一下。”
她:“你想怎么沟通?”
我:“这样吧,我能不能先问你几个问题,就是些很普通的,你随意回答一下就行。”
她放下了筷子,看了我一会儿说:“行,你问吧。”
我试着问了第一个问题:“你多大了?”
她:“四十六。属狗的。”
我:“你叫什么?”
她:“现在的名字,曹金花。”
我:“现在的名字?那你原来叫什么?”
她:“原来的名字也只是一个代号,并不能代表什么。”
我疑惑地看了康锦一眼,这明显不是一个农村妇女应该有的谈吐。康锦点点头,示意我继续。
我:“之前有没有去过外地?”
她:“没有。”
我:“不可能吧。你普通话怎么说得那么好?”
她笑了:“我觉得原来的口音太土了,很难听。怎么,这对你们来说很难吗?”
你们?这个词用得太奇怪了。我顿了一下说:“抛去曹金花这个名字本身的代号意义,那么,你到底是谁?”
她又笑了:“你问了一个聪明的问题。跟乡里派下来的那些人不一样。”
我附和着她:“是。那你能不能回答我?”
她叹了一口气,露出的表情就像哀叹今年的收成不好一样:“好吧,我告诉你,我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远到你不能想象。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执行一个任务。可惜,我来晚了,任务早已经完了。我是一个迟到的流浪者。”
我:“执行什么任务?”
她摇摇头,又端起了搪瓷碗:“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不能回想太多以前的事情,想多了就头疼。我迷失在旅程里的时间太长了。”
我无奈地站了起来,看到曹金花的丈夫正站在门口略带惊讶地看着我。出门后他对我说:“奇了怪哩,金花跟你说了这么长时间,还真是第一次。原来乡里来的那些人,说不两句她就摔盘子摔碗的。”
我挠挠头,曹金花说的那些话我还不能消化。康锦合上手里的笔记本,询问道:“曹金花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就上个月,到现在还不满二十天。”她丈夫想了想说。
康锦问:“突然间就变成这样了吗?”
“怪突然的。那天下地干活回来以后就不行了,也没谁招她惹她,她就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发癔症,先是哭,哭完一阵又笑,笑完以后就成这样了,说些我们都听不明白的话。”
“她普通话跟谁学的?”
“谁知道啊,原来谁也没听她说过。”
“你们有孩子吗?”
“有,在广州打工。就年底能回来一趟。”
“曹金花去广州看过儿子?”
“没,没去过。别说广州了,她长这么大都没出过乡,连县城里都没去过。”
“平时喜欢看新闻联播?”
“嘿嘿,庄稼人,谁看那个啊。”她丈夫有些不好意思,挠挠脑袋,“天线坏好几年了,只能收两个本地台,还不清楚,平时也都没人看。”
这时村长已经把看热闹的人都撵走了,拿袖子擦着汗过来问:“怎么样,康教授?”
“大体情况都已经了解了,先回村委吧,有些具体情况还要等明天再说。”康锦走的时候又安慰了一下她丈夫,“别担心,这个案例虽然有些特殊,但也不算很棘手。晚上回去我再考虑一下。”
她丈夫有点发蒙。村长在一边搡了他一把:“还是康教授有本事啊,乡里来的那些人是一点法子都没有。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谢谢康教授?”
她丈夫醒过神来,忙不迭地握着康锦的手上下摇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