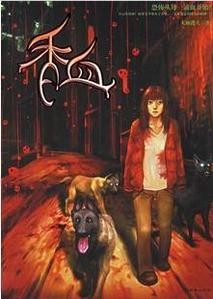香血-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键的秘密。到了沈浩的出事地点 ,却发现什么香气也没有——那时候距离沈浩出事不过两个小时,按照郭德昌死后香味残余的时间来看,香 气应该不会这么快消失。这让他们觉得有些奇怪。在现场地面上留下的一小摊血迹,除了正常的血腥味,再 没有其他味道。他们带去的痕迹专家通过辨认足迹,带着大家慢慢走过好几条街道,大约过了两个小时,转 了差不多大半个城市,众人忽然都闻到了那种芳香。
一丝丝,漂浮过来,让人心中一紧。
警犬们都狂吠起来,铁链被拉得不断作响,人们都有些紧张,江阔天感到恐惧在心里慢慢滋生,然而他 表面却不动声色——他是警察,是队长——他这种表面的冷静让其他人稍稍安心了。
在江阔天对我讲述当时的情形时,他的额头又再次冒汗了。我若不曾体会过那种恐惧,就不会理解他当 时的心情。正因为我也被那种恐惧所缠绕,所以接下来的话,他不必说,我也知道了。
他虽然表面上很冷静,心里却很惶恐,甚至有些无助的感觉。这让他立即想到了我,只有在我面前,他 才不用掩饰他的恐惧。因此他便打了我的手机,而我也没让他失望,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谢谢你。”他在车里真心诚意地说,倒让我忍不住笑了——我帮他的次数多了,他几时对我这么客气 过?
也只有那样的环境、那样的遭遇之后,他才会仿佛变了个人似的对我心存感激。这才只过了一个夜晚, 他便恢复了大大咧咧的本性,对我毫不客气。我穿衣洗漱总共不过十分钟,弄完之后立即出门,才到电梯口 ,他又打我的手机,连声催我要快。我刚刚答应,电梯到了,走进电梯,信息也随之中断,这使我没来得及 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语气仿佛和平常不太一样,我从来没听见过他那样的……我搜索着词句来形容他的 语调,一个词蓦然蹦了出来,让我心头一惊。
那是——“惊恐!”
江阔天并没有在公安局等我,当他给我打第二个电话时,他已经到了法医检验处的停尸房里。我赶到那 里时,他和老王两个人正站在门口喝酒,一人一小瓶烧酒往嘴里灌,刀子般的烧酒灌下去,他们的脸色还是 惨白,仿佛在停尸房被冷冻得过头了。
“出什么事了?”我直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江阔天看到我,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打我,却听见他激动地说:“你总算来了— —快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晚了就看不到了!”边说边揪着我的衣领将我朝停尸房内推。他身形高大,将我 推得踉踉跄跄。我跟他正要进去,老王一把拉住我,将烧酒递到我嘴边:“喝两口!”他的声音和江阔天的 声音一样紧张得有些颤抖。
我空腹出来,尚未吃早餐,不宜饮酒,正要推辞,江阔天已经举着那扁酒瓶朝我嘴里一灌,我不得不连 吞几口那烈火般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心里,滋味实在不好受,我赶紧推开他:“够了!”
“不够!”他白着脸道,又要朝我灌,我见势不对,一闪身溜进了停尸房。
一股干燥的寒气迎面扑来,带着福尔马林的味道。灯已经被打开,明亮的灯光下,解剖台上的尸体和白 布显得有几分刺眼。
江阔天和老王也跟了进来,两人站在我身边,不断喝酒,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具尸体。
虽然相隔有十米左右的距离,我还是看出,那具尸体,是郭德昌。
走到尸体边,我感到有几分惊讶。他死了这么久,脸部的恐怖表情依旧,其他部位也没有任何改变,肌 肉仍旧十分有弹性——尸体保存得这么好,着实出人意料。
然而我没看到任何特别的地方。
我困惑地看看老王,他额头已经汗得如同才被水浇过,伸出一只白得眩目的手掌,轻轻掀起了覆盖着尸 体的白布。
郭德昌的身体整个暴露在我的面前。
黄色人种的尸体其实是很奇怪的,有的人死后皮肤是蜡黄色,黄得像用颜料染过;而有的人死后,却是 惨白一片,白得像个白种人;还有一些尸体,则分明地变成绿色,当然不是植物那样的绿,那种绿是一种漂 浮在皮肤之上的绿意,不很明确——我一直对这种现象感到困惑。但郭德昌的尸体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情况 。他的皮肤原本就是白里透红,只微微有点黄,现在,除了那点红不再透出来,依旧是黄白混杂,看上去很 自然,甚至比我刚刚发现他尸体的时候都更加自然,不像一具尸体,倒像是个活人睡着了。如果不是他腹部 那条解剖的伤痕依旧醒目,我简直会怀疑他根本就没有死。
等等!
我的眼睛掠过他身体上什么地方,忽然产生了一丝不安的感觉。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我仔细地查看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却再也不知道那种感觉从何而来。
“你还没看出来?”老王颤声道,他和江阔天看一眼尸体又看看我,那眼光让我心里发毛,要不是熟悉 他们俩人,我一定会认为自己面前的这两个人精神不正常。我转开眼睛继续研究尸体——相比他们的目光, 倒是这具尸体比较不令人胆寒。
“你们想要我看出什么?”看了许久,什么也没发现,我不由有些恼怒——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
江阔天带着酒气的嘴凑在我耳边,低声说出两个字:“伤疤。”
他这么一说,我的心不由一沉。
正是伤疤——正是郭德昌身上那道解剖的伤疤让我感觉不对劲!
那道伤疤,就在他的腹部,从肚脐延伸到腹股沟附近,细小的一道黑色印迹,仿佛一条蚯蚓蜿蜒在他的 身体上。
如果我不是昨天见过他的尸体,我绝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从表面上看来,他的尸体和其他普通尸体没 什么两样,一点怪异之处也没有。
但是我分明记得,昨天的时候,这道伤疤是从胸口一直延伸下去,伤痕又粗又大,足有我的拇指那么粗 ,现在却只出现在肚脐以下,胸口光滑无比,不要说缝合后的伤疤,连一道小小的痕迹也没有。不止如此, 现在这道伤疤,细得像筷子,完全不像昨天那么醒目。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自己记错了,虽然我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说我记错了,又 有什么别的解释?
但是,当我仔细看着那道伤疤大约两分钟时,我情不自禁地用一只手捂住胸口,另一只手,从江阔天手 里将那瓶只剩小半瓶的烧酒抢了过来,咕嘟咕嘟连喝了几大口。
酒在腹内产生的热量,并不足以驱散我心底产生的寒意。我吞下最后一口酒,望着江阔天和老王:“我 是不是眼花了。”
他们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紧紧捏住那只冰冷坚硬的酒瓶——我不知为什么要捏住它,可是总得捏住点什么东西,我的手才不至 于发抖。再次朝那道伤疤望去,先前所看到的事情仍旧在发生,我没有眼花,江阔天和老王也没有,这怪事 真的发生了。
那道黑色的伤疤,在微微地蠕动,蠕动得非常缓慢,不仔细看,仿佛是静止的。那种蠕动,不是改变位 置的运动,而是自身的一种变化。随着伤疤的蠕动,它慢慢地缩小、变短,每次只收缩很小很小的一点距离 ,但是却在不断进行着。我看了一阵,一滴冷汗从额头滑落到眼睛里,涩得我的眼睛一痛。抹去眼中的汗水 和泪水,我咬了咬牙,将手指凑到尸体上——冰冷,僵硬,这的确是一具尸体无疑——在接触到他皮肤的那 一刹那,我几乎忍不住要大叫起来,一阵触电般强烈的恐惧感从手指尖传遍我的全身。我勉强控制着自己, 将手指轻轻点在伤疤靠近肚脐的一端。我们三个人屏住呼吸,六只眼睛紧紧盯着那道伤疤和我的手指。
我的手指就点在端点之上,黑色的端点下,伤疤正有条不紊地蠕动着。过了几分钟,我一条手臂都因为 紧张而发麻了——我的手指一动也没有动,绝对没有动,它紧紧地按在尸体上,微微凹下去一个窝。
我的手指一动也没有动,但是它现在不在伤疤的端点处了。伤疤又缩短了一小部分,现在它的端点距离 我的手指有两厘米左右的距离。而我的手指落下的地方,现在没有任何痕迹,变得光滑异常。
伤疤果然是缩短了。
“它又缩短了,”老王喃喃地道,“现在只有15厘米左右了。”我真佩服老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职 业习惯仍旧没有丢失,居然坚持用一根尺量了量伤疤的长度。
“刚才我们量的时候,还有25厘米。”江阔天对我说。
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怪不得他们的表现这样反常,怪不得江阔天对我说“晚了就看不到了”,原来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怪不得他们不肯先告诉我,这样的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
“你比我们强,我们第一眼看到这种情况,都逃了出去。”江阔天苦笑着道。
我暗叫一声惭愧。
我何尝不想逃?只是双腿已经软得没有一丝力气了,要不是偷偷用小腿靠着解剖台支撑着自己,我怕我 已经倒下去了。
老王将尺留在尸体的肚皮上,我们走了出去——我的脚步有点摇晃,江阔天却没有像往常一样笑话我, 想来他和老王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时,大概也是摇晃着出去的吧。
出了门,我立即反身将门紧紧关上,又连喝了几口酒,却一点也没有压住心底的恐惧。那种恐惧,反而 随着房门的关上而翻江倒海,更加厉害。
在这扇关上的门后,一具那样变化的尸体,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会不会一开门,他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关于尸体和鬼怪,中国和外国的小说、电影、传说都不缺乏,现在都集中在我脑海里翻腾,让我越想越 觉可怕。
对于不在眼前的郭德昌的尸体,我有无穷想象,而每一种想象,都比伤疤的收缩要更加可怕。
我擦了一把又一把冷汗,低声道:“他会变成什么样?”
“不知道,”老王也抹了一把汗,“我没见过这样的尸体——我甚至不敢断定他是不是真的死了。”他 的话又让我吓了一跳,我瞪大眼睛望着他:“他应该是死了吧?”
如果郭德昌其实没有死,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无法想象一个活人被解剖的滋味,忍不住又打了个 寒战。
老王苦笑道:“根据常规来说,一个血液流光、被解剖了一天两夜、并且没有任何呼吸心跳的人,应该 是死了。”
“但是人死了,他的伤痕又怎么可能恢复?”
江阔天叹了一口长气:“你又见过哪个活人的伤痕恢复得这么快?”
我们忽然都不再说话。
关上了停尸房的铁门,我们还是不敢在门口待得太久。这间停尸房所在的地方,是整个检验所最偏僻阴 暗的角落,矮矮的一间房,蜷缩在四周高大建筑物的阴影下,终年不见阳光,也没有什么人来,显得格外凄 清。
绕过一条长长的走廊,阳光照在身上,我们三人互相望了望,都是死人般的一张脸。在那个停尸房里, 除了尸体本身的变化,还有一件事也令我非常不安,可是我无法说出那是什么,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无 法言说。
酒已经喝完,江阔天从口袋里掏出烟,一人叼了一支,大口吞吸,总算镇定了一点。
“你们怎么看?”江阔天问。
老王沉默着摇了摇头:“我检验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吐出一口烟,回头望望停尸 房,“我不放心。”
江阔天也道:“我也不放心。”
“我也是。”我说。
除了担心和害怕,我们似乎也不能再做什么了,守在这里,没有多大意义。江阔天打电话叫了一小队警 察守在这里,说要严防人进出,弄得那些警察莫名其妙,不知道有谁会进去,更不明白会有谁从里面出来。 我们当然不能说里面有一具尸体可能会突然活过来,随便找了个理由胡乱解释一番,就离开了。
老王去化验室查看分析结果,我和江阔天也在半道分手,他回局里,我到医院去看看沈浩,当然,还有 貂儿。
我赶到医院时,没看到貂儿,沈浩的病房里陪护的是个老护士,慈眉善 目,看到我进来,知道我的身份后,不等我问,便将沈浩的情况告诉了我。
昨天被送进医院时,沈浩的情况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