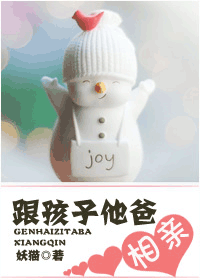农村孩子的蜕变-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给工头留个好印象”之类的,担心自己孩子出去了不能被工头看重撵回来了。父亲也叫他好好的干,能被工头欣赏以后就不担心没有挣钱的门路了,能跟一个好工头不容易,样子哦自己好好把握。
怀揣着父母的嘱咐与希望,与一群一个也不熟的陌生人厮混在一起,不管都有什么样的梦想,到了工地就属出力干活最为现实。工头接的是污水泵房的土方工程,全是掏力气的活,每天上班十个小时,除了吃饭每天可以挣不到二块钱,在那里他第一次受了伤,几乎是致命的。
那天,他和两个伙伴下到八米深的地下污水泵房基坑底,往吊篮下的翻斗车里装土,上面有人负责把翻斗车卸下拉走,再由另外的人把空车子挂上吊篮放下来。本来都已经干顺了的活路,都没怎么的担心会出现意外的,偏偏该他倒霉,等上面放空车的刚挂好车子,起吊的吊篮将横在钢管上站人的模板带起来掉下来,掉下来的目标平着结结实实的砸在了彭泽林带着篾质安全帽的头上。
看着一下子被砸到的同伴,下面的两个人也都被突如其来的状况砸懵了,不知道施救,也没有想起来喊人,等了几分钟看着被砸的人还没有反应,他们才惊醒过来,大叫着“砸死人啦”、“砸死人啦”,等上面的人发现底下出了事故后,赶紧吩咐下面的两人把伤员抬上翻斗车,挂在吊篮上慢慢吊上来,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放平了他,有人用手试试鼻孔说“还有气”,一个年纪大点的让大家帮忙抬到阴凉的地方平放着,“不要惊动他,是砸晕了,一会儿该过来了”。
迷迷糊糊中过了一会儿,似是有人背起他,不知往哪里走,等放他下来时睁眼瞅瞅,原来是自己住的工棚,那工友叫他躺下休息,别乱动。他问工友队长会不会扣工日,回答说想必不会扣他的工日。“唉,都差点被砸死了,还在乎半个工日,真是要钱不要命的主啊!”工友摇摇头出去了。
是啊,要是今天忘记带安全帽了,或者是那块板子不是平着掉下而是垂直砸在头上,那就不会单单是被砸晕的结果了。假如钢丝绳或挂钩断了呢,彭泽林有些不敢往下想了,他不是那种胆大妄为之辈,毕竟有一副灵活的大脑,只是现在被砸懵了,不能清晰的理清头绪
晚上队长回来,知道了有人被砸伤的情况,过来看了看,摸摸头问了几句说:“没什么大问题,当时就是被砸晕了,好好的休息两天,休息的这两天还给你记工”。感激的点头,有时一阵头晕。
躺了一天,感觉没啥事,第三天就又和大家一起上班干活了。接下来的绑扎钢筋对他不算很陌生,拿起扎勾熟练的绞着很正规的结,让甲方的技术员很是赞赏,称赞他是个不错的钢筋工,能得到技术员的认可,算是出人头地的啦,彭泽林兴奋了一大阵子。
第一次见到大板钢模板,思索着如何接头、如何加固,与队长探讨还需要购买哪些材料和工具,他敏捷的思路、切实可行的工序衔接让工头对他刮目相看,想他年纪轻轻的就有这副头脑,将来一定是棵做技工的好苗子。
伙房里有个与他玩的最好的工友叫杜明,老家是周党的,杜明老说彭泽林的身子弱,需要加强锻炼,所以每天都喜欢拉他去工棚后面老远的泡桐树林里,跟着他学拳。杜明打小就和哥哥一起跟着他爸学洪拳,现在他的拳已经有些火候了,虽然对拳术一窍不通,但是看见他行拳所带过的拳风,还是每每紧张的很,有的也是羡慕。
按照杜明讲的套路,先练习扎马步,然后教他洪拳的八式开拳式,马步是练不扎实的,就连自己照葫芦画瓢的出拳,也还是什么架子也使不出来,搞的他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每到他泄气时,杜明就劝他要有耐心,说自己是练过二十多年才有现在的成绩,练拳练的就是耐心劲,等他练习惯了就能强身健体。时间一长,他也能稳下心来学拳,虽然还是没有什么拳风之类明显的改变,但自己的下盘稳了,身板也较之之前直了许多,行走间有些军人的风姿。
不知不觉间已过去三个多月了,打完了混泥土,配合推土机回填好了土方后,工程也算告一段落,再进行的是机器安装,那类活甲方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和队伍干,彭忠诚他们施工队的工作也结束了,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简单的结束会,告诉他们工钱得过一段时间才能领,让大家先回家,等他领到工程款后回去挨家挨人送回去。
临走的晚上吃了一顿最实惠的大餐,比过年的年夜饭还要丰盛,饱餐了一顿。吃晚饭后每人领了十块钱,算是预支的工钱,第二天各自都坐车回家了。
回到家,将坐车没用完的九块九毛钱交给了老妈妈,和母亲说了工头没算账的事,也告诉二叔多留意彭忠诚啥时间回来送钱等等。便问起家里还有啥活要干的,母亲说就是没有柴火了。
属于大别山的余脉,每年冬天气温都较平原地区低近十度,所以这里的住户每家每户都会提前储存一垛垛的劈材,以备过冬时的取暖防寒。所谓劈材,就是山上砍回的麻栗树、松树、树兜子之类的能烧火的柴火。
看着没积存多少劈材,想想往年那冻死人的难过劲,二话没说就扛起大锄翘了辕子(“辕子”是三只腿约一米高能装东西可以挑、背的简易搬运工具)上山去挖树兜子。
记得原来每年秋后到了挖树兜子的时候就头痛,人家有力气的十来分钟挖一棵,他却半小时也挖不出来一棵,到最后都是琢成了“丝瓜颅”,没有一个完整的。
现在出去历练了几趟,自觉着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干这样的活已经没有什么难的啦,小半天也挖了一满辕子的树兜子,有松树的,有黄莺条的,也有栗树的,一天几辕子的收获,没几天也堆了一大堆,估计只要不连着下几场大雪,存柴应该够烧一个冬天的啦。
83年的“年”还是不早不晚的来了,相比往年不是很冷,过年走亲戚拜年的络绎不绝,平时不算拥挤的集上连班车都进不来,南来北往的人新年味很浓,庄稼人的那股醇厚的亲切劲感染着所有人,就连平常不是很熟的人碰上了也连忙打招呼,互道声“过年好“,彼此都热情的不得了。
和往年一样,所有的亲戚都要去拜年的。今年不用紧吧着时间做作业,也不用一连算计着几天走那几家的人家,还要赶在农历初八前回来,不能耽误了上学报名的时间,所以心情也就相对的轻松了许多。
正月十二的去河那边共爷的大姐家拜年时,知道了已经下学的弟弟没有什么出路,大姐便让姐夫帮他给搞建筑的拜把子兄弟董新政打个招呼,让他年后带着小兄弟在他手下的工地里打小工,也算帮了二叔、二娘一个忙。
姐夫黄先立也没叫大家失望,果然联系上了董老板,答应过了十五就上班,不远,就在街上盖养老院的活,到时候去帮忙活灰帮小工。
难得的谋划好了干活的路子,心情无比愉悦起来,中午时被几个哥哥拿来消遣了,大家你劝一杯,我劝一杯的让他不好意思推辞不喝,菜还没上齐,就被灌了个酩酊大醉。
前天去涩港姑妈家就被几个哥灌醉了,那是他第一次学喝酒,后来几个哥还有表兄都被姑妈骂了,姑妈很喜爱自己这个小侄儿,从小看着长大的,一直都是那么懂事,所以看见当老大的那几个大侄子起哄作弄他时,便笑着骂他们打伙儿欺负小的。今天是生平第二次喝酒,又让他们糊弄着灌翻了,吐的一塌糊涂,害的大姐家的地板又得拖上好几遍了。
回家一连睡了几天透还是昏昏的,没有喝过酒的他一连喝醉两次,就算是老喝家也会很伤身体的。农村的正月十五是与过年一样的看重,称为十五“大祀年”,中午,二叔烧了供神的香纸,叫他放炮,吃了十五饭便算是一个新年过完了,也是到了该干嘛干嘛的时候。
刚放完炮,湾里就有人喊他上街看玩龙的。往年每年正月十五乡里都会拿些钱办一些文艺活动,像“玩龙的”、“玩狮子的”,有时还有“玩船的”,每年他也都会和大家一起赶集看热闹,今天头还晕,便推辞没去,吃完饭就又睡了。
第九章 首次被偷
九首次被偷
下大雪的原因开工推迟到了正月底,每天早上去工地,晚上下了班回家,中午工地管伙,除了吃饭,每天发一块五毛钱的工钱,相比一起帮小工的要高三毛钱,理应是董老板看在和黄哥是拜把子亲戚的份上硬多开给他的,这样的好事继续了不到一月。
不是养老院的工程结束了,原来人罗湾的彭守珠三哥找人去柳林后勤部搞拆房活,听说那边的二老板是他女婿张成国,他那工地是按劳取酬发工钱,肯定要比在街上干小工挣钱些,彭泽林就跟着二哥彭守国报了名,同去的还有本生产队的队长彭乃前,父族的认识的夜曲了几个,一行三十多个人浩浩荡荡的挺进后勤部。
除了这几年在电影里看见过英勇献身的那些解放军,没见过军人的他平常感觉中军队的人都是很神秘的,尤其对后勤部了解的就更少了。
第一次看见成排的几十个威武的军人出操,着实让乡里人开了眼界:整齐高昂的喊操声、雄壮有力的出操步,配上今年才换的新式制服,一副副年轻的面孔,给人不怒犹威的袭人煞气,看的彭泽林心里为没有参军后悔不迭,听说当兵不但每年发好几套让人眼馋的制服,而且每月还有钱发,多好的事啊!
每天出完操都可以在水池子旁见到他们一个个的笑脸,也没有传说的那样难以接近,特别是基建科的那些当官的都很平易近人的,有时老板给烟他们也抽,后来听说那个黄科长还给老板多开有工程量,难怪当初成天在工人面前板着脸的老板当时总是有事没事的往基建科跑,小道消息说他和那军官搭上了亲戚,没人的时候都是兄弟长兄弟短的称呼。就连每天登记我们活量的那个老板的小姨子李三毛也喜欢往部队人住的地儿去,还带回一套新军装想大伙儿炫耀。
“小骚货,和她姐一样都是被男人包养的货色”,比较了解她家背景的守珠三哥很没人情味地骂她。当然是背着她的面当我们跟前说的。大家都知道彭守珠喜欢说些荤话,他有一句话很经典:“男人都要找女人干啥?女人的那和一块猪肉穿个窟窿有么子区别?”很是被人炒作了一段时间。
后勤部的活干有一个多月完成了,二老板来结算了大家伙的工钱便解散了人。彭泽林把从工地偷偷拿的一个崭新的八磅大锤带回了家,听二哥说这是部队军工厂生产的东西,很耐用的,他头几天回家时带走了一个。
没活干了就同大哥二哥一起在团山包开石窝打石头,打下来的石头卖给附近盖房子的人,买回去下地基用。
打石头是个辛苦活,每天起早贪黑的不算,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最危险的装炮药是大哥的,点炮也是他和二哥干,老三没经验连边都没让沾。他只负责在他们点炮的时候在很远的路上看着,不让行人走进危险段就行。再有的就是炒zha药,将硫酸高温熔化,掺入谷壳或树沫,控制不好一点就能燃着,这活只有走南闯北的大哥彭守荣才能胜任的啦。
零零星星的打了几个月的石头,六月初,原来在柳林一起干过活的人罗湾的彭乃纯叫他一起去信阳,还是跟他姐夫张成国干。工地好像也属于部队的活,是一个叫什么“武汉基地医院”的家属楼。
在信阳的工地上他又经过了一生里第三次受伤,在外墙架子上勾缝时从三楼高的架子上掉了下来,要不是有一块竹夹板一起溜下,在他落地前恰好是站在竹夹板上,非把他摔个半死不可。承包木工的老板高耀驰把搭架子的几个民工狠骂了一顿,骂归骂,摔疼的屁股可是别人替不了的。
一个月就受伤了两次,第二次受伤是在转来信阳前没多久时候的事。当时还在柳林后勤部里干活,那天的活是清理废墟里还能利用的整块砖头,当清到礼堂那边,他看到有两根电线断在地上,心想部队上肯定对安全保护上很负责任,不应该还有电的。因怕有电,不放心地把两根电线对着半死的青蛙点点,没发现有啥异常,就一手捏了一根,一下子麻的他摔手不迭,差点把自己的小命都玩完了。在场的几个人都说他傻,其实也不是,都是他太相信部队的军事化管理了,谁能知道拆迁的地方还通着电呢?
在信阳工地干了快两月,还没一个月的工日,等到放假算账,领了二十四块三毛钱的工钱,彭泽林和本大队的伙伴董效有一起去汽车站买第二天回家的车票。董效有买的是直到彭新的,一块二毛钱,为了省钱,他宁愿多走六里多路只买了九毛钱回涩港的车票。口袋里装着剩下的二十三块四毛钱准备去车站旁的小吃店里吃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