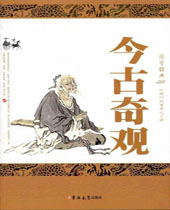今古奇观-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杀生报主意何如?解道功成万骨枯。
试听沙场风雨夜,冤魂相唤觅头颅。
杨顺见书大怒,扯得粉碎。
却说沈炼又做了一篇祭文,率领门下子弟,备了祭礼,望空祭奠那些冤死之鬼。又作《塞下吟》云:
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已著劳。
不斩单于诛百姓,可怜冤血染霜刀。
又诗云:
本为求生来避虏,谁知避虏反戕生!
早知虏首将民假,悔不当时随虏行。
杨总督标下有个心腹指挥,姓罗,名铠,抄得此诗并祭文,密献于杨顺。杨顺看了,愈加怨恨,遂将第一首诗改窜数字,诗曰:
云中一片虏烽高,出塞将军枉著劳。
何似借他除佞赋,不须奏请上方刀。
写就密书,连改诗封固,就差罗铠送与严世蕃。书中说:“沈炼怨恨相国父子,阴结死士剑客,要乘机报仇。前番鞑虏入寇,他吟诗四句,诗中有借虏除佞之语,意在不轨。”世蕃见书大惊!即请心腹御史路楷商议。路楷曰:“不才若往按彼处,当为相国了当这件大事。”世蕃大喜,即分付都察院:“便差路楷巡按宣大。”临行,世蕃治酒款别,说道:“烦寄语杨公,同心协力,若能除却这心腹大患,当以侯伯世爵相酬,决不失信于二公也。”路楷领诺。不一日奉了钦差敕命,来到宣府到任,与杨总督相见了。路楷遂将世蕃所托之语,一一对杨顺说知。杨顺道:“学生为此事,朝思暮想,废寝忘餐,恨无良策,以置此人于死地。”路楷道:“彼此留心。一来休负了严公父子的付托,二来自家富贵的机会,不可挫过。”杨顺道:“说得是!倘有可下手处,彼此相报。”当日相别去了。
杨顺思想路楷之言,一夜不睡。次日坐堂,只见中军官报道:“今有蔚州卫拿获妖贼二名解到辕门外,伏听钧旨。”杨顺道:“唤进来。”解官磕了头,递上文书。杨顺拆开看了,呵呵大笑。这二名妖贼,叫做阎浩、杨胤夔,系妖人萧芹之党。
原来萧芹是白莲教的头儿,向来出入虏地,惯以烧香惑众,哄骗虏酋俺答,说自家有奇术,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颓。虏酋愚甚,被他哄动,尊为国师。其党数百人,自为一营。俺答几次入寇,都是萧芹等为之向导,中国屡受其害。先前史侍郎做总督时,遣通事重赂虏中头目脱脱,对他说道:“天朝情愿与你通好,将俺家布粟换你家马,名为‘马市’。两下息兵罢战,各享安乐,此是美事。只怕萧芹等在内作梗,和好不终。那萧芹原是中国一个无赖小人,全无术法,只是狡伪。哄诱你家抢掠地方,他于中取事。郎主若不信,可要萧芹试其术法。委的喝得城颓,咒得人死,那时合当重用;若咒人人不死,喝城城不颓,显是欺诳,何不缚送天朝?天朝感郎主之德,必有重赏。‘马市’一成,岁岁享无穷之利,煞强如抢掠的勾当。”脱脱点头道:“是。”对郎主俺答说了,俺答大喜。约会萧芹,要将千骑随之,从右卫而入,试其喝城之技。萧芹自知必败,改换服色,连夜脱身逃走,被居庸关守将盘诘,并其党乔源、张攀隆等拿住,解到史侍郎处。招称妖党甚众,山陕畿南处处俱有,一向分头缉捕。
今日阎浩、杨胤夔亦是数内有名妖犯。杨总督看见获解到来,一者也算他上任一功,二者要借这个题目,牵害沈炼,如何不喜?当晚就请路御史来后堂商议,道:“别个题目摆布沈炼不了,只有白莲教通虏一事,圣上所最怒。如今将妖贼阎浩、杨胤夔招中窜入沈炼名字,只说浩等平日师事沈炼,沈炼因失职怨望,教浩等煽妖作幻,勾虏谋逆。天幸今日被擒,乞赐天诛,以绝后患。先用密禀禀知严家,教他叮嘱刑部作速覆本。料这番沈炼之命,必无逃矣。”路楷拍手道:“妙哉,妙哉!”两个当时就商量了本稿,约齐了同时发本。严嵩先见了本稿及禀贴,便教严世蕃传语刑部。那刑部尚书许论,是个罢软没用的老儿,听见严府分付,不敢怠慢,连忙覆本,一依杨、路二人之议”圣旨倒下:妖犯着本处巡按御史即时斩决。杨顺荫一子锦衣卫千户;路楷纪功,升迁三级,俟京堂缺推用。
话分两头。却说杨顺自发本之后,便差人密地里拿沈炼于狱中。慌得徐夫人和沈衮、沈褒没做理会,急寻义叔贾石商议。贾石道:“此必杨、路二贼为严家报仇之意。既然下狱,必然诬陷以得罪。两位公子及今逃窜远方,待等严家势败,方可出头。若住在此处,杨、路二贼,决不干休。”沈衮道:“未曾看得父亲下落,如何好去?”贾石道:“尊大人犯了对头,决无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为重,岂可拘于小孝,自取灭绝之祸?可劝令堂老夫人,早为远害全身之计。尊大人处,贾某自当央人看觑,不烦悬念。”二沈便将贾石之言,对徐夫人说知。徐夫人道:“你父亲无罪陷狱,何忍弃之而去?贾叔叔虽然相厚,终是个外人。我料杨、路二贼奉承严氏,亦不过与你爹爹作对,终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亲倘然身死,骸骨无收,万世骂你做不孝之子,何颜在世为人乎?”说罢,大哭不止”沈衮、沈褒齐声恸哭。贾石闻知徐夫人不允,叹惜而去。
过了数日,贾石打听的实,果然扭入白莲教之党,问成死罪。沈炼在狱中大骂不止。杨顺自知理亏,只恐临时处决,怕他在众人面前毒骂,不好看相。预先问狱官责取病状,将沈炼结果了性命。贾石将此话报与徐夫人知道,母子痛哭,自不必说。又亏贾石多有识熟人情,买出尸首,嘱付狱卒:“若官府要枭示时,把个假的答应。”却瞒着沈衮兄弟,私下备棺盛殓,埋于隙地。事毕,方才向沈衮说道:“尊大人遗体已得保全,直待事平之后,方好指点与你知道,今犹未可泄漏。”沈衮兄弟感谢不已。贾石又苦口劝他弟兄二人逃走,沈衮道:“极知久占叔叔高居,心上不安。奈家母之意,欲待是非稍定,搬回灵枢,以此迟延不决。”贾石怒道:“我贾某生平,为人谋而尽忠,今日之言,全是为你家门户,岂因久占住房,说发你们起身之理?既嫂嫂老夫人之意已定,我亦不敢相强。但我有一小事,即欲远出,有一年半载不回,你母子自小心安住便了。”觑着辟上贴得有前、后《出师表》各一张,乃是沈炼亲笔楷书。贾石道:“这两幅字可揭来送我,一路上做个纪念。他日相逢,以此为信。”沈衮就揭下二纸,双手折迭,递与贾石。贾石藏于袖中,流泪而别。原来贾石算定杨、路二贼设心不善,虽然杀了沈炼,未肯干休,自己与沈炼相厚,必然累及。所以预先逃走,在河南地方宗族家权时居住。不在活下。
却说路楷见刑部覆本,有了圣旨,便于狱中取出阎浩、杨胤夔斩讫,并要割沈炼之首,一同枭示。谁知沈炼真尸已被贾石买去了,官府也那里辨验得出?不在话下。
再说杨顺看见止于荫子,心中不满,便向路楷说道:“当初严东楼许我事成之日,以侯伯爵相酬。今日失言,不知何故?”路楷沉思半晌,答道:“沈炼是严家紧对头,今止诛其身,不曾波及其子,斩草不除根,萌芽再发。相国不足我们之意,想在于此。”杨顺道:“若如此,何难之有?如今复上个本,说沈炼虽诛,其子亦宜知情,还该坐罪,抄没家私。庶国法可伸,人心知惧。再访他同射草人的几个狂徒,并借屋与他住的,一齐拿来冶罪。出了严家父子之气,那时却将前言取赏,看他有何推托?”路楷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乘他家属在此,一网而尽,岂不快哉!只怕他儿子知风逃避,却又费力。”杨顺道:“高见甚明。”一面写表申奏朝廷,再写禀帖到严府知会,自述孝顺之意;一面预先行牌保安州知州,着用心看守犯属,勿容逃逸。只等旨意批下便去行事。诗云:
破巢完卵从来少,削草除根势或然。
可惜忠良遭屈死,又将家属媚当权。
再过数日,圣旨下了。州里奉着宪牌,差人来拿沈炼家属,并查平素往来诸人姓名,一一挨拿。只有贾石名字,先经出外,只得将在逃开报。此见贾石幾之明也。时人有诗赞云:
义气能如贾石稀,全身远避更知几?
任他罗网空中布,争奈仙禽天外飞?
却说杨顺见拿到沈衮、沈褒,亲自鞠问,要他招承通虏实迹。二沈高声叫屈,那里肯招?被杨总督严刑拷打,打得体无完肤。沈衮、沈褒熬炼不过,双双死于杖下。可怜少年公子,都入枉死城中。其同时拿到犯人,都坐个同谋之罪。累死者何止数十人!幼子沈展尚在襁褓,免罪,随着母徐氏,另徙在云州极边,不许在保安居住。
路楷又与杨顺商议:“沈炼长于沈襄,是绍兴有名秀才。他时得地,必然衔恨于我辈。不若一井除之,永绝后患。亦相国知我用心。”杨顺依言,便行文书到浙江,把做钦犯,严提沈襄来问罪。又分付心腹经历金绍,择取有才干的差人,赍文前去,嘱他中途伺便,便行谋害,就所在地方,讨个病状回缴。事成之日,差人重赏。金绍许他荐本超迁。
金绍领了台旨,汲汲而回。着意的选两名积年干事的公差,无过是张千、李万,金绍唤他到私衙,赏了他酒饭,取出私财二十两相赠。张千、李万道:“小人安敢无功受赐?”金绍道:“这银两不是我送你的,是总督杨爷赏你的,教你赍文到绍兴去拿沈襄。一路不要放松他,须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回来还有重赏。若是怠慢,总督老爷衙门不是取笑的,你两个去回话。”张千、李万道:“莫说总督老爷钧旨,就是老爷分付,小人怎敢有违?”收了银两,谢了金经历,在本府认领下分文,疾忙上路,往南进发。
却说沈襄,号小霞,是绍兴府学廪膳秀才。他在家久闻得父亲以言事获罪,发去口外为民,甚是挂怀。欲亲到保安州一看,因家中无人主管,行止两难。忽一日,本府差人到来,不由分说,将沈襄锁缚,解到府堂。知府教把文书与沈襄看了备细,就将回文和犯人交付原差,嘱他一路小心。沈襄此时方知父亲及二弟,俱已死于非命,母亲又远徙极边,放声大哭。哭出府门,只见一家老小,都在那里搅做一团的啼哭。原来文书上有“奉旨抄没”的话,本府已差县尉封锁了家私,将人口尽皆逐出。沈小霞听说,真是苦上加苦,哭得咽喉无气。霎时间,亲戚都来与小霞话别。明知此去多凶少吉,少不得说几句劝解的言语。小霞的丈人孟春元取出一包银子,送与二位公差,求他路上看顾女婿。公差嫌少不受。孟氏娘子又添上金簪子一对,方才收了。沈小霞带着哭,分付孟氏道:“我此去死多生少,你休为我忧念,只当我已死一般,在爷娘家过活。你是书礼之家,谅无再醮之事,我也放心得下。”指着小妻闻淑女,说道:“只这女子,年纪幼小,又无处着落,合该教他改嫁。奈我三十无子,他却有两个半月的身孕。他日倘生得一男,也不绝了沈氏香烟。娘子,你看我平日夫妻面上,一发带到他丈人家去住几时。等待十月满足,生下或男或女,那时凭你发遣他去便了。”话声未绝,只见闻氏淑英说道:“官人说那里话!你去数千里之外,没个亲人朝夕看觑,怎生放下?大娘自到院家去,奴家情愿蓬首垢面,一路伏待官人前行。一来官人免致寂寞,二来也替大娘分得些忧念。”沈小霞道:“得个亲人做伴,我非不欲。但此去多分不幸,累你同死他乡,何益?”闻氏道:“老爷在朝为官,官人一向在家,谁人不知?便诬陷老爷有些不是的勾当,家乡隔绝,岂是同谋?妾帮着官人到官申辩,决然罪不至死。就使官人下狱,还留贱妾在外,尚好照管。”孟氏也放丈夫不下,听得闻氏说得有理,极力撺掇丈夫带淑女同去。沈小霞平日素爱淑女有才有智,又见孟氏苦劝,只得依允。
当夜,众人齐到孟春元家,歇了一夜。次早,张千、李万催趱上路。闻氏换了一身布衣,将青布裹头,别了孟氏,背着行李,跟着沈小霞便走。那时分别之苦,自不必说。一路行来,闻氏与沈小霞寸步不离,茶汤饭食,都亲自搬取。张千、李万初还好言好语,过了扬子江,到徐州起旱,料得家乡已远,就做出嘴睑来。呼么喝六,渐渐难为他夫妻两个来了。闻氏看在眼里,私对丈夫说道:“看那两个泼差人,不怀好意。奴家女流之辈,不识路径,若前途有荒僻旷野的所在,须是用心提防。”沈小霞虽然点头,心中还只是半疑不信。
又行了几日,看见两个差人不住的交头接耳,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