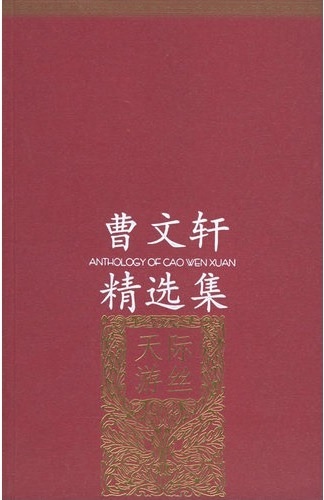曹文轩精选集-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的话人们不能不信,于是众人皆认定:“丈”与“父”属豆腐一碗,一碗豆腐。
刘某人在八们先生游说时,躲在草垛里不敢出来。
父亲又重回小学校做了先生。
刘某人找到挑糖担子的李某人:“你念过四年私塾,而且是全年的。曹小汉才念三年私塾,还是寒学。本该由你做先生,可你却挑糖担子走相穿巷地寒碜。”
这天下雨——他二人知道天下雨外面不会有行人,就闯到了父亲的小学校,当着众学生的面就开始羞辱父亲:“一个捉鱼的,也能做先生!”“字写得不错嘛,跟蚯吲爬似的。”“那字写错了,白字大先生。”“瞧瞧,瞧瞧,不就穿件黑棉袄嘛!”
学生们便立即用眼睛去看父亲身上那件黑棉袄。
请你们出去!“父亲说。
他们笑笑,各自找了个空位子坐下了:“听听你的课。”
父亲忽然发现他是有几十个学生的,对小八子们说:“还不把他们二人轰出去!”
学生们立即站起,朝刘某人与李某人走过去。那时的学生上学晚,年龄偏大,都是有一身好力气的人了。二人一见,赶紧溜走。
父亲追出门,见他们远去,便转身回教室,但转念—想,又追了出来,并大声喊:“有种的,站住!”把脚步声弄得很响,但并不追上。
河两岸的人都出来看,像看一场戏。
事后,那几位先生都看见你在追他二人,他二人狼狈逃窜了。
寒假过后,区里开全体先生会,文教干事宣布了先生们的调配方案(每年—次)。八位先生有的从完小调到初小,有的从双小降到剃、,有的从离家近的地方调到了离家远的地方……最后宣布:新分来了几个师范生,师资不缺了,曹先生不再做先生了。
众人不服。文教干事说:“这是区里决定的。”
散了会,八位先生都不回,走向坐在那儿动也不动的父亲,说:“散会了。”
父亲朝他们笑笑:“我还是喜欢捉鱼。”
“走。”
“上哪儿?”
“酒馆。我们八个人今天请你。”
进了酒馆,父亲心安理得地坐着不动,笑着,只看八位先生抢着出钱。最后八位先生说好:八人平摊。
他们喝着洒,都显得很快乐。
窗外,飘起初春的雨丝,细而透明,落地无声。
“以后想吃鱼,先生们说话。”父亲挨个与他们碰杯。
无话。
李先生先有了几分醉意,眯着眼睛唱起来。其他几位先生就用筷子合着他的节奏,轻轻地敲着酒杯。父亲就笑着看他们八位,觉得一个个全都很可敬。
李先生唱出了眼泪,突然不唱了。
依旧无话。
窗外春雨渐大,—切皆朦胧起来。
高先生突然—拍桌子:“桂生(我父亲的大名)兄……”
父亲一震。他一直将他们当长辈尊待,没想到他们竟以兄相称,赶紧起身:“别,别别别,折煞我了。”
高先生固执地:“桂生兄,事情还不一定呢!”
“不—定!”众人说。
第二日,八位先生又开始了一次游说。这次游说,极有毅力与耐心。他们从村里游说到乡里,从乡里游说到区里,又从区里游说到县里。他们分散开去,又带动起一帮先生来游说。他们带着干粮,甚至露宿途中,—个个满身尘埃。他们的神情极执著。
此举,震动了十八里方圆几个月后,副区长调走了。本想换一个区,可哪个区也不要。他只好自己联系,到邻县一个粮食收购站做事去了。
刘某人从此好好做先生。
从此,父亲与八位先生结了忘年之交。
从此,父亲又做了先生。直到他去世,这地方上的人—直叫他“曹先生”或“二先生”。
—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北京大学燕北园
天际游丝——读卡尔维诺
'塔罗纸牌'
一群看来都十分古怪的人,穿越了一片密林,来到了一座神秘的城堡。而这次穿越,是以每个人失去说话能力为代价的──围着餐桌而坐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失聪变聋。但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向他人倾诉的欲望。此时,大概是城堡的主人,拿出了一副塔罗纸牌放在了桌上,这副牌一共七十八张,每张上都印有珍贵的微型画,有国王、女王、骑士、男仆、宝杯、金印、宝剑和大棒等。他示意,每一个愿意讲述自己故事的人,都可以通过塔罗纸牌上的图案,来向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纸牌上的图案,可以充当一个乃至几个角色和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组合中,它们代表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意思。于是游戏开始,就凭这七十八张纸牌,他们分别讲述了“受惩罚的负心人”、“出卖灵魂的炼金术士”、“被罚入地狱的新娘”、“盗墓贼”、“因爱而发疯的奥尔兰多”、“阿斯托尔福在月亮上”等奇特的故事。
这就是卡尔维诺的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
在《命运交叉的饭馆中》,他继续使用这副纸牌。那些因穿越密林而失去言语的人纷纷抢着可以表述他们各自心中故事的纸牌,又讲了“犹豫不决者”、“复仇的森林”、“幸存的骑士”、“吸血的王国”等奇特的故事。
这七十八张可以任意进行组合的纸牌,似乎无所不能。它完全可以替代语言,完成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所有事件和所有意思的表达,并且极其流畅,使在场人心领神会。
无论是哪一组、哪一系列,它们总会在一点上发生交叉,即在一个点上,呈现出他们具有共同的命运。
“饭馆”的组合原则与“城堡”有别。
卡尔维诺还想写《命运交叉的汽车旅店》。但不再是用塔罗纸牌,而是借用一张报纸上的连环画版。那些在汽车旅店中因一场神秘的灾难而吓得不能言语的人,只能指着连环画的画面向他人讲述:他们每个人的讲述路线不一样,或是跳着格讲,或是按竖线讲,或是按横线讲,或是按斜线讲。
卡尔维诺是我所阅读的作家中最别出心裁的一位作家。在此之前,我以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格拉斯、米兰·昆德拉,都属于那种“别出心裁”一类的作家。但读了卡尔维诺的书,才知道,真正别出心裁的作家是卡尔维诺。他每写一部作品,几乎都要处心积虑地搞些名堂,这些名堂完全出乎人的预料,并且意味深长。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一生不知疲倦地搞出一些人们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名堂。这些名堂绝对是高招,是一些天才性的幻想,是让人们望尘莫及的特大智慧。
我总有一种感觉,卡尔维诺是天堂里的作家。对于我们而言,他的作品犹如天书。他的文字是一些神秘的符号,在表面的形态之下,总有着一些神秘莫测的奥义。我们在经历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阅读经验。他的文字考验着我们的智商。他把我们带入一个似乎莫须有的世界。这个世界十分怪异,以至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总会有一种疑问:在我们通常所见的状态背后,究竟还有没有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另有逻辑,另有一套运动方式,另有自己的语言?
《看不见的城市》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小说──
忽必烈汗的帝国,疆土辽阔无垠。他无法对他的所有城市一一视察,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天下究竟有多少座城市。于是他委托意大利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代他去巡视这些城市,然后向他一一描述。这个基本事实是虚假的。
现在,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坐到了一起。马可·波罗开始讲他所见到的城市──严格来说,不是他所见到的城市,而是他所想像的城市。小说在格式上,用两种字体进行。一种字体呈现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对话,一种字体纯粹呈现马可·波罗所描绘的城市,后者有许多个片段。这些片段都是各自独立的。我们可以将它们当作优美的散文来阅读,而幕间式的忽必烈汗与马可·波罗的对话,则充满诗意与哲理,像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十分精彩。
这些城市只可能在天国,而不可能在人间。它们美丽、充满童话色彩:“一座台阶上的城市,坐落在一个半月形的海湾,常有热风吹过那里。……一个像大教堂那么高的玻璃水池,供人们观看燕鱼游水和飞跃的姿态,并由此占卜吉凶;一棵棕榈树,风吹树叶,竟弹奏出竖琴之声;一座广场,马蹄形环绕着大理石桌子,上面铺了大理石台布,摆着大理石制的食品和饮料。”又一座城市,这是一座“月光下的白色的城市,那里的街巷互相缠绕,就像线团一样”。这座城市的建造,只是复现人们在梦境中所看到的。又一座城市,这座城市非常奇怪:没有墙壁,没有屋顶也没有地板,只有像树林一般的管道,每根管子的末端都是水龙头、沐浴喷头、虹吸管或溢流管。这番情景使人联想到一定是水管工在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还未等到泥瓦工来到便先撤了,而实际上泥瓦工永远也没有到场。这是一幅后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画。又一座城市,这座城市显得神秘莫测:城中有一块地毯,而你如果细心观察,将会发现这座城市全都反映在这块地毯上,丝毫不差。再来看一座城市,它的名字叫贝尔萨贝阿。这座城市的居民相信,实际上有三座贝尔萨贝阿,除了地上一座,另一座在天上,那是一座黄金之城,有白银的门锁和钻石的城门,一切都雕镂镶嵌。还有一座则在地下。……
全书九章,共叙述城市五十五座。
书中的所有数字,都具有隐喻性与象征性。
这是些“看不见的”城市。他们是马可·波罗和忽必烈汗想像的产物。这两个人,是幻想家,是激情主义者,同时也都是诗人。他们坐在那里,海阔天空。忽必烈汗在马可·波罗的想像中又进一步想像,同样如此,马可·波罗也在忽必烈汗的想像中展开更辽阔的想像空间。忽必烈汗本是一个听者,但经常忘记他的角色而打断马可·波罗:你且停住,由我来说你所见到的城市。
像风筝一样轻盈的城市,像花边一样通透的城市,像蚊帐一样透明的城市,像叶脉一样的城市、像手纹一样的城市……这些城市络绎不绝地出现在他们的想像里。它们显示着帝国的豪华与丰富多彩,同时也显示着帝国的奢侈与散乱。
天要亮了,马可·波罗说,陛下,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城市都向你一一描述了。可忽必烈汗说,不,还有一座城市你没有说──威尼斯。马可·波罗笑了,你以为我一直在讲什么?在我为您描述的所有城市中,都有威尼斯。
作品最后回到了一个沉重的耐人寻味的主题上。这个主题是为天下所有不可一世的伟大君王所设定的:当他获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时,他同时失去了所有;一颗最伟大的灵魂,同时也是一颗最空虚的灵魂。
也许卡尔维诺的文字最使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思想,而是诗性、童话色彩、游戏性、汪洋恣肆的才情四溢等。而形式上的别具一格,自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阿根廷的蚂蚁》……这些作品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小说不仅是在内容上还有极大的可能性,在形式上也有极大的可能性──甚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大到如塔罗纸牌一样,可以有无穷无尽的变化。
在形式上大做文章,这是卡尔维诺与一般小说家的区别。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他要将自己的小说在形式上做得一篇与一篇不一样,每一篇的形式都是一个独创。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他没有在一九八五年去世而活至今日,他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种新颖而别致的小说形式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伟大。因为,一个不将心思花在形式上,而只是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作品的生存经验的透彻与思想的深邃方面的小说家,一样是伟大的。他们就在那些长久延用的古老的、经典的小说形式中,照样达到了一个令人仰止的小说境界。这犹如一粒王冠上的钻石,是包在手帕中还是放在木盒里都不能影响钻石本身的价值一样。但,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有些形式是与内容无法分解的,如美学家们所说的,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些形式我们就应另当别论了。也许说一些艺术品,可以显得更为直观:那些看上去仅为形式的雕塑,它们在我们的感觉里,究竟是内容还是形式的呢?我们无法将这两者剥离。当初建造埃及金字塔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代的种种猜测仅仅就是猜测。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毫无意义的──除非是那些科学家想从中获取什么。因为在我看来,当它出现在我们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