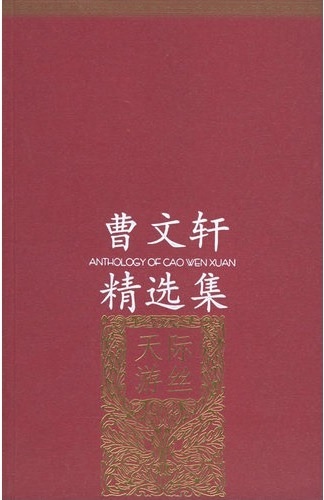曹文轩精选集-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种姿势时,可能会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景,而当身体处于彼种姿势时,就可能在那一刻回到儿时。“饭后靠在扶手椅上打盹儿,那姿势同睡眠时的姿势相去甚远……”他发现姿势奥妙无穷:姿势既可能会引起感觉上的变异,又可能是某种心绪、某种性格的流露。因此,普鲁斯特养成了一个喜欢分析人姿势的习惯。当别人去注意一个人在大厅中所发表的观点与理论时,普鲁斯特关闭了听觉,只是去注意那个人的姿势。他发现格朗丹进进出出时,总是快步如飞,就连出入沙龙也是如此。原来此公长期好光顾花街柳巷,但却又总怕人看到,因此养成了这样步履匆匆的习惯。
人在无所事事的佳境,要么就爱琢磨非常细小的问题,比如枕头的问题、姿势的问题、家具的问题,要么就爱思考一些大如天地的、十分抽象的问题。这些问题自有人类的历史的那一天就开始被追问,是一些十分形而上的问题。在普鲁斯特这里,他是将这些细小如尘埃的问题与宏大如天地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的——在那些细小的物象背后,他看到了永世不衰、万古长青的问题。
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他既需要具备一般知识分子的品质,同时又需要与一般知识分子明确区别开来。作为知识分子,他有责任注视“当下”。面对眼前的社会景观,他必须发言,必须评说与判断。“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被规定为:他必须时刻准备投入“当下”。当一个知识分子对他所处的环境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竟然无动于衷、麻木不仁时,他就已经放弃了对“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坚守。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识分子永远是强劲的驱动力。
然而,当他在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种——作家时,他则应该换上另一种思维方式。他首先必须明白,他要干的活儿,是一种特别的活儿。作家所关心的“当下”应含有“过去”与“将来”。他并不回避问题,但这些问题是跨越时空的:过去存在着,当下存在着,将来仍然会存在着。这些问题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此刻,那些琐碎的、有一定时间性和地域性的事物在他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他可以视而不见,而看到的是——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讲,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
“写小说应该写的,这是小说存在的惟一理由。”米兰·昆德拉说得千真万确。
诛犬
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我在日本东京井之頭的住宅中躺着翻看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部作品,无意中发现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世界上的许多暴力行动,是从打狗开始的。这一揭示,使我大吃一惊,并不由得想起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个故事。
那时我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却并不是我,而是油麻地镇文化站的站长余佩璋。
这个余佩璋不太讨人喜欢,因为他有空洞性肺结核。他有两种行为,总令人不快。一是他天天要用几乎是沸腾的开水烫脚。他常组织班子演戏,那时,他就会跟油麻地中学商量,将我借出来拉胡琴。与他在一起时,总听到他半命令半央求我似的说:“林冰,肯帮我弄一壶开水吗?”烫脚时,他并不把一壶开水都倒进盆中,而是先倒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分几次续进去,这样,就能保持盆中的水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还是烫的。烫脚在他说,实在是一种刻骨铭心舍得用生命换取的享受。他用一条小毛巾,拉成细细一股,浸了开水,两手各执一端,在脚丫之间来回地如拉锯似的牵、搓,然后歪咧着个大嘴,半眯着双眼,“哎呀哎呀”地叫唤,其间,夹有发自肺腑的呻吟:“舒服得不要命啦!”一双脚烫得通红。杀痒之后,他苍白的脸上显出少有的健康神色,乌嘴唇也有点儿红润起来。他说:“脚丫子痒,我就不怕。一旦脚丫子不痒了,我就得往医院抬了。”果真有几回脚丫子不痒了,他的病爆发了,口吐鲜血,抬进了医院。他的另一种行为,是让人更厌恶的。当大家团团围坐一张桌子共食时,他很不理会别人对他的病的疑虑与害怕,先将脸尽量垂到盛菜的盆子上嗅着那菜的味道,然后抓一双筷子,在嘴中很有声响地嗍一下,便朝盆里伸过去。叫人心中发堵的是,他并不就近在盆边小心地夹一块菜放入自己的碗中,不让人家有一盆菜都被污染了的感觉,而是用大幅度的动作,在盆中“哗哗”搅动起来,搅得盆中的菜全都运动起来,在盆中间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这时,他再嗍一下筷头,再搅。嗍,搅;搅,嗍……那样子仿佛在说:“我让你们大家也都吃一点结核菌,我让你们大家也都吃一点结核菌……”大家心中都梗了一块东西去吃那盆中的菜。吃完了,心里满是疑问,过好几天,才能淡忘。我理解他这一举动的心思:他是想说,他的病是不传染的,你们不用介意;他想制造出一种叫众人放心的轻松气氛来。
他也感觉到了别人的疑虑,平日里常戴一个口罩。他脸盘很大,那口罩却又很小,紧紧地罩在嘴上,总让人想起耕地的牛要偷吃田埂那边的青庄稼而被主人在它的嘴上套了一张网罩的情景。
他很想让自己的病好起来。他知道,得了这种病,吃很要紧。他穿衣服一点儿不讲究,家中也不去添置什么东西,拿的那些工资都用在了吃上。油麻地镇的人每天早上都能看见他挎一只小篮子去买鱼虾。他还吃胎盘,一个一个地吃,用水洗一洗,下锅煮一煮,然后蘸酱油吃。
油麻地镇上的人说:“余佩璋要不是这么吃,骨头早变成灰了。”
他决心把病治好,但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吃,于是就养了一群鸡。文化站有一个单独的院子,这儿既是文化站,又是他家的住宅。院子很大,几十只鸡在院子里跑跑闹闹,并不让人嫌烦。余佩璋要了镇委会食堂的残羹剩饭喂它们,喂得它们肥肥的。每隔一段时间,余佩璋就关了院门,满院子撵鸡,终于捉住一只,然后宰了,加些黄芪煨汤喝。
但这两年他很烦恼:老丢鸡。起初,他以为是黄鼠狼所为,但很快发现是被人偷的。油麻地镇很有几个偷鸡摸狗的人,八蛋就是其中一个。他守过几次夜,看到底是谁偷了他的鸡。但那几夜,油麻地镇却表现出一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文明样子来。而他一不守夜,就又丢鸡。他便站在文化站门口,朝镇上的人漫无目标地骂:“妈的,偷鸡偷到我文化站来了!谁偷的,我晓得的!”
这一天,他一下儿丢了三只鸡。
他骂了一阵,没有力气了,就瘫坐在文化站的门口不住地咳嗽。
有几条公狗在追一条母狗,那母狗突然一回头,恶声恶气地叫了两声,那些公狗便无趣地站住了。可当母狗掉头又往前走时,那些公狗又厚皮赖脸地追了上去。母狗大怒,掉过头,龇着牙,在喉咙里呜咽了两声,朝一只公狗咬去,那只公狗赶紧逃窜了。
余佩璋看着,就觉得心一跳,爬起来,回到院子里找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内有警犬,请勿入内。然后将木板挂在了院门口。他往后退了几步,见木板挂得很正,一笑。
一个消息便很快在油麻地镇传开了:文化站养了一条警犬。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也很快知道了,于是就有很多同学胆战心惊地在远离文化站大门处探头探脑地张望。谁也没有瞧见什么警犬,但谁都认定那院子里有条警犬。油麻地镇有很多狗,但油麻地镇的人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警犬。因此文化站里的警犬是通过想像被描绘出来的:“个头比土种狗大几倍,一站,像匹马驹。叫起来,声音‘嗡嗡’的,光这声音就能把人吓瘫了。一纵一纵地要朝外扑呢,把拴它的那条铁链拉得紧绷绷的。”
那天我和我的几个同学在镇上小饭馆吃完猪头肉出来,遇着了余佩璋。我问:“余站长,真有一条警犬吗?”
他朝我笑笑:“你个小林冰,念你的书,拉你的胡琴,管我有没有警犬!”
街边一个卖鱼的老头说:“这个余站长,绝人,不说他有狗,想让人上当呢。”
余佩璋再也没有丢鸡。
二
可余佩璋万万没有想到会有一场打狗运动。
打狗是人类将对人类实行残忍之前的预演、操练,还是因为其他什么?打之前,总得给狗罗织罪名,尽管它们是狗。这一回的罪名,似乎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狗跟穷人是不对付的;养狗的全是恶霸地主,而他们养的狗又是专咬穷人的。人们脑子里总有富人放出恶狗来,冲出朱门,将乞讨的穷人咬得血肉模糊的情景。狗是帮凶,理应诛戮。这理由现在看来很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很严肃的理由。上头定了期限,明文规定,凡狗,必诛,格杀勿论,在期限到达之前必须将其灭绝。油麻地镇接到通知,立即成立了一个指挥部,镇长杜长明指定管民兵的秃子秦启昌为头。考虑到抽调农民来打狗要付报酬,于是请油麻地中学的校长汪奇涵做副头,把打狗的任务交给了正不知将激情与残忍用于何处的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我们一人找了一根棍子,一个个皆露出杀气来。炊事员白麻子不再去镇上买菜,因为秦启昌说了,学生们打了狗,二分之一交镇上,二分之一留下自己吃狗肉。
油麻地一带人家爱养狗,总见着狗在镇上、田野上跑,天一黑,四周的狗吠声此起彼伏。这一带人家爱养狗,实在是因为这一带的人爱吃狗肉。油麻地镇上就有好几家狗肉铺子。到了秋末,便开始杀狗;冬天杀得更多。狗肉烀烂了,浇上鲜红的辣椒糊,一块一块地吃,这在数九寒冬的天气里,自然是件叫人满足的事情。这段时间,常见路边树上挂着一只只剥了皮的血淋淋的狗,凉丝丝的空气里总飘散着一股勾引人的血腥味。
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一想到吃狗肉,都把棍子抄了起来。大家来来回回地走,满眼都是棍子。
汪奇涵说:“见着狗就打。”
我们组织了许多小组,走向指定的范围。狗们没有想到人居然要灭绝它们,还如往常一样在镇上、田野上跑。那些日子,天气分外晴朗,狗们差不多都来到户外嬉闹玩耍。阳光下,那白色的狗,黑色的狗,黄色的狗,闪着软缎一样的亮光——我们的视野里有的是猎物。几遭袭击之后,狗们突然意识到了那无数根棍子的意思,立即停止嬉闹,四下逃窜。我们便很勇猛地向它们追杀过去,踩倒了许多麦苗,踩趴了许多菜园的篱笆。镇子上,一片狗叫鸡鸣,不时地有鸡受了惊吓,飞到了房顶上。
镇上的老百姓说:“油麻地中学的这群小狗日的,疯了!”
我拿了棍子,身体变得异常机敏。当被追赶的狗突然改变方向时,追赶的同学们因要突然改变方向而摔倒了许多,而我几乎能与狗同时同角度地拐弯。那一顷刻我觉得自己的动作真是潇洒优美。弹跳也极好,遇到水沟,一跃而过;遇到矮墙,一翻而过。
在油麻地镇的桥头,我们遇到了一只很凶的狮子狗。这狮子狗是灰色的,个头很大,像一只熊。它龇牙咧嘴地向我们咆哮着,样子很可怕。见我们朝它逼近,它不但不逃跑,还摆出一副随时扑咬我们的架势。
“女生靠后边站!”我拿着棍子一步一步地向狮子狗靠拢过去。
狮子狗朝我狂吠着。当我的棍子就要触及到它时,它朝我猛地扑过来。我竟一下儿失去了英勇,丢了棍子,扭头就逃。
有个叫乔桉的同学笑了起来,笑得很夸张。
狮子狗抖动着一身长毛,一个劲地叫着。它的两只被毛遮掩着的模糊不清的眼睛,发着清冷的光焰。它的尖利牙齿全都露出乌唇,嘴角上流着晶亮的黏液。
乔桉不笑了。看样子,狗要扑过来了。
我急忙从地上捡起两块砖头,一手一块,不顾一切地朝狮子狗冲过去。当狮子狗扑上来时,我奋力砸出去一块,竟砸中了它。它尖厉地叫唤了一声,扭头朝河边跑去。我捡回我的棍子,朝它逼过去。它“呜呜”地叫着。它已无路可退,见我的棍子马上就要劈下来,突然一跃,竟然扑到我身上,并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一股钻心的疼痛,既使我感到恼怒,也增长了我的英勇。我扔掉棍子,用手中的另一块砖头猛力地敲打着它。其中一下,击中了它的脸,它惨叫一声,松开口,仓皇而逃。
我觉得自己有点儿残忍,但这残忍让人很激动。
我的白衬衫被狮子狗撕下两根布条,胳膊上流出的鲜血将它们染得红艳艳的,在风中飘动着。
三
血腥味飘散在春天温暖的空气里,与正在拔节的麦苗的清香以及各种草木的香气混合在一起,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