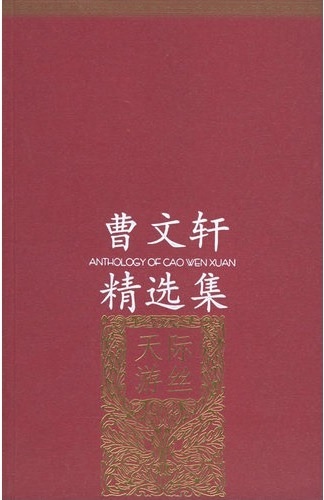曹文轩精选集-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灯笼,早晚会一盏一盏地被摘掉的,最后只剩下几根铁一样的黑枝。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枝上依然是二十八颗柿子。
又过去了十天,枝上还是二十八颗柿子。
那天,我在枝下仰望着这些熟得亮闪闪的柿子,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可思议。十多年前我家也有一棵柿子树──
这棵柿子树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给的,起初,母亲不同意种它,理由是:你看谁家种果树了?我说:为什么不种?母亲说:种了,一结果也被人偷摘了。我说:我偏种。母亲没法,只好同意我将这棵柿子树种在了院子里。
柿子树长得很快,只一年,就蹿得比我还高。
又过了一年。这一年春天,在还带有几分寒意的日子里,我们家的柿子树居然开出了几十朵花。它们娇嫩地在风中开放着,略带了几分羞涩,又带了几分胆怯。
每天早晨,我总要将这些花数一数,然后才去上学。
几阵风,几阵雨,将花吹打掉了十几朵。看到凋零在地上的柿子花,我心里期盼着幸存于枝头的那十几朵千万不要再凋零了。后来,天气一直平和得很,那十几朵花居然一朵未再凋零,在枝头上很漂亮地开放了好几天,直到它们结出了小小的青果。
从此,我就盼着柿子长大成熟。
这天,我放学回来,母亲站在门口说:“你先看看柿子树上少了柿子没有。”
我直奔柿子树,只看了一眼,就发现少掉了四颗——那些柿子,我几乎是天天看的,它们长在哪根枝上,有多大,各自是什么样子,我都是清清楚楚的。
“是谁摘的?”我问母亲。
“西头的天龙摘的。”
我骂了一句,扔下书包,就朝院门外跑,母亲一把拉住我:“你去哪儿?”
“揍他去!”
“他还小呢。”
“他还小?不也小学六年级了吗?”我使劲从母亲手中挣出,直奔天龙家。半路上,我看到了天龙,当时他正在欺负两个小女孩。我一把揪住他,并将他掼到田埂下。他翻转身,躺在那里望着:“你打人!”
“打人?我还要杀人哪!谁让你摘柿子的?”我跳下田埂,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拖起来,又猛地向后一推,他一屁股跌在地上,随即哇哇大哭起来。
“别再碰一下柿子!”我拍拍手回家了。
母亲老远迎出来:“你打人了?”
“打了。”我一歪头。
母亲顺手在我后脑勺上打了一巴掌。
过不一会儿,天龙被他母亲揪着找到我家门上来了:“是我们家天龙小,还是你们家文轩小?”
我冲出去:“小难道就该偷人家东西吗?”
“谁偷东西了?谁偷东西了?不就摘了你们家几颗青柿子吗?”
“这不叫偷叫什么?”
母亲赶紧从屋里出来,将我拽回屋里,然后又赶紧走到门口,向天龙的母亲赔不是,并对天龙说:“等柿子长大了,天龙再来摘。”
我站在门口:“屁!扔到粪坑里,也轮不到他摘!”
母亲回头用手指着:“再说一句,我把你嘴撕烂。”
天龙的母亲从天龙口袋里掏出那四只还很小的青柿子扔在地上,然后在天龙的屁股上连连打了几下:“你嘴怎么这样馋?你嘴怎么这样馋?”然后,抓住天龙的胳膊,将他拖走了,一路上,不住地说:“不就摘了几个青柿子吗?不就摘了几个青柿子吗?就像摘了人家的心似的!以后,不准你再进人家的门。你若再进人家的门,我就将你腿砸断!……”
母亲回到屋里,对我说:“当初,我就让你不要种这柿子树,你偏不听。”
“种柿子树怎么啦?种柿子树也有罪吗?”
“你等着吧。不安稳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后来,事情果然像母亲所说的那样,这棵柿子树,使我们家接连几次陷入了邻里的纠纷。最后,柿子树上,只留下了三颗成熟的柿子。望着这三颗残存的柿子,心里觉得很无趣。但,它们毕竟还是给了我和家人一丝安慰:总算保住了三颗柿子。
我将这三颗柿子分别做了安排:一颗送给我的语文老师(我的作文好,是因为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颗送给摆渡的乔老头(我每天总要让他摆渡上学),一颗留着全家人分吃(从柿子挂果到今天,全家人都在为这棵柿子树操心)。
三颗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枝头上,十分耀眼。
母亲说:“早点摘下吧。”
“不,还是让它们在树上再挂几天吧,挂在树上好看。”我说。
瘦瘦的一棵柿子树上,挂了三只在阳光下变成半透明的柿子,成了我家小院一景。因为这一景,我家本很贫乏的院子,就有了一份情调,一份温馨,一份无言的乐趣。就觉得只有我们家的院子才有看头。这里人家的院子里,都没有长什么果树。之所以有那么个院子,仅仅是用来放酱油缸、堆放碎砖烂瓦或堆放用作烧柴的树根的。有人来时,那三只柿子,总要使他们在抬头一瞥时,眼里立即放出光芒来。
几只喜鹊总想来啄那三颗柿子。几个妹妹就轮流着坐在门槛上吓唬它们。
这天夜里,我被人推醒了,睁眼一看,隐约觉得是母亲。她轻声说:“院里好像有动静。”
我翻身下床,只穿了一条裤衩,赤着上身,哗啦抽掉门栓,夺门而出,只见一个人影一跃,从院里爬上墙头,我哆嗦着发一声喊:“抓小偷!”那人影便滑落到院墙那边去了。
我打开院门追出来,就见朦胧的月光下有个人影斜穿过庄稼地,消失于夜色之中。
我回到院子里,看到那棵柿子树已一果不存,干巴巴地站在苍白的月光下。
“看见是谁了吗?”母亲问。
我告诉母亲有点像谁。
她摇摇头:“他人挺老实的。”
“可我看像他,很像他。”我仔细地回忆着那个人影的高度、胖瘦以及跑动的样子,竟向母亲一口咬定:“就是他。”
母亲以及家里的所有人,都站在凉丝丝的夜风里,望着那棵默然无语的柿子树。
我忽然冲出院门外,大声叫骂起来。夜深人静,声音显得异常宏大而深远。
母亲将我拽回家中。
第二天,那人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怀疑是他偷了那三颗柿子,闹到了我家。他的样子很凶,全然没有一点“老实”的样子。母亲连连说:“我们没有说你偷,我们没有说你偷……”
那人看了我一眼,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不就三颗柿子嘛!”
母亲再三说“我们没有说你偷”,他才骂骂咧咧地走去。
我朝柿子树狠狠踹了几脚。
母亲说:“我当初就说,不要种这柿子树。”
晚上,月色凄清。我用斧头将这棵柿子树砍倒了。从此,又将我们家的院子变成了与别人家一样单调而平庸的院子。……
面对山本先生家的柿子树,我对这个国度的民风,一面在心中深表敬意,一面深感疑惑:世界上竟能有这样纯净的民风?
那天,中由美子女士陪同我去拜访前川康男先生。在前川先生的书房里,我说起了柿子树,并将我对日本民风的赞赏,告诉了前川先生。然而,我没有想到前川先生听罢之后,竟叹息了一声,然后说出一番话来,这番话一下子颠覆了我的印象,使我陷入了对整个世界的茫然与困惑。
前川先生说:“我倒希望有人来摘这些柿子呢。”
我不免惊讶。
前川先生将双手平放在双膝上:“许多年前,我家的院子里也长了一棵柿子树。柿子成熟时,有许多上学的孩子从这里路过,他们就会进来摘柿子,我一边帮他们摘,一边说,摘吧摘吧,多吃几颗。看着他们吃得满嘴是柿子汁,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孩子们吃完柿子上学去了,我们就会站到院门口说,放了学再来吃。可是现在,这温馨的时光已永远地逝去了。你说得对,那挂在枝头上的柿子,是不会有人偷摘一颗的,但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不觉得人太谦谦君子,太相敬如宾,太隔膜,太清冷了吗?那一树的柿子,竟没有一个人来摘,不也太无趣了吗?那柿子树不也太寂寞了吗?”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心中回味着前川先生的话。他使我忽然面对着价值选择的两难困境,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又见到了山本家的柿子树。我突然地感到那一树的柿子美丽得有些苍凉。它孤独地立着,徒有一树好好的果实。从这里经过的人,是不会有一个人来光顾它的。它永不能听到人在吃了它的果实之后对它发出的赞美之辞。我甚至想到山本先生以及山本先生的家人,也是很无趣的。
我绝不能接受我家那棵柿子树的遭遇,但我对本以欣赏之心看待的山本家的柿子树的处境,也在心底深处长出悲哀之情。
秋深了,山本家柿子树上的柿子,终于在等待中再也坚持不住了,只要有一阵风吹来,就会从枝上脱落下三两颗,直跌在地上。那柿子实在是熟透了,跌在地上,顿作糊状,像一摊摊废弃了的颜色。
还不等它们一颗颗落尽,我便不再走这条小道。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里,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红瓦》中感慨良多、充满纯情与诗意地又写了柿子树——又一棵柿子树。我必须站在我家的柿子树与山本家的柿子树中间写好这棵柿子树:
在柿子成熟的季节里,那位孩子的母亲,总是戴一块杏黄色的头巾,挎着白柳篮子走在村巷里。那篮子里装满了柿子,她一家一家地送着。其间有人会说:“我们直接到柿子树下去吃便是了。”她说:“柿子树下归柿子树下吃。但柿子树下又能吃下几颗?”她挎着柳篮,在村巷里走着,与人说笑着,杏黄色的头巾,在秋风里优美地飘动着……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痴鸡
每年春天,总有那么几只母鸡,要克制不住地生长出孵小鸡的欲望。那些日子,它们几乎不吃不喝,到处寻觅着鸡蛋。一见鸡蛋,就会惊喜地“咯咯咯”地叫唤几声,然后绕蛋转上几圈,蓬松开羽毛,慢慢蹲下去,将蛋拢住,焐在胸脯下面。但许多人家,却并无孵小鸡的打算,便在心里不能同意这些母鸡们的想法。再说,正值春日,应是母鸡们好好下蛋的季节。这些母鸡—旦要孵小鸡时,便进入痴迷状态,而废寝忘食的结果是再也不能下蛋。这就使得主人恼火,于是就会采取种种手段将这些痴鸡们从孵小鸡的欲望拖拽回来。
这样行为,叫“醒鸡”。
我总记着许多年前,我家的一只黑母鸡。
那年春天,它也想孵小鸡。第—个看出它有这个念头的母亲。她几次喂食,见它心不在焉只是很随意地啄几粒食就独自走到一边去时,说:“它莫非要孵小鸡?”我们小孩一听很高兴:“噢,孵小鸡,孵小鸡了。”
母亲说:“不能。你大姨妈家,已有一只鸡代我们家孵了。这只黑鸡,它应该下蛋。它是最能下蛋的一只鸡。”
我从母亲的眼中可以看出,她已很仔细地在心中盘算过这只黑鸡将会在春季里产多少蛋,这些蛋又可以换回多少油盐酱醋来。她看了看那只黑母鸡,似乎有点为难。但最后还是说:“万不能让它孵小鸡。”
这天,母亲终于认定了黑母鸡确实有了孵小鸡的念头,并进入状态了。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她忽然发现黑母鸡不见了,便去找它,最后在鸡窝里发现了它,那时,它正—本正经、全神贯注地趴在几只尚未来得及取出的鸡蛋上。母亲将它抓出来时,那几只鸡蛋早已被焐得很暖和了。
母亲给了我—根竹竿:‘撵它,大声喊,把它吓醒。“
“让它孵吧”
母亲坚持说:“不能。鸡不下蛋,你连买瓶墨水的钱都没有。”
我知道不能改变母亲的主意,取过竹竿,跑过去将黑鸡撵起来。它在前面跑,我就挥着竹竿在后面追,并大声喊叫:“噢——!噢——!”从屋前到屋后,从竹林追到菜园,从路上追到地里。看着黑母鸡狼狈逃窜的样子,我竟在追赶中在心里觉到了一种快意。我用双目将它盯紧,把追赶的速度不断加快,把喊叫的声音不断加大,引得正要去上学的学生和正要下地干活的人都站住了看。几个妹妹起初是站在那儿跟着叫,后来也操了棍棒之类的家伙参加进来,与我—起轰赶。
黑母鸡的速度越来越慢,翅膀也耷拉了下来,还不时地跌倒。见竹竿挥舞过来,只好又挣扎着爬起,继续跑。
我终于精疲力竭地瘫坐在了草垛底下,一边喘气,—边抹着额头上的大汗。
黑母鸡钻到了草丛里,一声不吭地直将自己藏到傍晚,才钻出草丛。
但经这—惊吓,黑母鸡似乎并未醒来。它晾着双翅,咯咯咯地叫着,依旧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