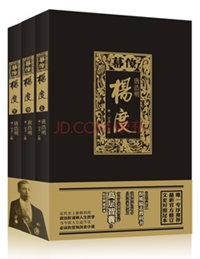杨度-第1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车走雷声不动尘,千门驰道接天津。杜鹃九死魂应在,鹦鹉余生梦尚新。
抱瓜黄台成底事,看花紫陌已无春。汉家陵阙都非故,残照西风独怆神!
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诗写得不错,在江亭壁上数以百计的题诗中可谓上乘。诗中忧国忧民的情绪十分浓烈,看来是一个失意而不失忠诚的文人写的。眼下又是西风落叶的时候,看着面前颓废的慈悲庵,陈旧的江亭,四壁上那些令人不忍卒读的游人题辞,联想到处于颠簸危殆之中毫无一丝指望的国家政治,以及多年来负岌东游求得的学问,殚精竭思设计的立宪宏图都将一无所展,杨度一时百感交集,心胸郁闷,方才与静竹共忆初恋时的美好心态被扫除得无影无踪。
“老爷,题首诗吧!”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站在杨度的面前,带着乞求的腔调望着他说。
小男孩黑瘦得吓人,上身披着一个破烂麻袋,下身穿一条破旧单裤,赤着脚,一只手端着个缺边瓷碗,碗里有些墨汁,碗边上横着一支粗糙的毛笔,一只手提着个黑木桶,桶里装着石灰水,插一个旧扫把。
京师里的穷孩子成千上万,有讨饭乞钱的,有拾荒捡破烂的,有帮人做各种小工杂活的,但用这个办法来赚两个小钱的苦孩子还从来没见过,杨度和夏寿田对望了一眼,又心酸又哀痛。
“好吧!”
“谢谢,我来刷墙!”小男孩高兴极了,忙将扫把沾满石灰水,要把壁上的这首七律刷掉。
“莫刷这里。”夏寿田赶紧制止。
“老爷,你要题哪里?”小男孩停住扫把,大眼睛骨碌骨碌地望着夏寿田。
“刷这里吧!”夏寿田指了一块文句庸鄙字迹粗劣的地方说。
“行!”小男孩三下两下刷出一块白壁来,又将笔蘸上墨,给杨度递了过去。
杨度接过笔,凝思着。
静竹说:“既然过去的《百字令》找不到了,那就再题一首新《百字令》吧!”
杨度沉默地点点头。一股从居庸关外吹来的北风破窗而入,吹得他脖子后颈冷嗖嗖的。他皱着眉头,绷紧面孔,久久地伫立不动。突然,手中的墨笔靠近了尚未全干的灰墙,一行行浑厚遒劲的碑体字出来了:
戊戌年,余与午贻同赴礼闱。余罢第,午贻高中一甲第二名。离京前夕结伴游江亭,时所谓承平岁月也,实大祸已暗伏,国人多未
窥几而已。予赋《百字令》:“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此意已寓其中。不久变生肘腋,随之帝后播迁,而今则烽烟四起。
一十二年来,国事日非,无可救也。今与午贻、静竹重游旧地,欲觅昔日所题而不可见。秋风萧瑟,汉陵不见,余再题《百字令》一阕,
以纪此游。
朋侣携手,觅当年旧迹,尘土掩了。废寺危亭卧寒雀,更接无涯枯草。惹祸博鸿,匿影扶桑,又赴洛阳道。尧都远矣,何来自取懊
恼!谁付伊周重托,神州宏图,由尔展描?昨宵一梦兼春远,梦里江山更好。南疆水清,北国原莽,西域昆仑豪!醒来依旧,西风频吹
人老。
静竹轻轻地诵读了一遍,说:“好是好,但未免太消沉了点。你今年才不过三十五岁,难道西风就把你吹老了?”
杨度苦笑着,不做声。
夏寿田说:“当年我们是一人一首,今天也不能让你专美。”
夏寿田从杨度手中取过笔。在杨度题壁的时候,榜眼公已经打好腹稿了,他不假思索,飞快写了起来:
戊戌年与皙子共游江亭。皙子叹时事多艰,余言朝政无阙,小有外侮,足以惕在位,不宜遽作亡国之音,失哀乐之正。和词云“万
顷孤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意以矫之,亦喻朝廷宜礼贤用才,以人治国。曾湘乡谓朝气不难致也。乃未几政变狱起,继以拳祸,
两宫西狩,几致亡国,始叹其见微。今与皙子再游江亭,皙子重题《百字令》,有“西风频吹人老”句,静竹惜其消沉。然国事日非,
余又遭家难,心绪或许比皙子更消沉也。
一纪过后,正黄花初开,霜打野草。废苑孤蒲新又雨,作得秋声不了。雁字南飞,声断燕岭,回望帝京渺。万里长城,犹如灰线曲
绕。弹指光阴流逝,功名无望,更兼文章夭。旧年一腔书生气,渐被岁月磨消。国难当头,家祸突兀,人世多烦恼。不如狂饮,一壶浊
酒醉倒。
静竹也把夏寿田的《百字令》轻轻吟诵了一遍,叹道:“十二年了,想不到国家不但无一点起色,反而越来越坏,也怪不得你们消沉。”
这时,岳霜跑过来说:“店老板把饭准备好了,快去吃吧!”说着就来扶静竹。
静竹也说:“苦吟了半天,也该去吃饭了!”
“走吧!”夏寿田拉起杨度衣袖就走。
“老爷,赏我几个钱吧!”
侍候笔墨的小男孩站在一旁可怜兮兮地说。
“哎呀,你看我们都忘记了!”杨度一边掏口袋,一边对夏寿田等人说,“你们先走。”
杨度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约有三四十文,都送给了那孩子。小家伙欢天喜地地鞠了一躬走了。
杨度正要转身,却忽然看到慈悲庵里走出两个出家人来:前面是一个年岁较长的和尚,后面跟着一个中年尼姑。二人来到大门外,都停了脚。
和尚双手合十说:“师妹留步,过两天我再来。”
中年尼姑久久地望着和尚,好久才说了一句:“师兄好走了。”
杨度被这一僧一尼的情景所吸引,征怔地望着出神。那和尚转过脸向江亭这边望了一眼,又朝着尼姑身边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杨度看清了这位和尚,原来竟是多年不见的故人!
“寄禅法师!”杨度惊喜地喊了一声。
和尚停步,扭头一看,也喜道:“原来是皙子!我正要找你,不料你也到江亭来了!”
当杨度和寄禅一起来到慈悲庵大门口时,寄禅向尼姑介绍:“这是我的俗家朋友杨哲子施主。”又指着尼姑说,“这是我的师妹净无法师。”
杨度向净无弯了弯腰。他瞥见这个尼姑的脸上略有点不自在。净无右手摸着胸前的念珠,左手竖起,停了好一会才说:“请杨施主进庵里叙话。”
寄禅忙说:“师妹,我看不必了。”又转过脸对杨度说,“皙子,我今天有件要紧的事去办,就不在这里说话了。我在法源寺里挂单,明天夜里我在寺里等你,我们再好好叙话。你一定要来!”
说完,又望了净无一眼便走了。净无也不再和杨度搭腔,赶紧转回庵里,把大门关了起来。倒是杨度一个人在庵门外默默地站了很久,他看得出寄禅和净无之间的关系非比一般。
九 悟宇长老指明朝廷亡在旦夕的三个征兆
法源寺是北京城内年代最老、规模最大的寺院,位于宣武门内法源寺前街。它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当时叫做悯忠寺。后来宋钦宗被金兵从汴梁掳至燕京,就囚禁在这里。明代改名为崇福寺。清雍正年间改建后更名为法源寺。
寺内共有五进院落。第一进为天王殿,第二进为大雄宝殿,第三进为观音阁,第四进为毗卢殿,第五进为藏经楼。法源寺最引以自豪的便是这个藏经楼。它藏有唐人和五代人的写经,以及宋、元、明、清各种刻本,还有用西夏文、回骼文、傣文、藏文、蒙古文书写的佛经,是我国寺院中藏经最多、版本最珍贵的藏经楼之一。藏经楼一楼左边有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客房,专为接待国内各寺院的高僧,寄禅就是以浙江天童寺住持、著名诗僧的身份住在这里。杨度进了法源寺,略一打听,便有一个小沙弥把他带进这间房子。寄禅早已沏好了名贵的天童茶在等候他了。
自从光绪二十九年杨度第二次东渡日本以来,他们已经整整七年没有见面了。这期间只有智凡法师在他们中间充当过一次青鸟。这次法源寺重聚,杨度没有询问寄禅这几年来的行踪,却抓住慈悲庵的那一幕师兄师妹别情来打趣他。
“想不到大法师也有儿女私情。真佛面前不烧假香,你今天当着我这个真正的师弟面前,把那个假冒的师妹的根由说清楚。否则,我就把她公之于十方丛林,让他们晓得原来得道高僧,竟是个风流情种。”
说罢哈哈大笑起来。
寄禅赶紧制止:“皙子,这里是法源寺,不是湘绮楼,怎能这样放声大笑,惊动了长老,会把我们赶出去的。”
杨度笑道:“莫拿这个来打岔,快好好交代。做个风流诗僧有什么不好?曼殊法师就是一个顶顶有名的风流诗僧。在日本时我最喜欢和他交往,倒是那些一本正经只晓得打坐数念珠的和尚,乏味极了。曼殊年少,法师年老,一老一少,相映成趣。哪一天我过得不如意了,也祝发入空门。我们三人,一老一少一中年,鼎足三立,做三个风流诗僧闻名于世。”
杨度越说越得意,寄禅也跟着笑了起来,说:“不瞒你说,我也喜欢曼殊法师,只可惜无缘与他谋面。”
“不要紧,听梁卓如说他就要回国了,我来介绍你们认识。”
“那好,我多时想结识他了。”寄禅真诚地说,“大家都说我是诗僧,其实,当今真正的诗僧要数他。他的诗有一种佛门韵味,我写了一辈子的诗,自认不及他。看来这不关乎苦吟,而是关乎慧根。最近我在《南社丛刊》上读到他的一首诗,真是妙极了。”
“这诗怎么写的?”杨度兴致勃勃地问。
寄禅拖长声调背道:“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背完后又情不自禁地赞叹:“齐己、皎然皆不如,堪称我禅门第一诗人。”
“噢,这首诗我早几年在日本时就读过。”杨度说,“你知道,他这首诗是为谁而作的吗?”
寄禅摇摇头。
“他是为日本一个名叫百助媚史的艺伎而作的,此人是他眷恋多年的情人。”杨度说到这里忙刹住。“我不和你扯远了,还是好好交代你的慈悲庵的师妹吧!”
“真拿你没办法!”寄禅苦笑道,“这事既然让你撞见了,我也只得跟你说一点了。其实,师兄我一生所缺的正是这‘风流’二字。若多一分风流,也就不会苦了净无了。”
杨度插话:“看来大法师与那位女菩萨真有一段动情的故事了。”
“唉,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寄禅收起笑容说,“光绪十年,我第三次去雪窦寺,谒见悟宇长老。长老那时正在讲授《心经》,四面八方都有僧尼前来听讲。我也在寺里住了下来,早晚两次听长老的课。有一天,突然有个年纪轻轻的女尼走进我住的禅房,说是听人讲我爱写诗,要看看我的诗。我那时只有三十多岁,血还很热,见有人要看我的诗很高兴,便把诗稿拿出来给她看,又详详细细地把每一首诗讲给她听。这位女尼很爱诗,隔两天又来看,于是我又讲。这样一来二往就很熟悉了。她的法名叫净无,是杭州城外覆舟庵的,来此挂单半年了。我问起她出家的缘由。才知她原是旗人,父亲是杭州旗营一个小把总。后来父亲病故,家里无钱运柩北归,便把她嫁给浙江臬司做小老婆。这臬司也是旗人,过门那年,已是七十三岁的老头子了。两年后臬司死去,大老婆容不得她,将她赶出家门。她无法生存,无可奈何地进了覆舟庵,削发做了个尼姑。净无的身世很苦。我们都是苦出身的,彼此互相怜悯。一个月后,她突然对我说:师兄,我们一起还俗吧!我听后大吃一惊,说:我已在阿育王寺舍利塔前烧去了两指,立下了海誓,如何能背叛还俗?净无再没说二话,便出门了。第二天上午没有见她听讲经,到了下午我一打听,才知道她回杭州去了。两年后我去杭州,特地到覆舟庵去找她。庵里的女尼告诉我她到京师去了。我想,她原是旗人,一定是还俗回籍了。从此便不再想这件事了。前几天我来京师,住在这里,与轮浆大法师谈起京师丛林中的僧人。他盛赞慈悲庵的净无法师禅学精妙。我心里想,这个净无是不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净无?怀着这个念头,我那天去了慈悲庵。一见面,果然是净无!我们惊喜极了。净无说,二十多年来,她常常记起我。遭到我的拒绝,她心里很凄苦,便只有一心礼佛,以钻研佛经来摆脱那层俗念。我听了心里直难受。”
杨度插话:“既然你难受她记念,再一起还俗也不迟呀!”
“我都六十岁了,净无也快五十了,还还什么俗!”寄禅的眼神黯淡起